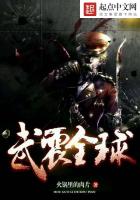“蹬鸡”
我们养的几只小鸡已经长得很大了,特别是我的九斤黄,更是长得高大。斗起鸡来,德明的两只芦花小公鸡,都是它的手下败将。刚开始,那两只羽毛未丰满,脾气却相当暴躁而且自命不凡的芦花小公鸡每次和九斤黄碰头就要比个高底。它们自以为是亲兄弟,常常合起伙来欺负九斤黄,但九斤黄没兴趣,懒得理它们。那两个自不量力的家伙得寸进尺,以为九斤黄是好腐头(好欺负),常常要挑起事端。有一次,九斤黄被它们逼急了,发起威来,头颈上的毛根根倒竖。它居高临下一斗两,没几个回合,那对难兄难弟便被啄得头破血流。从那以后,两只芦花小公鸡碰到九斤黄就如见到老祖宗,缩着鸡头颈,服服贴贴,而九斤黄也不计前嫌,与它们友好相处。
可是近来这三只小公鸡,都一本正经地开始学起了打鸣。虽然稚嫩的嗓门叫得不怎么响,可还是有板有眼的。张妈怕影响别人,就想把这两只小公鸡“蹬脱”(阉割掉),所以德明这几天都在留意阉鸡师来了没有。小时候,每到春夏之交,弄堂里时常会听到“蹬鸡……悠”的吆喝声。那时城里养鸡的人家多,后来,居委的阿姨经常到弄堂里来宣传城里养鸡的弊端,现在养鸡的人比以前少多了,所以蹬鸡的也相应地少了。
我们几个在小组里刚刚闹好坐定。突然,弄堂那一头传来一声德明企盼已久的吆喝。德明和我立刻奔了出去把那人叫了过来。那蹬鸡瘦瘦的小个子、黑黑的脸,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好像今天没有夜饭米。他腰夸一只包,肩背一个网兜。我们就去捉那两只小公鸡,也许它们知道今天要吃苦头了,逃得是飞快,我们一只也逮不住。
那人说了声:“我来。”只见他从背后解下网兜,往鸡堆里一挥,手起网落,网到擒来。他把鸡交给了德明,然后又是一网,另一只小公鸡自投罗网,钻进了网兜。
一群小孩一窝蜂地围了上来。给人开刀他们不敢看,只能看看给鸡动手术。那人轻轻地将鸡头一扭,随手塞进鸡翅膀里,又利索地在鸡的小肚子上拔下几撮毛,再把鸡牢牢地夹在自己的双膝之间。他从包里取出一个黑布包,把手术刀之类的摆在脚边,一把是手术刀,一件是一只长长的竹制小调羹。他把刀在黑布上来回擦了几下,只听“扑”的一下,半寸长的刀口就开好了。
晓萍忙问:“这刀你怎么不消毒啊?”
“小姑娘,鸡不是人,没那么骄贵。”那人头也不抬,他随手从地上拿了一块竹片,顺手一弯,靠竹片的弹性把刀口张了开来。我们就看到了鸡肚皮里的内脏在跳动,不过分不清哪是心哪是肺,当然,更不知道他要取的是什么样子。他把那根长长的竹调羹伸进刀口,掏了几下,用一根套在一端的线把“公鸡蛋”(**)拉了下来,用竹调羹取了出来。
“看看,就是这个。”我们这时才看清,这东西像一粒黄豆。
“这是什么啊?”晓萍又问。
“你小姑娘不要问,这东西没了,鸡就成太监了。”
突然,那人将割下的“公鸡蛋”往嘴里一放,咽到肚里去了。
“啊呀,你这个人不讲卫生,真恶心。”
“这个东西很补的。”那人一边说,一边将另一只“公鸡蛋”也取了出来,吞到了肚里。接着,他用针和线像补衣服一样把刀口缝了起来。我觉得好笑,如果这公鸡蛋像人参一样大补,为什么他长得又僵又瘦呢。
手术前后不过三、五分钟,做完后,他在鸡的刀口上涂了点什么东西,那鸡就一颠一颠地走开了。另一只小公鸡,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阿巍,把你的九斤黄也来蹬一下。”德明对我说。
“不要,阿巍,它很疼的。”晓萍忙劝我。
“还是不蹬的好,不然漂亮的鸡毛就长不出来了。”小黄也这么说。想不到我听了他俩的话,我的“九斤黄”去见阎王的时辰就大大地提前了。
经过阉割的小公鸡,从此就失去了做爸爸的能力,看到母鸡再也提不起精神,再也耍不成流氓,再也打不出那响亮的鸡鸣,成了“雌孵雄”。不过它长得快,肉鲜嫩,没有老公鸡那种臊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