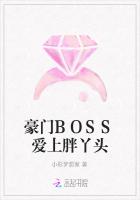如果说时光是岁月流逝中的沙,那么必定是握不住的,流逝的时光里的一幕幕,一个个片段,像是电影的回放,每当想起的时候都如同发生在昨日,如同还身临其境,感受着那时的快乐与悲伤,被拉长的时光里的情感也好,人也好,一成不变的都是曾经,都是那个当时。
道路两旁的树枝依旧往上延伸着,枝丫上新出的嫩芽分明还挂着清晨的露珠,像晶莹剔透的眼泪,一滴一滴的落下,落到行走在马路上的学生们身上,一晃,已经六年过去。
“呐呐,舒卿!你等等我!”君知背着书包气喘吁吁的跑来,呼出的气息喷薄在空气里形成白色的雾,“走那么快干嘛!!”
舒卿叼着一块面包,边咬边含糊不清的说话,“你再不快走,木清马上就追来了!”
“什么??”君知马上拔高了嗓音,没再有丝毫的犹豫拽起舒卿的手腕狂奔,“让一让让一让,江湖救急!!”
说起这个梗,要从三年前说起了,颜木清向君知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并开始了自己的追妻旅程,以至于吓得君知见到他就想跑,为此木清表示,一样很郁闷。
冲到学校的时候教室里暂空无一人,君知嘻嘻直笑,舒卿一愣神,看着君知眉眼弯弯的样子,忍不住吐槽,“怎么样?你还是第一次来这么早。”
气的君知去捏舒卿的脸,“你还是小时候可爱啊,你小时候多乖啊是不是,现在越来越不可爱了。”
这时候的舒卿长了一张婴儿肥的脸,圆圆的十分可爱,再配上粉嫩的皮肤,用君知的话来说,不捏一捏那不就可惜了。
窗外的鸟啼连绵不绝,藏在绿色盎然的枝叶中,春天的风吹得正厉害,通过打开的窗凑到两个少女的鼻息间。
教室里的人渐渐满员,离上课只剩一分钟时,木清才慌慌张张的跑进来,君知噗嗤一笑,他赶紧朝她笑,君知却又不高兴地别过脸不看他。
右边黑板的角落里用规整的楷体字写着,距离中考还有一百零七天。
人总是会觉得一切尚早,其实当某些事情到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了这么久,就像这已经过去的六年里,后来一度想要珍惜的情谊,在失去的时候才猛然惊醒,奥,原来是我没有抓住。
春日的路家大院最是有着古风的味道,少女的年纪正是怀春,最喜欢的便是荡在院中的花秋千,君知静静地坐在上面,歪着头倚在绳索上,手里折了一朵小花,一个花瓣一个花瓣的往下拽,嘴里还默念着,“他喜欢我,他不喜欢我,他喜欢我,他不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君知低头看看手机光秃秃的花,皱着眉头鼓着腮,“再来一次!”
“哟?眉头都打结了,这是谁又欺负我们的小君知了。”不再是少年吊儿郎当的模样,干净的白色运动服穿在路君凡的身上,衬得皮肤更加白皙,睁着和君知一样的微棕色大眼睛打趣。
君知不高兴的回头看了一眼,完全没有把他的打趣放在心上,“我说老哥,你要是闲的没事做的话,我今天的作业还没有写。”
路君凡正打算苦口婆心的来一翻教育,就被君知伸出一根手指头打断,“您老要是想教育我的话先回忆一下你自己吧,锦哥哥应该回来了,我去看看。”说罢将那朵残花小跑着塞到路君凡手里,还颇为正经的点点头,“这花儿跟你呀,绝配!”
路君知的衣角都看不见了路君凡才将那朵花放进左胸的口袋里,面上带着愁容,“区别对待啊,也不知,是福是祸。”
随着符锦泽年龄的增长,也不再与路君凡同住一阁,路泊清为他安排了一间比较大的客房。
房间与君知的杵君居临近,为此君知还高兴了好久,房间外种着几株百合花,据说是符锦泽亲自买来的。
君知站在门外有些开不了口,越是长大明白了自己朦胧的心思在面对符锦泽的时候越是不自然,君知觉得自己快被这种矛盾的感情问题折磨疯了。
没等君知敲门,符锦泽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是君知么?”
君知一阵哆嗦,感觉像是被抓住的小偷一样,想要说话才发现舌头都打结,“啊,是我,我,我来看看你回来了没有。”话刚出口,君知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明显就是借口。
君知觉得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多大点事啊,“嗯,我来找你的。”
符锦泽正坐在书桌前练字,拿着钢笔的手突然一顿,微微闭了闭眼,仿若在经历痛苦的挣扎,再开口时还是那样再平常不过的语气,波澜不惊,“有事么?”
君知一阵气结,“没事不能来找你么?”心里揪成一团,好像被人撕扯般的难受,一口气憋在肚子里,上不来也下不去。
自从自己明白了对符锦泽么心意之后,他就好像是知道了什么一样,总是故意和她保持着距离。
房门从里面打开,那一刻君知觉得少年仿佛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十七岁正植青春的年纪,骨架比例完美的豪无瑕疵,素来好看的面容如同这个春天里的一缕春风,能够吹走人心中的一切浮躁。
君知的嘴角立马扯开一个很大的弧度,波光在眼睛里跳动,“你肯出来啦?”
“我最近,比较忙。”
“忙?忙什么?”如果人是会变得,那么符锦泽认为路君知所变化的只有年龄和身高体重。
“忙父亲遇到的一些问题。”符锦泽的眼神明明灭灭,最终寂灭下来。
君知低头咬着手指,有些纠结和扭捏,“明天我们一起去后山玩儿吧,刚开春,后山的空气特别好,那儿还有一座假山你一定没有去过吧,平时看你总是窝在房间里……”
“砰!”的一声,门被符锦泽从里面关上,还传出他最后启齿的两个字,“不去。”
君知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突然觉得很委屈,这大概是她这辈子做过最丢人的事了,她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曾经背着她看散云,拉着她走过大街小巷的符锦泽突然从某一天开始陌生了,他们之间的相处不再是她熟悉的模式。
电话还在嘟嘟嘟的响,君知泄气的放下电话,嘴里喃喃自语,“舒卿这是去哪儿了呀,怎么不接电话。”然后编辑了一条短信发送。
躺在柔软的大床上,疲惫的一根手指都不想动,喜欢还是熟悉的喜欢,人却不是熟悉的人,君知认为有一句话是对的,我是喜欢你的,而你却是自由的,她想她应该永远也说不出口那句喜欢,就像她这个人一样,越是靠近别人,最终一定会分离。
那边的颜家,君知打来电话时刚好木清在旁,木清两眼放光的样子惹得舒卿一阵鸡皮疙瘩,连忙将手机藏起来,“你想干嘛?”
木清眼咕噜一转,装的十分不屑一顾,“我能干嘛呀?又不是只有你知道君知的电话号码,我问别人也一样。”只是离开时一步三回头的频率让这话的说服力十分低劣。
铃声不再响,舒卿发了一会儿呆,才从被子下面将手机拿出来,短信在这时送达:我好像,是真的喜欢上符锦泽了。
春季的黄昏凉风习习,舒卿起身走到窗边关上了窗子,又在房间里踱步了许久,神情时而怀念时而悲伤,时而痛苦时而纠结,时而开心时而茫然,时而艳羡时而不甘,最终叹了口气,“其实你们都好幸福,谁又能理解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