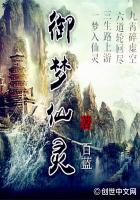我扯出一抹笑,说:“我没事。你呢?”
“我也没事。”他看着我,目光里泛着些研读式的怪异,但只有几秒,一晃便消失不见。他拍了拍身旁的位置,对我说:“过来我这里坐。”
我坐到他身边,他伸手抱住了我的腰,把我的头按到他的怀里,低声说:“真的很抱歉,让你受到了惊吓。”
我摇头:“我没有,不过……”
我想问,余光却看到病床上的小乐。我想还是等回去在问吧。林警官说的对,一定有事,否则温励不会如此自责。
小乐的情况称得上不幸中的万幸,他醒来后自己回忆,说他突然被人打昏,醒来时已经被丢进来鲨鱼缸。而温励眼尖地发现鱼缸里有血丝,从而做出了反应,蛙人下水,以最快的速度拉出了小乐。但此时最近的鲨鱼已经咬到了他的腿,好在鲨鱼个头小,工作人员又抛下其他活珥,终于救了小乐一命。
小乐的腿险些不保,愈合的周期将会很长,警方说他们会接手,费用温励这边会帮忙。因为有警方的解释,孩子们并没有受到很多影响,而且这次警方出面,一并解释了黑帮买画的事。
忙完这一天,我和温励都觉得十分疲倦,晚饭也没吃就躺下。
温励照例躺在枕头上看我祷告,等我祷告结束,便挺忧郁地看着我,问:“你整天都在祷告什么事?”
“有的时候祷告明天礼仪老师不要来,有时候祷告地铁上人少一点……每天都不一样啊。”重点是布朗说要每天祷告的,虽然我没见到温励祷告。但温励出生就信奉基督教,肯定已经做到心中有神,万神归宗的地步。我呢,还是希望全能的上帝能给我一点实质性的好处,“不过今天祷告的是希望小乐快点好起来。”
这是诚心诚意的,我们被拐卖过,并不是我们的错,是坏人太坏,不该让我们承担后果。
温励微笑起来,握着我的手臂,温柔地说:“别担心,他会好起来,以后也不会再有人伤害到他。”
我看向他,点头。
温励也微微地笑了起来,幽蓝的眼珠凝望着我,没有再说话。
此时,我只觉得他的眼神十分温柔,并没有多想任何事,却不知,一场冰寒透骨的噩梦,已经在我面前悄然拉开帷幕。
小乐的重伤导致我们后面的所有计划全部取消,温励怕我难过,说等去欧洲时再玩。
不久后,小乐被转到特殊医院进行保护和治疗,我和几个孩子一起去送他。
刚送他们上了飞机,我突然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她在电话那端尖叫着,几乎都快哭了,说:“温柔!宿伯伯给我打电话了!子衿睁眼了!”
挂了电话,我没有想到要打给任何人,一门心思地冲向了医院。
从机场到医院,坐车需要一个多小时。而在这一个多小时里,我的脑子是完全的放空状态。
满脑子只有一句话:我弟弟醒了,我所有的动力,最后的希望,唯一的家人。
我至今还记得爆炸的那天,冰冷的太平间,我一个人呆在那,看着对我有着再造之恩的父母。当时警察说,我们家是震源,所以,我父母的尸体,都是只有一点点。
他们不让我看,我却还是看了。
那时我还没有想到外债和其他,我只觉得我什么都没了,我是个煞星,自己倒霉,并且害死了救我的人。
当时子衿在急救室,抢救了一整天,推出来时,说是脑死亡。医生没有说得很明白,只告诉我也许会醒,但还是做好最坏的准备。
一开始我不能相信,但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金钱的拮据,让我不得不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准备接受我的天才弟弟变成植物人,永远不会醒来。
但现在他醒了。
而我连高兴的表情都忘了,冲进医院,冲进病房,却被拦了出来。
宿伯伯随后走出来,和颜悦色地笑着说:“刚刚我们给他做个检查,你现在可以进去看他了,情况很稳定。”
我走进病房,在子衿病床前坐下,他正躺着,张着眼睛,混沌地看着我。
我试探着叫他,“子衿。”
他也只是看着我,像个呆子。
我有好几天没有来看子衿了,因为自从手指动了以后,他就没有再做出任何改变,我似乎也习惯了,习惯他不会动的样子。
但他睁眼了,虽然他看起来不认识我,我也还没来得及询问宿伯伯,不知道他的情况,但我已经觉得所有的灾难都过去了,全都雨过天晴。
我就这样在子衿的病床前坐了很久,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恰似久别重逢。
突然,我看到子衿放在床单上,插着管子的手,无力地抬起,轻轻地放下,一下、一下、又一下地敲敲击着。
我伸手勾住他动作的手指,看到他漂亮的大眼睛凝视着我,眼神像婴儿一样,可爱又无辜。
这一刻,我不由自主地笑了,但与此同时,眼泪亦是不由自主地淌满了一脸。
没过多久,子衿就累了,又闭起了眼睛。我却以为他是突然出了什么状况,连忙跑去找宿伯伯,糊里糊涂地描述了一趟,宿伯伯吓得立刻赶来,看过子衿之后,笑着对我说:“没事,他是太累了,毕竟这两年都只是靠营养液维持生命,非常虚弱。”
说着到了他的办公室,宿伯伯坐下来,对我说:“子衿是昨天晚上开始睁眼的,当时是护士发现,我们也观察了一下,做了一些检查才通知了你们。我已经把所有的数据发到省里,会针对他的病情出新方案。”
我忙点头:“那费用……”
宿医生说:“肯定要有所增加,不过你先生之前来过,说账单只要发给他,不能给你过目,真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已经结婚了。”
回去的路上我依然兴奋得回不了神,王女士跟我说了好几次话,我都没听到。
一进家门,柯基小盆友就冲出来迎接我,我正抱着它打转,温励的车就停过来了。他下了车,来到我旁边,还没说话,我就已经放开柯基冲过去抱他了。
子衿能醒,温励是最大的恩人,没有之一。
温励任我抱了一会儿,在我要流着口水亲他时侧头躲开,笑着说:“我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亲爱的,拜托你在管家面前淑女一点。”
我这才醒过神,扭头看到布朗,他正低着头,却还是被我看到脸上抽动的肌肉。
好吧,我淑女一点。
我抱住他的脖颈,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说:“我弟弟醒了。”
他吻着我的头顶,轻轻地“嗯”了一声。
“我还没通知家里的亲戚,因为想独占这种高兴。”在这样灭顶的激动下,我几乎失去了全部理智:“我是不是太坏了?”
他搂住了我的腰,没有回答。
“那天出事之后,亲戚们都说,没人要的孩子不能养,养了克星。”我抱紧了他,忍不住地哭:“我反驳不了,因为我也觉得他们有道理。”
温励依旧没说话,抱着我的手,一动不动。
“所以我好怕他再也醒不过来,被我克掉了一家人的命。”我止不住地恸哭:“我爸爸妈妈都是好人,带我回家,养我长大……”
此时此刻,我只想发泄我憋了一下午,憋了足足两年,无人排解的情绪。我不是一个天天都开心的人,只是不敢告诉别人,因为这个世界很危险,不能释放软肋给任何人。
但温励是我信任的,因为他帮了我太多的忙,因为我好喜欢他。
我这样也不知哭了多久,终于渐渐冷静,松开了手,用衣袖擦着脸,忽然听到温励轻轻的声音,问:“你是孤儿?”
我愣住了。
我看着他,一时间没有回过神。
蓝色是一种冰冷的颜色,尤其是灰蓝色。
此刻温励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看着我,裹挟的并不是愤怒,而是浓浓的失望,他这样看着我,问:“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解释:“我是孤儿,我被拐卖过,抓我的犯罪团伙跟小乐是一个集团,那个集团到现在都没有全部落网,我不能说出去,警察不准我说。”
“所以,你那天告诉我,你的朋友被拐卖,那个人就是你。”温励完全不听我解释,只是非常失望地说:“小乐告诉我,他曾在那个团伙里见到你,他说你的名字并不是温柔,我认为他在撒谎。”
我愣住了。
我并不叫温柔?
温励抬起头来,看着我,问:“可以告诉我你真正的名字吗?我自认有些手段,竟没有发现你还有另一重身份。”
他一定是误会我了,我连忙解释:“我在那个团伙里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我妈妈她姓温,可能是因为这样……我真的记不清了。”
温励看着我,失望地痛心疾首,没有说话。
原本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却突然间不能再开心了,难过地问:“你会不要我吗?”
温励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目光看到了我的身后,低声说:“任何事我都可以接受并尊重,只有一个死穴,就是欺骗。我不喜欢被欺骗,尤其在我查不到真相的情况下。”
“是警察给我们重做了记录,所以你才会查不到。”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他才会信:“我不是有意要骗你,但……你看到小乐了吧?他对你都说了什么?肯定与那件事有关,他才会被扔去喂鲨鱼。”
温励看向我,深色依旧是那么冷:“在寻找捐助对象时,小乐的这段经历很容易就被我查到,他也告诉我团伙中另一个孩子的名字,我也查到了,是公开的资料。唯独你……”他看着我,轻轻摇着头,难以置信地说:“唯独你不通,今天早晨我联络到另一个孩子,他也称在那个团伙见过你。是不是只有你的背景被遮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