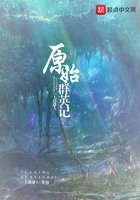胜利路X号,这是残联办公大楼的地址,某一层被单位多年前买下做办公地点。这条路是这个城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从步行街中段拐进就是残联大楼,大楼底层的店面租给了一些时尚店铺,橱窗里悬挂着哈韩哈日的服饰。
残联院内,挂着这样一些牌子:残疾人信访办、假肢技术中心、精神(及智力)残疾者亲友中心……,在这个地址上班,命运仿佛随时提醒你做为一个健康人的幸福。无论你刚被薄情寡义的爱情抛弃,还是几年来为之殷切奋斗的晋升机会被同事暗地干掉。从进入院子起到等电梯,你内心原本强烈的人生颓败与怨愤一点点显得可耻起来,因为劈面,你遇见了他们!
空荡着袖管或裤管,蜷着只到你膝盖的身高,听力(或视力)黑暗的他们,立在你身旁。有时在院里,在你放车时,他们三两个站着(或坐在轮椅)向你打听残联的某位同志。同志有时不在,他们就在院内静等——这是他们最惯常的姿势,无望的表情因为等待多少带了点惨淡希望。能找到这院子就不易,步行街不通车,必须穿过或南或北的小巷绕进来。他们来自各地市,包括偏远农村,带着在当地部门没能解决的问题,拎着人造革包(装着残疾证申请书之类),衣服陈旧(领口露出三种颜色以上旧线织的毛背心),粗糙开皲的脸和手,静默着,等待作为他们这个群体政府保护人的出现。他们极少有拍着大腿号哭或脸红脖子粗骂娘的来访者,他们只是耐心地立在那,等。
他们乘上质量糟糕,频频故障的电梯,电梯光线幽微(有时散发死鼠气味),每逢这时,我恨不能替他们做点什么,籍以补偿一丝命运对他们的残酷以及对我们这些人的高抬贵手,能做的当然只有摁电梯,且往往有手快的捎带替他们摁了——都知道他们要去的层数,不会是X楼的户外运动俱乐部,也不会是Y楼的私立牙科,只能是政府同志们所在的楼层。
有回,等电梯,碰见一个十四五岁的盲少年和父亲。尽管频繁地碰见残疾人使我已然有些渐趋麻木,但这个孩子还是让我猝然一痛。他不是牵着父亲,而是整个依傍着他,他有张纯洁柔和的面庞,丝绒一般,眼睛弯弯的,如果不盲,那会是双很好看的眼睛。世界于他就是父亲的衣襟吧——他的父亲,一个面染风霜的清瘦男人,看得出,为这孩子,心被沉重辗挤着。他们当然也是来申请或争取些什么,少年快赶上父亲的个了,神情却还全然是个羞怯孩子。他的心大概像冬天的植物,缓慢而纯洁地生长。
盲,那是怎样一片无边沼泽?少年的两手抓牢父亲胳膊,像那是惟一一座桥梁。
我曾认为,盲,这是身体缺损中最残酷的一项,以我对物质世界的恋厣和懒惰,我想“看”是与世界最直接的联系,薄薄的眼皮承载着人与世界的交往,而盲人们,他们的视力被谁预支走了呢?上帝引他们来到世上,却忘把灯拧开,要他们独自在暗中摸索。
在朋友那看伊朗影片《天堂的颜色》,里面的盲孩因为父亲续弦而被送去盲木匠那做学徒,他满怀悲伤地告诉师傅,在学校,老师告诉他,在这个世上他们并不孤独,只要伸出指尖,就能感受到上帝的温度。他说,“现在我不停地伸出手,直到有一天我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为止……”——这个善良,命运悲哀的孩子,他的指尖什么时候才能碰触到上帝的慈爱?
想起胜利路X号,那个在繁华的商业街背后隐着的地址,很久没去那儿了,很久没看见背阴处的他们,深秋的树桩一般戳在院里的他们。上帝离得那么远,指尖的温暖一时半会传递不到,人世的人们先对他们好一点吧,哪怕一寸微薄温度,有时,也许会让他们以为是上帝先行派来的信使。
傍晚,从家赶着上哪去,忽闻歌声。本往西去,歌声使我临时改了个道儿,决定从东边走。
路顶头是人民公园,右侧菜场,路两旁挨挤着店铺,土杂店,平价服装店,编织店,桂林米粉……这是条很市井的街,吸引着各种流动人员的到来。
人行道。音箱,话筒,椅上坐着小个子畸型女人,红布上写着“爱祖国残疾人表演团”,前方有个箱子——供路人投币。这是个由残疾人拼合的小团体,名称响亮忠诚,令人感动——他们这样子还不忘爱祖国。独臂男孩正唱《爱在深秋》,目光忧郁,与季节和歌声吻合。背后,是家卤菜店,以卤大肠闻名,几颗脑袋正为最后若干猪大肠挤进一个窗口。路上,行人车把上挂着晚餐材料,轮子踩得飞快,如果不是这辰光,或者愿驻足消遣的行人会多些,毕竟唱得很不坏,不比综艺节目里一些声嘶力竭的歌手唱得坏。
我攫着袋里的钱站在路对过,非常为难,不知怎么才能把钱放进箱子。箱子离他们有点距离,正式地摆在前方,投币的行人因此也会显得正式,像挺身而出,或某企业代表上台捐助爱心善款。这感觉先使我觉得了难堪,而且,那男孩,我确信,在他唱歌时女性的投币会暗中刺伤他,他齐整的衣着和眼睛说出了这点,当有姑娘路过,他的目光总是装作无意地别向他处——一颗年轻灵魂所有的一切敏感他都有,甚至更充沛,而他的歌声不能献给任何一位姑娘,更多为打动大妈大嫂们。
次日,黄昏路过,歌声仍在。换了个年长点的独腿中年男人,《上海滩》伴奏响起,他唱了第一句,颇有几分周启生(这个男人有倜傥颓迷的音质)之风,粤语纯正,我定在原地,老实说,他唱得真好!不止于歌唱技术的好,是内心经过风浪,把音乐消化了的好,不羁歌声里有能把人内心惊动的东西!他不像昨天那个男孩拘谨,他手持话筒,镇定自若(隐含一种对命运的反抗),对着一街人流,把公园路(街对过,环卫工把半筐烂白菜利落地扣在车内,结束一天营生的肉贩将刀子在油腻抹布上揩试)直唱成回肠荡气刀光剑影的上海滩,人生啊,浪奔浪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
洇开的路灯把街道抱个满怀。《上海滩》的歌声里,令人恍然觉得不应陷入在如此庸常,如此营营苟苟松垮如泥淖的日子里!而应当拼刀子,应当浪迹江湖朝不谋夕,应当爱得惊涛骇浪!我生出小说的联想,想他大约曾是歌手,一个在酒吧喝整晚酒也不会抬头的男人,日子洒脱,一个偶然(同时命定)的女人出现,她的容颜成为他沉溺的另种高度酒。与她有染的事件将他卷进,他因此得罪某人,此人染足黑道,为证明自己的不好得罪,把他一条腿给做了——如同发哥演的那些片子。再出江湖,歌厅不能唱了,从前一切烟消云散,女人不知所踪,他心如死灰,可不至去死,他见过世面,有担待,连悔都不言。往下活吧!于是拉了几个伴游走外省卖唱,潦草行头,颠沛的火车,从人们因过份谨慎使用而愈来愈吝啬的同情心里谋生计。喉咙,这是他活在人世最后最珍贵的行李。现在,只有庞杂的江湖能收容他和他的歌声。
第三天,黄昏,他们没再出现,连同一些路边摊与游民。或者是有关心这条街的正义而热心的市民反映,城管部门把有碍市容市貌的事物一并作了清理。像路上被风刮跑的随便一张落叶,他们去了下站吧?即兴的,惘然的,对他们来说全然陌生的下一站,或者,只是根据别的飘泊者的道听途说,据说,那地方人对歌声更敏感一点,同情心也稍许丰满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