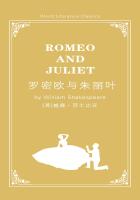相较往年,07年上海冬天真暖得一团和气,最高二十三四度的天气几乎和同期基金行情有一拼。高悬的八瓣雪花,红绿圣诞彩带,窗上喷的白靴——但因为暖,圣诞还是像借来的节日。以前圣诞,有寒冷打底子,多少有点以假乱真,似乎圣诞老人真会友情客串,坐着雪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今年这般暖,圣诞老人雪撬只有搁浅,节日就有些穿帮。
气候越来越含糊,四季暧昧,问阿姨小马,“不冷吧?”她肯定地答,不冷!有时弄错,把人着实冻一下。再一日,我问小马,今天冷吗,她刚从外面进来,用她的口头禅答,一点不错!今天特别冷!我穿了许多出门了,结果阳光普照,汗都出来了——但回去我没和小马讨论天气的事,我怕她会无所适从,此后会奔到外面用温度计测了温后再告诉我当日天气,谁让我们都不看天气预报呢?
潜意识里,觉得天气预报挺多余,在人世厮混这多年,冷暖还不自知?动物们从不听预报怎么过的?难道我们的皮肤不是最好的感应器吗,不比那些仪表更准确?只要静心体会四季,风或雨雪的讯息会通过某种感应秘密地传达到我们,像在古代,天气分明,人心灵敏,古人凭经验总结出的关于气节时令的经验缜密优美,淮南子先生就说,“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观象授时,这是优雅又沉静的科学。
还有那些民谚,“天公作变,水面变靛”,“云向南,雨漂船;云向北,晒干麦”,简短实用。有次看到远安县茅坪场中学“2005年校本课程”,课程上有“气象万千”一节,教学生如何观测天气,野外寻找水源、取火,如何穿越灌木林,防雷电,指北针的使用等,这学校有意思,是个和自然密切往来的学校。
现在,我们对天气的掌握全来源电视,“天气预报”这档节目的粉丝人数之众绝不亚于“超女”或“快男”,哪怕不大出门的老人,从李修平邢质斌罗京等同志坐在那起,他们目不转睛,竖起耳朵,像明天有重要的外事活动。次日,他们极可能就呆家看“夕阳红”剥毛豆——他们是替儿女关注的天气,这关系到各地儿女的出行以及本地儿女会否回来晚饭。这顿饭对晚年的他们是珍贵的。
气候从不是单纯的气候。比如我,总和天气弄拧,总不能恰如其分地穿对衣服,就像总不能恰如其分地融进人际以及其他天气。
气候对一个城市的浸染也显而易见,它的湿度和温度会直接影响城市性格及命运,寒冷伦敦,在狄更斯小说里,它终年弥漫大雾,街道潮湿,路灯昏黄,行人竖起衣领匆匆赶路,其中可能就有心怀远大前程的青年皮普。
还有长年灰色天空的丹麦,一位朋友在那呆了几年,说丹麦自杀率很高,头顶的那片灰也许给了人们过多心理暗示。还有越南,四季闷湿,所以会有电影《三轮车夫》和《情人》中的越南。
电影也总是热衷以天气配合人物命运,主人公遭遇突变,伤心冲出家门,天空多半电闪雷鸣;当主人公追忆一段纯洁爱情,多半在雪天;当老了,回忆往昔,公园长椅,秋风中必有五色树叶纷坠,如罗切斯特先生与家庭女教师简爱的重逢。
有部获1985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的法国电影《流浪女》,冬日晨曦,流浪女Mona像垃圾一样冻死在荒郊水沟,导演瓦尔达说,“这是部从死亡开始讲述的故事,终点即起点,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我理解为——它跨越了死亡!”
电影描述Mona 在生命中最后两个月的状态,没悬念,影片开头就展示了死亡。“不要问为什么,你只看一个年轻女人如何面对自己和孤独就行了”:
“这样的坏天气已经不适合露营了。”牧羊人
“我从不选择天气。”Mona
“那么你选择道路?”牧羊人
“是的。”Mo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