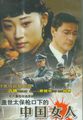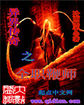他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位五十多岁的干部模样的人。他自报了姓名。开门的人先是一愣,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他无奈,便冒雪去小城五里以外的妹妹家借宿,妹妹收留了他。第二天,他的妹妹,一位六十多岁的农村妇人来到了他昨天晚上被拒之门外的门口。她叩开了门,劝说侄子收留他的父亲。这怎么可以呢?侄子至今还记得四十年前那个令人撕心裂肺的岁月。在将袓上留下的那份家业一一一个面坊、儿处宅院挥霍踢踏净尽,并留下一屁股烂债给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后,他与一位跟大孩子年龄差不多的小姑娘私奔了,此后再无音讯。他在外地又成了家,且生儿育女。几年前,那位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妻子死去了,孩子们对他也不孝敬。于是晚境凄凉的他,踏上了四十年前曾被他狠心遗弃过的这个家的归途。没想到,他当年遗弃过的孩子,现在这个家的命运的真正主宰者,也以同样的狠心拒绝了他。
儿子,这个五十多岁的普通干部,此刻的心里也是痛苦与矛盾兼而有之的。毕竞是生身父亲啊,将其拒之门外,未免有些冷酷无情。可一想到与年跟年轻的母亲含辛茹苦,挣扎着走过一个又一个艰难岁月的情景,心中的怒火又腾地升起!什么父亲?简直是坏蛋……然而,愤怒归愤怒,作为儿子,他也只能将其默默咽进肚里。可儿媳呢?却对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的突然回归,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就是自己丈夫的生身父亲么?就是那位年轻时吃喝嫖赌,出入于大小戏班日夜厮混,并最终遗弃了儿女妻子的负心汉么?她与他,不仅陌生,亳无亲情可言,而且在她眼中,他简直就是罪恶的化身她哪能接受得了?!
但儿子,还是不得不把父亲归来的消息告诉给了母亲。母亲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儿子简直不明白母亲早已干涸的泪泉,何以会依然存留着这么多苦涩的泪水?母亲央求儿子收留他,要儿子把这个负心的男人接进门。看样子,她也会像当年一样给他做吃做喝,伺候他的。儿子分明感到,母亲的精神世界在迅速向着当年那个青春时代回归。她满脸活气,仿佛一下年轻了十多岁!
儿媳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她大声问婆婆:“妈,屋里那个老汉是谁?”
最后,儿媳与儿子托着亲戚给老汉下了逐客令。老汉不得己离去了。
越?年,老汉又回来了。他当年的妻子又高兴地接纳了他。可儿子和媳妇还是想不通,他们要赶他走。老汉昵?此刻不但不再萎缩,而且以攻为守,向儿子儿媳兴师问罪:“你们为啥要在我的这个老宅基里盖房?为啥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啊,看那理直气壮的样子,好像这房产权还在他的手里。
儿子为此苦恼异常。不接纳他吧,他毕竟是跟内己有着血缘关系的老人,而且晚境又是那么凄凉,更何况,母亲也在切盼着某种缺失已久的感情的补偿;接纳他吧,那深嵌心底的怨恨,难听的名声,还有妻子这道几无越过希望的门槛,他化解、承受得了么?
绝望,驱使一个老人返归曾被自己厌弃的土地上寻找希望。垂暮,让他重新向往最初的黎明。
然而,一出由自己亲手编导的长长的人间悲剧,现在,却企图以光明的尾声作结,容易么?!
一串蹒跚零乱的足迹,留在小城深巷内外。这便是故事的结尾。
1985年11月1日
三蝠画像
1
一位年近八旬的长者。
他,高鼻深目,使人想起中国古画中的胡人形象。黧黑的面颊,犹如黑炭一般。大得出奇的耳朵,使人联想到大耳的米老鼠。一旦说起话来,便两眼忽而圆睁,忽而紧闭;那双大大的耳朵也跟着上下动着,很是滑稽。
面容清瘦,但绝少折皱,这倒透露了他的性格的一个方面:古板而又单调的表情。
剃过的头,短而硬的银发,如同—块黑炭上落着层薄薄的秋霜。记忆力蛮好,反应也快,说起话来吐字清晰但嫌啰嗦。
1982年5月28日
2
我要找人民公社领导。
一位热情的三十五六岁模样的干部把我领到他面前。他,头戴竹编的己经变成暗褐色的遮阳帽,像关中农村常见的那种既便宜又结实且不怕四级左右野风吹落的帽子一样。他正在将一只洗得发白的军用帆布袋,挂上放在自己的宿办兼用的房门口的肖行车头。
他瞥了我一眼,说声:“来!”便将我引入宿舍。接着递给我一杯水,并说:“嫩。”我瞅了一眼屋内可以落坐的东西,一只竹躺椅,一只矮矮的长椅,另奋一只木椅放在最里面靠近厘角的地方。显然,那躺椅该是主人常坐的位置,而对面这张矮矮的可以坐三人的长椅,便是来访者理想的位置了。
我取出介绍信交给了他。他接过看了,然后不假思索地说道:“这事杨主任管。但公社放假了,星期六人才回来!”简短,明了,公事公办。失望!我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我递一支烟给他,他摇摇手说:“我不抽。”但等我点着了烟,自己抽了起来时,他却又不知从哪儿捞起一只装有黑色卷烟的长杆烟袋,也点着火,抽了起来。一副冷漠、厌倦的神态。
我不能再待下去了,站起来说声“告辞”,他并没有站起,只将身子往前欠了欠,哼了句:“好!”……
五十开外的年纪。发胖而又松弛的面部肌肉,光头。
1982年9月9日
3
夏收碾场,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公社副书记,想借生产队麦场一角,提前碾自家自留地的麦子,正好被年轻的生产队长掩见了。XX哥,你把麦往啥地方拉?
―场里!我想叼空把自留地麦子碾了:只占用一角角场地!你往回拉!队里有纪律:大场不清,小场不开!一一只这一点,好兄弟,就给个方便!不行!你开了头,乱了谁负责?!
于是,这位干部便去找队长的父亲求情,没等老人开口,便被队长硬戳戳地回了一句:“谁来也不行!生产队难道没奋自主权?老汉败下阵来,这位公社副书记也怏怏而去。过了两天,这位公社干部调来所在公社一辆圆盘拖拉机,找到年轻队长说:“给咱队上帮忙种种地!”“好么!那你把司机经管好;粮油队里付!”
几乎同时,他破例腾出一块麦场角儿,让这位干部去碾自留地的麦了,并叮咛道:“碾完了拉到你门口去扬,这地方还紧着用哩!”
队长原是一位民办教师,因感卩所在生产队落后,便连写三封自荐15,要求担任生产队长。获准后只—年,便让这个队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1981年7月
嫉妒之果
A男、B男、C女系大学同学。
后来B男、C女结婚,并跟A男一块儿分往同—所中学任教。A、C常来往,似绝无隐情。
A教学成绩出众,引起某人嫉妒。遂找B男挑拨说,A、C有不正常关系。B半信半疑,回宿舍问妻子,遭坚决否认后,便去跟A谈心,试图和解。此后,A与B、C来往渐少。
假日某晚,B去厕所,路遇A跟一位教师持手电筒一块儿值班巡逻。C怕B跟A因旧事再起纠纷,便跟着去看,但没见着。返回时,正碰着B自厕所出来,C问我去A处怎么没见到你?B顿起疑心:先我一步去A处,莫非真有什么隐情?想到这儿便不由火冒三丈,转身去找正在巡逻的A挑衅,并指着A的鼻子大骂“流氓”。A被辱骂,也顷刻起火,即挥手电筒向B砸去。C见A、B厮打,即赶去叫来校长劝阻,斗殴遂止。A怒不可遏,要上法院控告;C亦因此蒙羞欲跳湖自杀;B此刻后悔莫及,但又不愿供出挑拨者。A、B、C均为受害者。害人者却暂时得以逍遥事外。“谣言可以杀人。”说得好极了。“谣言是成功的影子。”同样说得好极了。嫉妒之树上结出的,必然是下流的谣言这枚毒果。误食者大都是因为被它温柔漂亮的外衣所迷惑,因而遗恨久久。
但一经被揭露,法纪道义的利斧,便会毫不留情的连它的根也砍个尽净的。
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为自己的耳朵,打造一个坚实的根基。
1983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