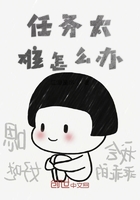努尔哈赤坐在木床上,捧起水罐喝了几口,就跟狱卒攀谈起来。
梨花站在窗下,透过窗户纸缝,把屋里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她看着,叹息着:他老了!灰白的头发盘在头上,额头上已是道道皱纹,脸上的皮肉已失去红润,变成核桃似的绛紫色,看着,看着,她眼前又浮现出在抚顺马市初次相见时努尔哈赤英俊的形象;想起在老秃顶子岭上的日子;忆起在北京悯忠寺的一瞥。几十年来朝朝暮暮,哪有一刻忘记过他呀!想到这里,她有心破门而入,同努尔哈赤彻夜长谈,然而当她离开窗口,又犹豫起来。她想,如若相认,岂不给汗王带来麻烦?再说半夜三更在狱中与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相会,也会给贺总兵招来是非。怎么办?咬咬牙,眼泪往心里流,救出汗王,就是一件幸事。想到此处,她抹了一下眼角,转身走出牢房的长廊,在狱门口找到侍女,一口气跑回总兵府。
此时,贺世贤正坐在堂屋西间吸烟,等待夫人查监的消息。烟雾伴着蚊香,满屋青烟萦绕,贺世贤望着袅袅烟雾,幻想着未来:一千名刀斧手押解着老汗王,进入京城,步入宫殿;宣武门外汗王被斩首示众,人人夸赞贺世贤有功;皇上亲赐蟒袍玉带,黄金白银……
“咯吱”一声,门被推开。贺世贤见夫人进来,慌忙站起,问道:“夫人,囚禁之人可是那汗王?”“一点也不假。”“你不是开玩笑?”“人命大事,谁敢开玩笑?”贺夫人梨花脸绷得紧紧的,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押送京城,邀功领赏!”贺世贤高兴得山羊胡子抖着说。
“他与你何冤何仇?”贺夫人梨花坐在炕沿,毫无笑意地问道。
贺世贤不解其意,反问道:“夫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君子向来不杀无辜!”贺夫人梨花站起来,两眼盯住贺世贤,道,“既然汗王与你无冤无仇,你为啥要伤害他?夫君,你还记得秦王李世民遇险,众生救驾的故事吗?”
贺世贤一时被问得晕头转向,他眨着两眼,坐在太师椅上,又吸起烟来。他吸一袋烟,把烟袋往条几上一扔,站起来问夫人道:“你是叫我把他放了?不,不,不能。镇疆守界是兵将之责,我要把夷人放走,岂不是叛国欺君?”
“你的忠心倒是可嘉。”贺夫人梨花道,“可惜,替纣王、秦二世那样的昏君卖命,那可是愚忠!”
贺世贤刚想辩解,贺夫人马上抢先发话:“李成梁、杨镐、李如柏、刘埏可谓尽忠尽义,可是他们哪一个有好下场!罢官的罢官,下狱的下狱,逼死的逼死,阵亡的阵亡。难道夫君,想步他们的后尘?”
“你这是替汗王说话!”贺世贤六神无主,抖动着肥胖的身子,白净的方脸上肌肉抽动着,不服软地说,“老汗王又与你何亲何故?”
“是我的救命恩人!”
接着梨花把自己从小卖艺,在抚顺被小罕子搭救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然后扑通跪在丈夫面前,恳求道,“夫君,请看在我的面子上,救汗王一命吧。”
贺世贤不加理睬,梨花步步进逼地道:“夫君如若不肯给我这个面子,那我就撞死在你脚下。”说着,贺夫人甩头朝椅脚上撞去。
贺世贤见夫人如此恳切,慌忙将夫人扶起,为难地道:“我可以答应夫人的请求。可,汗王被俘之事,已有人知晓,此事若传出去,岂不招来灭族之祸?”
“谁能认出老汗王?”贺夫人问道。
“贺小六。”
“他有什么凭证?”
“老汗王攻打开原时,他亲眼所见。”
“嗯!”贺夫人梨花笑道,“贺小六临阵脱逃,已够死罪,靠这样的人作证,岂不向外人表明你是窝藏逃兵的罪臣。夫君,你不要再干那种引火烧身的傻事啦!”
贺世贤被说服了。在贺夫人梨花的策划下,以夜审为名,把努尔哈赤请到总兵府,以礼相待。
第二天下午,贺世贤正陪着老汗王宴饮,忽然门官来报:“一个沈阳城老相识前来求见。”
贺世贤陪努尔哈赤在正房西间宴饮,为避人耳目,特意到东间接客,门官把客人带来,贺世贤见是个眉目端正的中年汉子,连忙问道:“请问客人尊姓大名?”
“沈阳人氏范文程!”
贺世贤听到这熟悉的名字,连忙站起,把范文程让到座位上,致歉道:“先生本是大宋范仲淹之后,卑职有失远迎。”
范文程客气了一番,正欲打听努尔哈赤的下落,忽然努尔哈赤推门进屋。范文程一惊,立刻迎上去施礼问安。贺世贤见两人一见如故,笑道:“原来二位一条是苏子河,一条是小沈水,异道同归,共人大海哟!”
三人互相寒暄一番,就一起入席再饮。这样,范文程陪老汗王在总兵府一连住了七八天。
一天,京内忽然传来万历皇帝驾崩的消息,沈阳城一片惊慌。恰逢这年辽东碰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眼看已到秋收季节,辽河两岸的庄稼都是遍地枯黄。高粱无粒,稗谷无穗,而满地乱爬的黑盗虫,把地里仅剩下的野菜,也咬得叶梗皆无。饥荒袭击着辽沈村民,他们一听说皇上已死,一个个生怕兵荒马乱,便四处逃荒,寻求生路。沈阳城内到处挤满求生的难民。
贺世贤眼见这种悲凉景象,十分懊丧。一天傍晚他邀老汗王、范文程再次酌饮,就大发起牢骚来。他坐在八仙桌右侧,喝得红头涨脑,连损带骂道:“他整年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一死完事。可剩下我们这些带兵的,一无粮,二缺饷,怎么混下去?真他个奶奶的,皇上,皇上,就是黄了上西天!”他拎起银酒壶为努尔哈赤斟了满满一杯酒,又说:“汗王,您也是一方之王,我很佩服你!你能带兵,能打仗,还亲自探察,不怕坐牢房。来,来!”他举起酒杯,邀汗王干杯,边喝边道,“我真佩服你这马上皇帝!”说着推开椅子,向努尔哈赤跪下。
努尔哈赤慌忙将贺世贤扶起,道:“小人只是个族人头领,哪能跟真龙天子相比!”
“不,不!”贺世贤有些醉意,手发颤,说话舌头根发硬地道,“什么龙不龙,那都是骗人的玩意。我只信奉一条,能替百姓着想的人,才配当皇上。汗王,您就到北京当个皇上吧。”
范文程马上接着话茬儿道:“汗王可是北方夷人哟!”
“什么夷人不夷人,还不都是皇羲、女娲的子孙!”贺世贤又为老汗王斟了一盅酒,自己先喝干,把酒盅一推,道,“当今谁有本事治理天下,谁就该登基坐殿!”
贺世贤话刚落音,贺小六陪着龙敦偷偷地推门进了屋,嬉皮笑脸地道:“哟!总兵大人,您长几个脑袋!”贺世贤抬头一看,马上目瞪口呆。因为皇上治丧期间,是不许设宴取乐的。此事若叫皇室知道,定要杀头。
贺世贤虽有几分醉意,但头脑仍很清楚。他想:捕获老汗王之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底细。今后若万一被小六子传出去,必招大祸。今日何不先下手,以除后患。贺世贤历来手脚利落,他想到此处,一面从身上摸护身匕首,一面唤道:“小六子,你身后是谁?”
贺小六子刚一转身,一刀飞去,正中贺小六后心,便一命呜呼。跟随贺小六前来拜会总兵的龙敦,见贺小六身亡,转身就跑,他刚跑出门槛,早被范文程飞镖打中后心,于是转眼间,也命归西天。
努尔哈赤见倒下去的,一个是捕获自己的那个汉子,另一个是自己追杀的叛逆内奸,就连忙站起,朝贺世贤拱手致谢,道:“日后我若得天下,一定请将军为帅!”
贺世贤拱手笑道:“鄙人只要不再受大明朝的窝囊气就是了。”
贺世贤叫近侍把贺小六、龙敦的尸体抬走,又畅饮了一个时辰,便各自歇息。又过了一日,贺世贤便差人把努尔哈赤、范文程两人送至城外。临走的那天,贺夫人梨花站在城楼,遥望着汗王的身影,暗自流下了眼泪。这些天,她既高兴,又觉得委屈。高兴的是,老汗王安然无恙而归;委屈的是,因礼教家法,不得面见汗王,像当年那样促膝谈心。而老汗王走出城门,也恋恋不舍,他一步一回头,心里想着梨花。他在总兵府虽住了数日,但高墙相隔,难得与梨花相见,虽有心与梨花见面,但又不便与总兵提起此事。所以,近在咫尺,遥距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