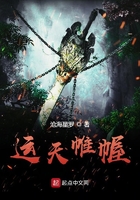入夜,肖云夏跟着牛十口一道,由陈幺娘带路,一路到了一座坟包跟前。
“就是这了?”牛十口问。
“是,是这。”陈幺娘见儿子坟墓,又忍不住掉了泪。
牛十口站了一阵,嘴里连连说道:“奇怪,奇怪,夏小子,你可有什么想说的?”
肖云夏哼哼一声,说:“师父,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周围,都是坟包,今晚又是黑月风高,按理说应该是阴风惨惨,野鬼游荡才对,但是现在看来,却是安静的很,这满山的坟头,没有一个鬼魂。”
牛十口点了点头,似乎十分满意,但表情却是凝重的很:“所以说啊,奇怪了,我有十分不好的预感,不管了,夏小子,你先试试看吧。”
肖云夏牛十口说完,便在地上摆了些供果,据陈幺娘说,都是他儿生前喜欢吃的东西,燃了符箓,掐了指诀,只在嘴里碎碎念到:“老祖传牌令,金刚两面排,千里回魂症,速归本性来。”
肖云夏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念了百遍,符箓燃了好几张,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只急的满头大汗。
一旁看着的陈幺娘不禁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只怕是觉得自己方才那一跪太亏了,又请来一个冒牌货。
牛十口脸上挂不住,让肖云夏退到一边,青铜古剑一凌,插上一张拘魂符,凭空引火点燃,再掐了个追魂诀,居然想要千里拘魂!
最终还是失败了,牛十口根本感应不到任何鬼魂的气息——“难道都转世轮回去了?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么说,真有人……不会,这么多坟头,不会的……”
牛十口喃喃自语,扭头看了看那陈幺娘,说道:“走,带我去其他人家的坟看看!”
陈幺娘本不想答应,此刻她已经认定了这家伙是个没本事野路子,甚至骗子,但看牛十口一脸焦急近乎发怒,她一个老婆子也不敢惹,便只得带他去了。
一连去了好几个坟头,牛十口施法好几次,都和第一次一样,什么东西都没招来,这满山的坟头野地,居然没抓到一只游魂野鬼!
没办法,牛十口只得在那陈幺娘鄙视的目光中回了村子,陈幺娘也不好多说,只简单收拾了一间屋子给他们住下,自己去和陈秀云挤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牛十口就找到陈幺娘,虽然对方已经有些不耐烦,但依旧问到:“老太,那些人,都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辰?”
陈幺娘没好气的看了牛十口一眼:“哪里?自己屋里!半夜的时候,莫民奇妙的就发狂死了,不是中了邪,是什么?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
肖云夏在一旁听了这话,立马就跳了出来,说道:“什么行不行?我们又不收你们一分钱,还骗你不成?”
“管饭不要钱啊?”陈幺娘见肖云夏还嘴,脸色一下就拉了下来。
肖云夏偏不让,直说道:“明跟你说了吧,不光你家儿子魂不知去了哪,这整个山头,就没见到一缕魂,你们村,出大事了!还说我师父没本事?”
陈幺娘懒得理他,摇着头,直接走了。
肖云夏几步追上去,继续说道:“别走啊,你倒是给我说一下,你们这还有哪几个人以前是骚扰过那个红鲤的,还有,这些人死的顺序是怎样的啊?”
陈幺娘没回头,但话还是回了:“大概还有三个了,但具体老婆子我就不知道了,张银生,张大禄,张林。”
说完,便不再回话,只顾自己走了,师徒两个也不好去追,只得楞在那里,这备受冷落的感觉,真是让人不好受啊。
陈秀云倒是给师徒二人端了一些稀饭面饼,打了一叠酸菜,算是早饭了。
草草吃了饭,牛十口收拾了家伙,就带着肖云夏出门了,师徒二人在村子里转了一整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也没捕捉到什么有鬼停留过的气息。
随后,他们又找到了那三个目前的“幸存者”的家,打听些情况,这些人家一见到牛十口是个道士,都是欢欢喜喜的接进门去,有问必答。
这三个还没遇害的男人无一不是对他们骚扰红鲤的事情悔青了肠子,现在整日里担惊受怕,生怕哪天和其他人一样的下场,丢了性命;肖云夏突然兴趣使然,问他们为什么不跑?
但几人回答都是一样:“不是不跑,是跑不掉,之前有人跑过,都是被人在半路上捡了尸体回来,既然跑不掉,横竖要死,还不如就死在自己家里。”
之后,肖云夏又问了问他们骚扰红鲤的先后顺序,和过分的程度,再问了问这些人死亡的先后顺序。
起先那几人碍于面子,不愿回答,但最终还是败给了对死亡的恐惧,也一一说了出来,只求肖云夏和牛十口能相处法子救他们一命。
但是,没有什么规律,也不知是几人记错了,还是怎样,总之,这死人的顺序,和红鲤被骚扰的先后顺序无关,与严重程度也无关,这样一来,就不知道那索命的无常接下来会找到三人中的哪一个。
最后,肖云夏没有办法,只的叫牛十口给他们三个人一人一道蓝阶辟邪符,叫三人贴身放着,自己却找了个草垛睡了。
一天晚上,三个人没发生任何事情,师徒两个拖着疲惫的身子从藏身的草垛里出来,刚伸个懒腰,就听见村子里一阵喧哗吵闹,两人跟着声音过去一看,却是一群村民围着一个院子,一个个怒气冲天,一面往里面丢石头,一面叫骂,内容大多一样,都是叫那家人滚出张家村,别在这里祸害别人。
肖云夏挤进去,找个人问了才知道,就在昨晚,肖云夏和牛十口守着那三个人的时候,又有人被害死了,与以往不同的是,死者是个女人,据说就在前两天因为她家男人的死,逮着红鲤骂了一顿,还打了她一巴掌。
这回村民们彻底愤怒了,决定将他们两口子赶出村去,所有人都相信这些事情和红鲤有关,即便不是她亲手所为,也是被她害死,毕竟这些人,都得罪过她!
而这里就是那红鲤和李打渔的家。
篱笆小院,三间青石瓦房,的确比周围的房子要好了许多;此刻家门紧闭,窗户也关的严实,似乎不准备搭理外面的人。
一个老者站在最前面,双手抬了抬,示意大伙儿安静,待所有人都停止了叫骂,那老者才对着那屋子喊话:“红鲤啊,李打渔?听的到我不?”
“张保长,您老有话就说吧。”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屋里传来,果然十分好听。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但民愤难平,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日子以来,死于非命的人都多多少少和你有所牵连,我劝你还是早日搬走吧,别等着我也管不住他们,让他们做出出格的事情来啊。”这张保长的话中,看似劝说,却是软硬皆有。
“看来,他们的确没证据说是这红鲤干的,要不也不会仅仅是赶走她那么简单了。”肖云夏在一旁想着,突然很想见红鲤一面,看看她究竟生什么模样,是人是鬼,还是妖。
“不管是鬼是妖,都麻烦了,能在这青天白日里行走,且还是个人的模样,而且还和应大活人生活了一年多,那级别不知要多高,至少也是妖将或者鬼王……”肖云夏不敢往下想了。
这时,红鲤又说话了:“张保长,这些事情,任何一件都与小女子无关,既与我无关,我为何要搬走?这些年来,我家相公虽不是大富大贵,但也送与你们不少好处,不说银钱,鱼总是数不过来了吧?怎因你们的孽反倒要赶我走?”
张保长听了,说道:“即便不是你所为,但只要你在,我张家村就不得安宁,叫你家相公出来说话,你一个女人家,做不得主!”
话音刚落,就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保长啊,你不要说了,我听我娘子的,这事我们也觉得蹊跷,又被大伙儿误会,心中更是委屈,就这么一走了之,岂不是背了个名声?”
两人皆不同意搬走,张保长也没有办法,摇了摇头,退了出去。
村民们又开始叫骂了,有的人甚至翻了进去,拖着锄头就要去砸别人大门。
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肖云夏睁大眼看清那女子模样:柳叶眉,鹅蛋脸,淡抹两朵朝霞,嘴抿胭脂,头挽云鬓,一只碎玉步摇跟着她一步三摇;披一件淡橘鳞纹披风,着一身橘色涟漪鱼尾裙,三步金莲藏在里面,每走一步就荡起一阵涟漪,比起青槐县柳悻婷来,不相上下,却更多了几分端庄典雅。
“果然是个美人,也怪不得那些男人整日里想着她了……”肖云夏暗自想着。
那红鲤一出来,叫骂声突然降低了许多,也不知是那些男人又转意了注意力,还是害怕了这个女人,就连那几个气势汹汹要去砸门的男人,也是一步步的往后在退。
总算见到了这个女人,肖云夏心中却是更加疑惑了,这个女人,他看不出有任何异样,除了生的好看之外,和平常女人,没有其他任何区别,要硬说点区别出来的话,那就是这个女人的气场庞大,根本不像一个农家媳妇!
“难道是那个男人?”肖云夏不得不转意了思路,但瞬间就被否定了,因为那个男人紧跟着就出来,虽是生的高大,但不用多说,一看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渔夫,老远就闻的到他身上那股鱼腥味,也不知这红鲤怎么就看上了他?
肖云夏无奈,扭头看着牛十口,牛十口也是一脸茫然,显然,他也没看出什么蹊跷来,这红鲤,并不是鬼或者妖,如要真是,那就是等级太高,也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