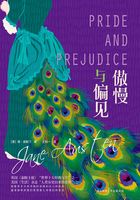毫无疑问,一旦一个人的命运由权力决定,要想改变命运只有匍匐在权力的脚下,这么多年在官场,我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看作被权力决定的物件,指哪儿打哪儿,其实,在官本位的驱使下,每个人都习惯了用“子女”的眼光看官员,这才有了父母官之说,人们早就习惯了服从各种权威、传统、道德等等,在这种服从中,人们是极其厌恶的,但又不得不投向权力的怀抱。因为谁也无法抗拒用官本位的价值观评价一切,这种价值观驱使人们在权力面前自愿放弃自己的自由,成为听话的工具。在成都开会时,我和张怀亮陪张副市长去了一趟都江堰,站在咆哮的岷江面前,望着被水利工程驯服的壮丽的江水,张副市长颇为感慨,他说“深淘滩、低作堰”有些像做人的三字经,“遇湾截角,逢正抽心”,有些像官场的八字真言,我觉得他说的很形象,这都江堰好比官场,张副市长就好比岷江的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然而,现实中的官场又有几个人能读懂都江堰消灾、滋润、濡养的内涵呢?
回到东州,我搜集了有关张副市长的所有资料,从资料中得知,张副市长祖籍在北京,清朝末年北京大栅栏有一家赫赫有名的玉石老字号叫“玉石张”,便是张副市长的祖辈开的,后来为躲避战乱和仇家逃难到了东州,在东州扎了根,不过玉石生意和手艺从张副市长的祖父手里丢掉了。张副市长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十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从小就是孤儿,是在亲属家长大的。由于个人勤奋好学,又有心计,一点一点奋斗到今天的地位,其中甘苦可想而知。
古人讲,“用谲不失其正,行权不诡于道”,可是我对张副市长的规矩越来越不敢恭维,总觉得他的内心世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让我对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隐忧。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在识别领导选择领导的同时,也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的命运毫无疑问地与张副市长拴在了一起,他值得信赖吗?其实,我经常这样问自己,然而我越扪心自问越迷茫。
在剖析张国昌灵魂的过程中,我的灵魂却躁动不安起来,我的思想像苏醒的黑水河,不停地寻找心灵温柔的两岸,并朝它幽远的深处流去。我在这种苏醒中发现,时代不同了,古代的太监被阉割了 阳 具,现代的我们被阉割了个性。太监的 阳 具 是别人割去的,而阉割我们个性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我的个性是什么时候被阉割掉的,我只知道命运的虚伪不是一般的虚伪,而是非常成熟的虚伪;命运的圆滑不是一般的圆滑,而是非常成熟的圆滑。面对命运,我无法逃遁,也无处逃遁。生活给人更多的不是感动,而是震撼,领悟生活,首先要领悟自己,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提醒了别人,自己才可能有出路。张副市长会接受我的提醒吗?我陷入一种深深的迷茫。
为了写好党性分析报告,这两天我煞费苦心。我按照中央党校提纲要求的五个方面,写了约有一万字,因为我从未写过这类东西,先抛砖引玉,等张副市长看后再删改。
一晃又是周末,我去北京接张副市长回东州,在飞机上,我将写好的党性分析报告交给他,他在飞机上一直看,看的很认真,一路上基本看完了,但什么也没说,我的心顿时揪了起来,贴身跟了他快一年了,对他的品性我再熟悉不过了,没说什么就是不满意,但也没提出再让我修改的意见,似乎我写的这个报告可有可无,我断定张副市长一定也找别人为他写党性分析报告了,会找谁呢?最熟悉张副市长同时他也最信任的人只有韩寿生,难道张副市长也把党性分析报告的活儿交给韩寿生了?我带着这个疑问陪张副市长回到了东州。
第二天下午,张国昌和李国藩一起召开了銀环路工程调度会,会场安排在工地指挥部。调度会开得热烈紧张,李国藩和张国昌都是大烟筒,与会者赛着抽大哥大,指挥部里是云雾缭绕。
“同志们,”李国藩打着手势说:“这是一场战役,是一场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的大仗,为此,我们要把银环路工程建成廉政建设的示范工程。”
“我与李市长商量了一个六不准,五公开,”张副市长环视一圈会场说,“下面请仁杰同志给大家念一念。如无异议,便是铁的纪律,便是银环路建设的‘军法’。”
丁仁杰清了清嗓子念道:“六不准的内容是:不准各级管理人员介绍亲朋好友参与工程、搞不正当竞争;不准以任何借口收受回扣或索取任何好处;不准任何施工企业在使用材料上掺杂使假,以次充好或转手加价;施工中,不准多头分包、层层转包,二次转包需经指挥部批准;不准地平材料(砂砾、石料)借机哄抬物价,缺尺少秤,违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准任何部门的工程建设和施工单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五公开的内容是:公开动回迁和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公开实行工程建设的招投标;公开成本造价;承建单位公开材料进货渠道、价格和原材料消耗;公开责任体系、监督网络。”
丁仁杰念完后,张副市长接着强调说:“大家如果对七不准,五公开无异议,就由市纪委、市监察局组成的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执行。”
散会后,李国藩、张国昌又到工地,看望了工人。在工地,李国藩煽情地说:“工人师傅们,你们的任务很重,很艰巨,困难很大,但东州市人民相信你们。希望你们既要有科学的态度,又要大胆创新,不负全市人民的希望”。说着与工人们一一握手。
我陪张副市长忙了一天。傍晚送他回家,刚下车就对我说:“雷默,你跟我上一趟楼。”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便跟着上了楼。走到他家门口时,他突然停住脚步说:“雷默,应该说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都高,但是写的东西操作性不强,我在车里没说,是怕马厚听见,你不好意思,党性分析报告我让韩寿生也写了一份,我觉得比你写得好,操作性强,咱俩上楼,我用传真机给你复制一份,你拿回去学习学习。”
我的预感终于应验了,当我拿到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后,心情复杂极了,好比夜里被霜打了的花朵,我看着张副市长近视镜后面凸起的眼球,仿佛看到了靡菲斯特的目光,张副市长先是揶揄我,“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都高”,然后又挖苦我“但是写的东西操作性不强”,仿佛在借靡菲斯特之口说:“理论之树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绿”,然而,我一边下楼耳边一边回响着《跳蚤之歌》:“跳蚤穿上了龙袍,浑身金光闪耀,宫廷内外上下跳,他威风得不得了。啊哈!哈哈哈哈!跳蚤?……”我觉得我就像歌中的跳蚤,却又像被跳蚤咬了一样浑身痛痒。
晚饭后,杨娜想让我陪她去散散步,我说太累了,便把一个人关在书房内看着放在写字台上韩寿生做的党性分析报告运气,不知不觉抽了半包烟。杨娜散步回来时,一支烟正在我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燃烧。
“默,干吗呢,眼睛直勾勾的,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杨娜关切地问。
“还不是党性分析报告闹的,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写完了,人家不满意,说什么操作性不强,党性分析报告又不是会议纪要,是剖析思想,要什么操作性,这不,背着我让韩寿生也写了一份,说韩寿生写的有可操作性,把我写的给枪毙了。”
“张市长怎么这么做事呀?”杨娜抱怨地说,“每天都像在搞阴谋诡计似的。”
“这种人对谁都不信任,我看他连自己都未必全信。”我牢骚满腹地说。
杨娜顺手拿起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看了起来,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默,这哪儿是党性分析报告,这不是坦白书吗,这份党性分析报告,张国昌如果交上去,怕是要开除党籍了!这还是人民公仆吗?这里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谁知道是真是假,明天我送他回北京,飞机上再说吧。无论如何我都得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要让他知道韩寿生写的这份党性分析报告一旦交上去的后果。”我愤愤地说。
“默,”杨娜心疼地说,“真难为你!”
“娜,你不知道,我现在就像一团萤火,既不燃烧,也不熄灭,游荡在日出与日落之间。”我痛苦地说。
“默,原以为当上市长秘书前程就有了保障,没想到你这么痛苦。”杨娜抚摸着我的头说。
“娜,有时候我真想学学《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喊上一句:皇帝他没穿衣裳!但是看一看周围那些欢呼雀跃的人,你就知道世俗的力量有多强大,什么勇气都没了。”我又点了一支烟蹙着眉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