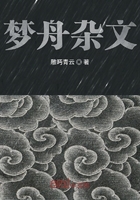小倩遇见过几次林峰,眼神像定海神针,盯哪定哪,邪性地骇人。
小兵不知什么时候出去的,一回来就跟鬼子进村似的,鸡也叫鹅也喊牛也哞,叮了咚咙。因为怕被指责一天就知道玩啥也不干,所以就自觉地跑着喂鸡喂鹅喂牛。
“天哪!赶快洗脸去,你小子比恐怖分子还恐怖!”
一家人围在桌边吃饭是最温馨的。夜幕黑它的,灯会照亮屋子。电视节目只是陪衬。
“我都打听好了,小倩走的时候我去送,女娃娃子安全要紧,不就来回的火车票么!”
“毛衣我让绢子妈给打呢!”
“还早呢!”
虽然熄灯了,一片黑暗。可是小倩毫无睡意。
“以后不要让小倩一个人去地里头,又是闹鬼又出了这么件事,要防着点。”
“严翠花怕是自己把自己砍了吧?脖子肩膀上好多淤血呢!你说说出了这种事咋好活人呢……”
小倩静静听着,心想被打出那么多血来了,都应当告状打官司,怎么还怕传出去丢人,到底是农民,太没有法律意识了!
乡村的风似鬼游荡,夏夜,凉如水,梦也浅。
二
天刚麻麻亮,早就睡不着觉的王萍下了炕。今年像是遇鬼了,老是似睡非睡的不塌实,身上也老觉着麻麻的,起来活动活动还好一点。
一连串吵吵嚷嚷,由远及近,停顿在大门外,又变成激烈拍击铁门的咣咣嗵嗵。
鬼催命啊?清明大赶早的!翻身穿衣服的周新皱了皱眉头。
一个鬼里鬼气的白发魔女,直冲进屋,血红的眼睛扑到周新后,就滂沱淌眼泪,“你就是队长!我们是严翠花的老不死的爹娘!那个驴日的牲口把我的闺女往死砍呢?你说说让人咋活……”
王萍把女人搀住,按她坐到炕沿上,“慢馒说!”
女人吸了吸鼻涕,觉得不管用,干脆拿手拧了抹在裤子上。男人显得镇静多了,从裤兜里摸出烟,递了一根给周新,然后自己叨了一支。
“女儿早晨连饭也还没吃就出去淌水,我在家左等也不见回来右等还是不见人影——谁知道——呜呜——”女人说着说着又嚎开了。
男人无可奈何,只好提高嗓门说:“都是养人的人,看见娃娃成了那个样子,老婆子当时就不行了。你是队长,有些事还得请你给帮忙,看看事情该咋处理?”
女人勉强抑制着情绪,但是旋涡里的悲愤,使她整个人都在抽搐,浮肿的脸上五官也扭曲了,特别是眼睛,火辣辣的喷着凶光,“要是没人管,我就拉上女儿到村上到县上到市里头告状去!个驴日的,我告不倒他就不活了!”
王萍攥住女人的手,“谁的人谁心疼!”
女人的眼泪又喷出来了,目光柔和了许多,“我的三个娃娃从小到大,自己都还没有舍得指个一指头呢!你说,嫁给他姓林的,就让人这么个欺负!他林有理装好人,顾着兄弟,不把我的女儿当人看!没人管了我领上回……”她的气焰因为愤恨又变得嚣张了。
小兵本来还要在炕上赖一会儿,可是闹哄哄的,特别是那个老女人,像动画片里的红眼睛巫婆。
人都沉默了,听凭女人发泄。抽烟的抽烟,做饭的做饭。直到女人意识到了失态,不好意思起来,“你们看看我都气傻了,顺着嘴就胡遛,大清早的。”
她揉了揉眼,哗得就苦笑了,“我们来,其实也没别的。你是队长,情况可能也了解一些。他林有理不管是经公还是私了,我都想请你给做个证,麻烦你去医院看看我女儿让那个驴日的伤成啥样子了。”
“啊,就是这么个事!”男人补充说。
“你们来找我就是看得起我。我尽量劝着把事情处理好。”周新说。
看到小倩往桌上端饭,女人就要走,“耽搁你们了——跟上儿女心都操碎了。”
“坐下吃饭!”
“不了!不了!”
周新和王萍一起把老两口送了出去。
吃完饭,听到周新推车子的响声,王萍忙跟了出去,“你好是去林冲家呢?”
“不么!我去苏庆那儿看看。”
天气透着凉,风爽快地撒欢。村子中间的小路坑坑洼洼的,还淤积着几天前汪的雨水,周新不得不推着车子走。
何仙姑坐在自家墙角的沙枣树下搓草要子,看到周新,老远就讪讪地笑。
“哎呦,你把石灰抹到脑门子上了?别演戏的画得是白眼窝,你这是当白脑门盖呢?”
“嘿嘿……可能早上的油没抹开!”
“怕是猪油庆住了抹不开!”
“唉!个老别咱的!”何仙姑起身,抓起一根草绳甩着打周新。
周老五在院子里和了一大滩泥,拎着锨,光着脚板在掺了碎柴的泥浆里面来回走着踹。
周新脸上的余笑还没散尽,“上房泥呢?”
“唉!一下雨就漏,他妈的气死人呢!”
周老五的媳妇气哼哼地抱怨道:“上回叫你多上上一层,你不听,看看这次打得这个麻烦!猪脑子!”
“呵呵——猪脑子也怨你找上了!”
“房泥上好了晾一晾,去沙窝拉一车沙子在上面撒一层。”
“他们四爹也这么说呢!”老五媳妇笑着问,“三爹,听说大舌头昨天晚上让派出所的人给抓走了,就是吧?”
“我不在家,可能吧!”周新推着车子赶紧走。
人都闲得心慌呢,到处查事。
黄毛的墙根根站了一伙,李虎的大门口围着一群,窝在一起肯定是说三道四的,也不怕让人多心?
刚到村头的公路上,周新看到林冲和老外母提着包包蛋蛋的坐上了公共汽车,看样子是去医院。不知从哪里就窜出梁玉林婆姨汉子,张着爆米花的脸,笑望着开走的车,嘴里还唧唧呱呱的。
周新别过脸,蹬上车子准备骑,却听到黎明喊,“你先别忙,我还有个事呢!”
周新停在路上,“你不是跟别都干活去了——怎么在这里日呀游呢?”
“睡忘记了!没赶上趟。正好放一天假,打打麻将!”
“你别咱的活得好么!快说啥事,我还忙着呢。”
“还不就那天的那个事。”
“你自己总先去叫去呢,看看她是个啥意思,再和你妈商量商量看咋办。就是我去,也就是劝劝。”骑上车子,周新在心里忍不住骂,个胡日赶赶的,不好好过日子老是打媳妇,就该让别娘家整一整。
如今,什么都讲究效益,农村也是这样。一年就忙上几个月,种到田里再收到回家里,闲时候多,事也就多了起来。很多事不说不知道,一说呀,不由得让人感慨人事无常!
何仙姑家的沙枣树下,坐了五个婆姨,人人面前一捆草,手不停地搓着草绳子,嘴不住的说着笑着,抑扬顿挫,传说着各自听到的小道消息。
“老张建的婆姨放命着呢,没几天了!”梁玉花的女儿就嫁在五队,所以她提起这件事时,表情很认真,左右打量了每一个人,确信没有碍事的,才压低嗓音说,“那年,老张建跟刘老五的婆姨跑了,她就喝药没闹死。你看看撑了这几年硬是给气死了!胃癌晚期——噫?这几天,你没听你们老二家的说?”
“别自从女儿嫁了个有钱的,变得眼睛朝天瞪着呢!”周老三的女人面无表情的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吴怀理的女儿也让那个坏良心的女婿折磨疯了。”她是吴怀理的小姨子的表姐的堂妹。
“是不是就是去年在我们家猪圈里钻得那个媳妇?”
周老三的女人捅了一把甄红英,“这都是丢人臊毛事,你别瞎嚷嚷!”
也许说点别的,跟谁也挨不着边,会痛快些。秦香莲说起三队前几天打场,一个十五岁的丫头让脱粒机把一条胳膊打折了。其他的四个女人也放开眼光,把谈资扩展开来。讲起一队那年因为打人劳改的那个人,刚放出来又把人轧死了。四队苏美老认为婆姨把钱偷偷给娘家了,动不动就找因因打,婆姨一气之下喝了一瓶乐果,头发现送医院已经迟了,临死才告诉,钱在哪点哪点藏着呢!六队查出来已经有五个人得了肝癌……
然而,这些故事终究由于传闻的来源渠道太曲折,说起来缺乏细节,淡得没嚼头。
秦香莲用几乎耳语的声音说,“你知道那个大舌头那年为啥离婚?”
“不是那个媳妇要离得么?”甄红英结好草绳子头,停下来竖起耳朵听。
“我听别人说,那个媳妇在法院告大舌头尽打她,还说不管她身上的血干没干,就硬要来……”
“啧啧!这个媳妇子!真不害臊,啥都敢说!”
“说是说呢,那个长得又白脑子又好使,比这个强多了!黑不溜球的蜂窝煤……”
何仙姑好久都没说话,但是心里头一直翻着冒泡泡。说吧,传出去又说她戳是非,不说吧,憋地心里头涨得难受。有一回,她去林冲家转,看到大舌头翻着两个白实实的眼睛也坐在屋里头,即不说话也不挪窝。她觉得不是个滋味要走,但是严翠花说啥也不让,悄悄跟她说林冲不在,这个林峰又使也使不走,死气捭呆地怪慎人的。而且,出事的那天早上,她去田里揪梅豆,大舌头好象就一直在林冲家周围东蹙西看的,贼头火烧的。她一直怀疑要出事,果不然——不过活该,谁叫严翠花长得招骚呢!
“大舌头可是个不要脸的下三烂!别看话说不利索,心思恶心着呢!那个黑媳妇才回了一天娘家就闹出了这个事,天生就是个断子绝孙的显货!”听着大伙儿的议论,甄红英冷不丁的插了一句,然后“呸!呸!”地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唾沫,入了一撮草,把最后一节搓完,利落地绾住梢子。
什么事情结论一旦出来,就好说多了。女人们的兴致越发高扬,说得时候挑眉弄眼声音小小的,骂起来野辣辣的,笑起来又肆无忌惮哈哈的,就像头顶上的一片片沙枣树叶,随着风的南来北往,左右摇晃变幻着阴影的形状,发出无拘无束的动静声响。
人聚在一起,就得说话,至于是人话还是鬼话,全在听众的判断。
周老五新盖得砖房前,一伙男人边干着活边东拉西扯,从中国加入世贸说到布什决心倒萨,从陈水扁搞台独骂到李宏志的法轮功,从税费改革讲到种草种树搞养殖……一架银色的飞机轰隆隆低低飞过,震耳欲聋的声音压断了唾沫四溅的讨论,他们都停下手里的活,仰着脖子看,直到天空恢复了宁静。
周老大的大儿子周力往房顶上扔了一锨泥,说:“这一向子,老有飞机在天上飞,而且低低的,怕是找啥着呢?”
周军在房顶上把哥哥撂得那团泥攒到锨上,端着倒在他三叔跟前,故意扬声说,“中国准备打台湾呢!”
“胡说,胡说!飞机是来勘测修新农村路的。路线都划好了,就在华华的田前头!”正在用锨踹着和泥的周老五狠狠往房顶撂了一锨泥,破锣嗓子像遭了电击。
蹲在房上的周老三周老四被突如其来的大喊骇住了,便歇下抹子专注地听,然而不过只是这么一句话,周老五又默然和泥了。
周老三说:“我怎么听说是划分开发区来着!”
“胡说,胡说,开发区早就划好了!”周老五胀红了脸,宽出了2寸腮帮子。
周老四笑了:“还有人说是泰国人要找个没污染的地方养奶牛呢!”
“胡说,净都胡说!”周老五急得把才抽了两口的纸烟,狠狠往地上一砸,抬起光脚板,实实的碾了3个来回,才感觉到烫,边跳脚边喊,“净都胡说!”
终于找到了机会,报复讨论时世时老抢白自己的五叔,周军笑嘻嘻地说,“我们老爸爸赶上朱容基了——啥都知道!”
大家都轰隆隆笑开了。连在屋里张罗着做饭的周老五媳妇也跑出来问什么事。周军惟妙惟肖地学了一遍。
“可是个转脑子!”周老五媳妇骂了一声,扭头钻回屋。
周军哈哈哈的大笑,“还是老婶婶厉害!”
周老五急了,“到冬天给你找个媳妇管死你呢!”
“我才不找呢!冬天我跟人去西藏呢。”
“怕东藏呢!到时候想女人想出毛病来跟那个大舌头似的!”
周力把举起的一锨泥又扔到了地上,“老爸爸你胡说啥呢!”
“嗨嗨,跟小军开玩笑呢!”
房顶上的周老三周老四哥俩,随着房泥的扩展,撅着屁股,越挨越近了。原本有一搭没一搭的商量着秋后买几头小尾韩羊,听到扯起大舌头的事,便转了话题。
“那个小驴日的,该让人吊起来用鞭子抽再把皮剥了!”周老四把一团泥用抹子刮平,严严地往实抹,“老面鱼那年冬天去烧锅炉不在家。那个坏别咱的天天晚上都在外头寻着,有一天晚上吓得老面鱼的媳妇叽哩哇啦的乱喊,我和亮亮他妈跑过去一看,就是那个小杂驴日的。”
“那怕就是刚跟第一个离了吧?”
“这次那个黑蛋媳妇又回娘家了,嘿嘿,真是个杂驴日的!杂东西那年为淌水,差点把亮亮妈按到水里淹死了!”
“八成是心理变态!再不就是虐待狂!”周军插嘴说。
“你个小狲知道个啥呢!”周老三周老四又讲起买羊的事。
一色男女讲一类型,男女混合的言论就是满汉全席。
想打麻将就径直去周中林家,这是庄子里人人皆知的。
周中林实在是想不明白,自己这辈子为什么总是输。自打单干开始,开油坊赔了,贩牛捣牲口赔了,卖化肥赔了,跟人开砖窑又赔了,这些他都能承受!可是老天爷实在是不开眼,他从小抓到大的儿子,给娶了媳妇就跑得无影无踪!快出门的小女儿还被驴日的给糟蹋了!他真跟个没头的苍蝇嗡嗡地胡飞了一辈子。他脸色黑青,坐在麻将桌前,一根紧接着一根地抽,烟雾弥漫开来,虚虚实实的一团白气,由于嗓子被烟痰熏得呵啦啦的,时时都要提气咳上一咳,吐掉那口浓液。
周丽娟也是一有空就来凑热闹,双手哗哗地摸着麻将牌,新的一局又开始了,一切又有了希望,多好!她从小被姑妈领养,大了又听姑妈的话招了女婿,谁知却招了一辈子的烦恼。看个子像柱子,说话也像个人,就是啥也不想干,动不动就跑了,十天半个月的才回来。两个娃娃都十八九二十了,真不知自己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方世玉最不服气穆桂英,不就是男人在外面开电焊铺,一天烧得跟个要下蛋的老母鸡,到处呱呱叫。她有几个牙齿?输10块钱就心疼地嚷嚷,好象谁抢了她似的。
周进仪是个老光棍,哪儿人多往哪儿凑。
周老二的小子周华喜欢隔三岔五的摸上几把,稍稍赢上几包烟钱,还能跟穆桂英套套近乎,从老布鞋那儿揽点活。
杨瑞听老婆和方世玉嘀嘀咕咕地好象是说周美燕回来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鬼使神差也跑来掺和。
黎明最活跃,周中林是二爷爷,周进仪是老爷爷,周丽娟是四姨妈,方世玉是仙姑,穆桂英是富婆,跟杨瑞说话时他倒是规规矩矩地称三哥。
输赢对于周中林已经没有意义,还不及嘴里的烟有味道,辣辣地过瘾。今天周丽娟只赢了一把,周华也输得下了桌,黎明输输赢赢,恨不得扑进麻将牌里一起码。
穆桂英看到黎明打出一张八万,把牌一推,“多谢老兄弟。胡了!”纹过的眉毛和眼线黑黑地笑对着黎明背后的参谋方世玉,接着又说,“小伙子怕是想婆姨想傻了!嘿嘿……赶快去接回来,不要跟那个大舌头似的!别人的老婆再好也焐不热炕!”
“大舌头咋了?”方世玉闻出了穆桂英话里话外的味道。
“不就是让派出所抓去了呗!”
“你把话说清楚!”
“说清楚?像那种猪狗不如的东西,连自己的嫂嫂也看的眼里头,早该抓起来收拾了!”穆桂英毫不示弱,嘲笑道,“你咋还心疼这种小叔子?”
“你——”
瞧着势头不对,周华立即连拉带劝地把方世玉拖了出去。
穆桂英冷笑了一声,呼啦呼啦地洗着牌说;“婆姨离不开汉子,汉子离不开婆姨,就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女人哪,不仗着汉子给撑着,也就活得像她那样儿!养兔子卖几个钱啊?一天苦得像个驴似的!”
“林国干活也就是一忽忽都没事,一袋子稻子都抱不动!”周丽娟叹着气说,“在农村遇不上个好男人苦着呢!”
“严翠花以后还不得看林冲有没有良心!唉!怎么队上就出了这么一个畜生!”
“好象也没咋地吧?”
“谁能说得清?还不都是女人的倒霉!女人呐——”穆桂英若有所思的神情使她的面部柔和了许多,加工后的眉眼展开来也不是那么狰狞。
人与人之间说闲话,往往是没有什么逻辑,各说各的,只关心自己在意的内容——这并不防碍说话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