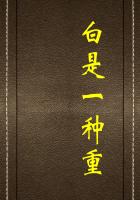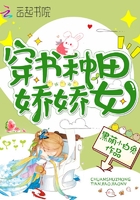1、俞平伯心中的“杭州梦”
丙戌清明后两日,由杭州归至南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俞平伯、钟敬文、郁达夫诸老有关杭州的描叙和情思。那描叙大抵是工笔的,那情思却往往是写意的。工笔的文和写意的情,让八十年后游观杭州的我,不禁重重叠叠地感慨起“沧桑”这一条“人间正道”来。
一九二五年三月,俞平伯先生在《清河坊》中,曾经表示了对伦敦、纽约等“欧美名都的忙空气”的排斥,以及对杭州以清河坊为代表的“闹热中的闲散”和“闲散中的闹热”的欣赏;三年后,钟敬文先生在致广州友人的信中,也还在嘉许着杭州的朴素、宁静和柔婉,称道着“这里虽然是浙江的省会,并且境地邻近所谓东方有名闻的商场的上海,但工商业却不见怎样发达,马路的努力开辟,也正是一年来的事……”可是到了一九三五年,郁达夫先生在《花坞》中,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有钱有势”这种社会功利对杭州民风的侵袭,不仅“花坞的住民变作了狡猾的商人”,而且连“庵里的尼媪,和退院的老僧,也不像从前的恬淡了,建筑物和器具之类,并且处处还受着了欧洲的下劣趣味的恶化”。
尽管如此,当年秋冬间,郁先生还是与胡秋原、温源宁、老龙夫妇等友好同游,尝着了西溪这“西湖近旁的野趣”;而我于清明当日,也曾与友生们行走西溪,却只是处处见着了雕琢的斧痕和人工的拙劣,恰如七十年前温源宁对西湖的批评:“湖光山色,太整齐,太小巧,不够味儿!”
此行既闻《杭州杂志》创刊,则不能无作,乃创意作此“说文解人”专栏,大抵凭文解读现代文士与杭州之笔墨因缘、人生际会,或可为湖山增色之一助,料此亦杂志不可或缺之典欤?
俞平伯先生的《湖楼小撷》、《芝田留梦记》、《清河坊》和《城站》,依次写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九二五年三月,一九二五年十月,都收录在《燕知草》(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〇年六月)中。也就是说杭州最可人的春秋两季,俞先生都曾用文字为之剪影。尽管他在《湖楼小撷》之“楼头一瞬”中,曾为自己入住杭州将近五年,对于西湖“惜墨如金”而暗唤惭愧。
至于第六个年头,俞先生笔下终于有了《芝田留梦记》,并在文章中自命为“江南之子”来:“在杭州小住,便忽忽六年矣。城市的喧阗,湖山的清丽,或可以说尽情领略过了。其间也有无数的悲欢离合,如微尘一般的跳跃着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称我为杭州人的了。最后的一年,索性移家湖上,也看六七度的圆月。至于朝晖暮霭,日日相逢,却不可数计……”
瞧他眼中的湖山,那是身在西湖之孤山俞楼才有的视角:
从右看去,葛岭兀然南向。点翠的底子渲染上丹紫黑黄的异彩,俨如一块织锦屏风。楼阁数重停峙山半,绝顶上停停当当立着一座怪俏皮,怪玲珑,怪端正的初阳台,仿佛是件小摆设,只消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挑得起来的。岭麓西迄于西泠。迤西及北,门巷人家繁密整齐……
瞧他心里的城站(老杭州人对杭州城火车站的习惯性简称),该是一个还乡青年的情怯罢?
城站无疑是一座迎候我的大门,距她的寓又这样的近;所以一到了站,欢笑便在我怀中了。无论在那一条的街巷,那一家的铺户,只要我凝神注想,都可以看见她的淡淡的影儿,我的渺渺的旧踪迹。觉得前人所谓“不怨桥长,行近伊家土亦香”,这个意境也是有的。
瞧他笔下的街市,又分明注想着多少对人情往事的怀念!
这儿名说是谈清河坊,实则包括北自羊坝头,南至清河坊这一条长街,中间的段落各有专名,不烦枚举……杭州的热闹街市不止一条,何以独取清河坊呢?我因它逼窄得好,竟铺石板不修马路亦好;认它为typical杭州街。我们雅步街头,则矻磴矻磴地石板怪响,而大嚷“欠来!欠来!”的洋车,或前或后冲过来了……我们雅步街头,虽时时留意来往的车子,然终不失为雅步。
typical的意思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如此说来,清河坊就是作者心目中杭州街市的象征了,尽管它同他处的老杭州街道,以及街道两旁的店铺一样,同样给人以“狭陋”的和“逼窄”的观感。
由《湖楼小撷》而《城站》而《清河坊》,杭州何幸,赢得青年俞平伯一而再、再而三的佳文美墨?
我注意到,作者其时正当二十五六之龄,恰是情真意挚的年岁。他精细地写了入住初居湖楼后的第一个春晨,“耳际再不闻沉厉的厂笛和慌忙的校钟,惟有聒碎妙闲的鸟声一片,密接着恋枕依衾的甜梦”(《湖楼小撷》)。我发现,他对繁闹洋场的强烈厌倦,“在上海作客的苦趣,形形色色,微尘般的压迫我;而杭州的清暇恬适的梦境悠悠然幻现于眼前了”(《城站》);我看到,他对杭州氛围的嘉许:“我在伦敦、纽约虽住得不久,却已嗅得欧美名都的忙空气;若以此例彼,则藐乎小矣。杭州清河坊的闹热,无事忙耳。他们越忙,我越觉得他们是真闲散。忙且如此,不忙可知——非闲散而何”?(《清河坊》)
然则与其说作者当日是在怀念昔日曾住的杭州,还不如说是在表达初到北京的不适应。他在《城站》里曾经遗憾地嘟囔道:“到北京将近一年,杭州非复我的家乡了。”试看《燕知草》一集中,有多少文字是“写于北京”、“作于北京”的?
你看,当时北京的大街在他眼里是“破烂的”,北京的胡同在他笔下是“荒寒的”,北京的秋叶在他心中是“打抖”的,北京小贩的市声在他耳畔是“尖厉的”,北京人的寒暄则是“车骨碌”的……
另一方面,就《清河坊》来说,与其说作者当日是身在北京,念在杭州,毋宁说他是怀念与妻子许宝驯及其女友在清河坊踩马路的种种美好旧光阴。
我以为,也许正因为有了“我俩和娴小姐同走这条街的次数最多,她们常因配置些零星而去,我则瞎跑而已……在这狭长的长街上,不知曾经留下我们多少的踪迹”的生动情节,才终于建构了如此浓厚的情结:“若我们未曾在那边徘徊,未曾在那边笑语;或者即有徘徊笑语的微痕而不曾想到去珍惜它们,则莫说区区清河坊,即十百倍的胜迹亦久不在话下了。”
难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知俞氏甚深的朱自清先生于清华园寓所灯下,在《燕知草》序中说:
杭州是历史上的名都,西湖更为古今中外所称道;画意诗情,差不多俯拾即是。所以这本书若可以说有多少的诗味,那也是很自然的……但“杭州城里”,在我们看,除了吴山,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像清河坊、城站,终日是喧阗的市声,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居然也能引出平伯那样怅惘的文字来,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
其实也并不奇。你若细味全书,便知他处处在写杭州,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不错,他惦着杭州;但为什么与众不同地那样粘着地惦记着?他在《清河坊》中也曾约略说起;这正因杭州而外,他意中还有几个人在——大半因了这几个人,杭州才觉可爱的。好风景固然可以打动人心,但若得几个情投意合的人,相与徜徉其间,那才真有味;这时候风景觉得更好……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写这本书的感兴,其实也在此。
在文中,朱先生还指实了俞先生的“意中人”,那是“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就这几个人,给他一种温暖浓郁的氛围气”,甚至连那《塔砖歌》与《陀罗尼经歌》,看上去好像在发挥着“历史癖与考据癖”,其实,“也还是以H君为中心的”。
实际上,除了“好静的”但“平日兴致极好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H君和他的一家小儿女外,还有杭州家中堂会席间邂逅的C君呢,这女士可是“曾颠倒过我的梦魂”(《芝田留梦记》)的可人儿呢。
青年俞平伯,原是多情的骚客呢,多愁善感的“江南之子”呢。何况,“江南二月最可怜,家家芳草当门前;当门前,离离欲齐行客肩……朝朝中酒年年病,人到来年忆此年”(《江南二月》);何况,“明日的人儿等着呢,今日的你怎能不去!”(《清河坊》)何况,“追挽已逝的流光,珍重当前之欢乐,两无着落,以究竟将无所得也”……(《燕知草·自序》)
那么,能说俞平伯的杭州情结,不是眷恋人情之结么?而眷恋人情,或即追挽自己将泯的童心和未尽的春梦,也未可知呢。如此说来,多情的俞平伯之于《红楼梦》读而研,研而读,引曹雪芹为前尘知己,实在是大有因缘的呀。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们对于《红楼梦辨》的作者,或者也当作如是观。
2、“红楼书梦”
对于俞平伯来说,在其清暇恬适的杭州梦境里,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旧书梦”。不过,这个“旧书梦”虽然造就了他斐然的学术声名,可也曾演绎了他人生的梦魇。
俞平伯始读《红楼梦》,是在一九一二年,大约十二三岁的辰光。据说一九二〇年,他与新潮社同人傅斯年同船前往英国,一路上就曾剧谈此书。淋漓的兴味,竟至将漫长海轮的寂寞和疲劳消解了不少。可他从学术上来研究此书,却是从杭州开始的。
一九二一年八月,俞平伯在杭州完成了《〈石头记〉底风格与作者的态度》一文。当年八月八日,他致顾颉刚函中还表达了应该“办一研究《红楼梦》的月刊”的想法。原来他在杭州的旧书摊上,买到了一部百年古书——清嘉庆十年刊《红楼复梦》,又在城站一家书铺购得六册《读〈红楼梦〉杂记》,这些为他的《红楼梦》版本校勘和考证工作提供了条件。为此,他用了三四个月的功,完成了三卷十七篇的《红楼梦辨》,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出版。
钱大宇先生在《俞平伯与杭州》一文中议论说:“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真正的起步工作是在杭州进行的,在杭州购得的两种书无疑对他的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不妨说,这也是杭州书摊给了他的机缘。”
三十年后,即一九五四年九月以后,中国文艺界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严厉批判。由此到翌年五月,国内主要报刊发表的各种批判文章和座谈纪要多达一百三十余篇,这其中还没有包括毛泽东那封信和俞先生本人的检讨。据杜渐先生在《访俞平伯谈散文》中说:“俞老成了批判的对象”,可他“挨批了那么久,毛泽东那封信他从没看过,直到‘文革’时报上发表了这封信,俞老才恍然大悟。”由此,则当年“政治批判”的荒唐性大略可知。
又据蒋和森先生《记俞平伯》:“当时的报刊上,俞平伯的名字几乎随手一翻便可见到,真是看得很熟了。”当他于一九五六年秋,调到俞先生所在的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工作以后,才发现他“很少发言,说起话来也好像有点结结巴巴的,似乎不擅辞令。他看上去像个老夫子,穿一身中式布衣布鞋;身材较矮,但脑袋却很大。白发萧疏,神态豁然,一副平和冲淡的样子。除了那副眼镜和沉静的目光透露出一股书卷气以外,实在看不出他还有秦淮荡舟的名士风流”。
根据当时官方的说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为了批判“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而针对胡适的批判,主要是为了肃清“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以群在遵命而写的《建国十年来的文艺思想斗争》中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及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则除了解决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国人民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对我国文化艺术的曲解和贬低,以及对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的诬蔑和虚无主义态度之外,还开始接触到了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时期的世界观改造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据说,直到一九八六年一月,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俞平伯举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六十五周年纪念会时,他才破了自己立下的“家里家外不讲《红》”的规矩,开始发表自己的新心得。当年底,香港三联书店和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还曾联合邀请他赴港“谈《红》”,颇为轰动。而此前他用于遮挡的妙语常常是:“毛泽东那封信还在,我怎么讲《红楼梦》呢?”
这三十二年不“讲《红》”的老例,想想都叫人痛心。
无独有偶。周汝昌在回忆他当年求学于燕京大学期间的顾随老师时也说,当全国掀起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运动”以后,顾先生也是从此“再也不提《红楼(梦)》一字”,而他“把《红楼梦》分以十大方面来深细论析赏会”的写作计划也遽告中止,“我向他请讨已经写成的部分,亦置而不答——我一直无法知道已写成了多少,皆作何语,只能怅然‘想像’。”并随后附注云:“‘文革’抄没先师手稿书物,皆堆于楼道空处,无人管理,经过之人随手取去作废纸使用,或加撕扯……”
以世界之大,反例亦曾有之。牟小东在俞平伯去世之后所写的一篇悼念文章中说:“我是在平伯先生受到批判之后,才开始阅读他有关红学研究的着作而且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认为平伯先生的研究着重从《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深刻的艺术辨析,探索了《红楼梦》的内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俞平伯自然更是在劫难逃。
对此朱寨在《俞平老的书生气》中记述道:“刚被揪出的那天,也曾让他跟其他人一样去扫院子。他拿着扫帚不知怎样使用,像追赶小鸡一样,拿着扫帚追赶那些飞飘的树叶纸片。不论监管人员怎样训斥,怎样示范,都不管用。因此,只让他单独留在楼上,擦抹那些桌椅。他做起来倒是非常认真。他颤微着碎步,拿着抹布,在那些桌椅间蹀躞不停……他擦抹桌椅并不挨着次序,都是这抹一下,那擦一把,像在画布上涂彩抹改。抹布也很少洗。经他反复抹过的桌面,反而留下一道道污痕。”在那荒谬时代,他的“书生气”,还有更绝色的一幕:
惩罚性的劳动使人疲惫不堪。但不让去劳动,在楼上静候听命,更加难受。这意味着,不是要拉出去示众,就是要有人来批斗……(一天)经过反复踢打折磨,最后非让他自己承认是“反动权威”不可。但他承认“反动”,却不承认“权威”。他坚持说:“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说得非常诚恳,完全是出于虚心,却被看作是“顽固”(朱寨《俞平老的书生气》)。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铁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凡是到文学研究所去的,总要“参观”一下大名鼎鼎的俞平伯。有一次,来参观的红卫兵严辞质问俞老:“你是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俞老诚惶诚恐地回答:“反动则有之,权威则不敢。”小将们顿时大怒:“你还不是权威,你还敢翻案!”俞老遭到痛斥以后,才多少明白一点,谦逊哪怕真诚,也得看看对象(石越《忆俞老平伯二三事》)。
对此,当时陪跪一旁的朱寨,后来满怀敬意地议论道:“谦虚原来不是随声附和,不是俯仰顺从,不是好好先生,而是理性的顽强”,他说自己由此对于“书生气”有了新的理解,原来正是这种“书生气”,在延续着人类的“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在“文革”初,俞平伯家里的书籍和资料全部被抄没。朱寨回忆说:“即使处于生死攸关的逆境,他对知识的崇敬追求之心也丝毫未懈。他对书籍有一种酷爱。当时一切书籍都被查封,他在打扫房间时,见到什么有字的纸片,他都珍惜地拣起来阅读揣摩。在什么也不能阅读的时候,他便默诵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