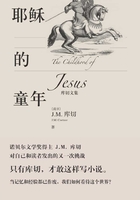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能吃过头饭,不说过头话”这句千年古训,今日在赵玉虎身上应验了。
三年前,当上访专业户万老六告他告得最凶的时候,他曾在赵家坪全体村民大会上有恃无恐,得意洋洋地说:“咱们村有人不自量力,下至乡政府,上至党中央,把我告了个遍,可结果怎么样?他还是他,我还是我!实话对你们说吧,想把我姓赵的送进大牢,没门!我赵玉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行的什么都坐过,就是没有坐过监狱;国宾馆的钓鱼台、香港澳门的五星级大酒店、还有中国的、外国的豪华别墅,什么都住过,就是没有住过牢房;黄金的、白银的、镶钻的什么都戴过,就是没有戴过手铐!”可是眼下,这个不可一世的村霸,监狱也坐了,牢房也住了,手铐也戴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当他第一次迈进岗哨林立、高大森严、前边划着三道警戒线的铁门时,当他在看守所五号院值班室被例行公事的管教干部抽去腰上皮带、搜去身上现金、手机、银行卡时,当他看到监所围墙上高高的电网和背枪的武警来回走动时,当他被塞进一间不到十平方米、又矮又暗、脚汗味、尿臊味熏得人几乎窒息的班房时,当他看到同号比他先到的六个杀人犯、强奸犯、小偷、流氓用狼一样的目光,不怀好意的直盯他、审视他时,他才真正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无奈、懦弱和悲哀。
此时此刻,他想起一个伟人说过的话:“没有经历过监狱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命运对他还是不错的。
就在他被放进普通监室还不到一小时,正被同号几个老资格的人犯搜身、欺侮的时候,看守所所长周小鹏回来了,他在值班室发现了赵玉虎的名字,便立即向公安局长刘一浩电话汇报。按照上峰指示,他亲自给赵玉虎从五号院调到一号院,并安排在一个单间。
虽然也是监室,虽然面积同样不超过十平方米,但朝阳,通风,干净卫生,里面放了一张单人床,一张简易办公桌,一把木折椅,桌上还放着一摞报纸和杂志。
根据周小鹏的吩咐,管教还给他搬来一捆啤酒,一包香肠和一箱方便面,接着又送来一个暖水瓶,一只茶杯,一筒高级茶叶和碗筷。并说他如果想吃别的,可以随时吭声,让勤杂人员到外面去买。
管教还告诉赵玉虎,他这个监号白天不锁门,他除了睡觉,看报纸外,还可以随便到院子里活动。
这在监狱来说,已经是绝无仅有的待遇了。
赵玉虎看着这一切,心里有几分得意。
但这种优越感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被一股莫名的恐惧所代替。
他平时习惯了主席台、镁光灯、吃盛宴、坐轿车、听惯了颂歌,住惯了豪宅,过惯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腐化生活。行有“大奔、”洗有“桑拿”、出门前呼后拥,身边美女如云。
如今身陷囹圄,虽然刘一浩和周小鹏法外开恩,将政策用到极限,承担了很大风险,为他提供了应有尽有的便利条件,让他享受到了监所中的贵族待遇。但这里毕竟是与世隔绝的牢笼,自己毕竟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囚犯。此时此刻,他才真正理解当初造字的先哲们,为啥给“囚”字的定形是口中有人。把人放在密不透风的四堵墙里,出不去,跑不了,这不就是‘囚’吗?俗话说得好,能当人上人,不为阶下囚。如今既然论为囚犯,那就成了人的另类。白天还好熬一些,他想坐便坐,想躺便躺,不想坐不想躺就到院里溜?,到值班室和看守下棋,到厕所看蛆虫上墙,或者趴到每个监号铁门的瞭望孔上看“人犯”们打架斗殴,听他们侃些低级下流的闲篇。最要命的就是夜晚。当刺耳的熄灯哨响过之后,他这个单间也和其它囚室一样,铁门被“咔嚓”一声挂上一把大锁。他也必须按照监规躺到床上,钻进被窝里,哪怕你睡不着,也不能有任何响动,必须忍受这无穷无尽的寂寞。
四周静得可怕,整个监所像一座巨大的坟墓,感觉不到一点生机。只有高墙岗楼上探照灯的白色光柱,不时的在每个铁门上扫来晃去。偶尔夹杂着几声值班警犬的狂吠,令人毛骨悚然。
赵玉虎丝毫没有睡意,他睁大两只眼睛,借着从铁门瞭望孔射进来的一线月光,死死盯着墙角的天花板出神。
那里有一个比洗脸盆小一些的蜘蛛网,上面网住了一只硕大的绿头苍蝇,这只倒楣的苍蝇拼命扇动翅膀,想挣脱网丝的捆缚,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它渐渐地安静下来,不再反抗,不再挣扎,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越胡思乱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胡思乱想。他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开始感到沉寂和孤独的可怕,接下来便是对自己前半生辉煌与罪恶的反省。
他用两天来在监号里学习的法律条文,对照自己过去的行为,的确不少地方都构成了犯罪。偷税,贪污,行贿,强奸,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如果法院数罪并罚,那么不死也得无期徒刑。
一想到自己后半生很可能要在监狱里度过,便害怕得浑身发抖。他开始认真回想,究竟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事情咋能发展成这样。他终于发现,一切厄运都是从筹建黄河炼铁厂开始的。强占杨发才的果园,对杨发才的人身伤害和非法拘禁,三号矿洞的塌方,杨发才的猝死,杨凤霞等人的集体上访,朱光哑和朱光富兄弟的举报,外地民工们的罢工,因拖欠工资引起的诉讼等等。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赵玉虎一步步把对方逼上梁山,同时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细细想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钱”字。他真有点后悔,我他妈的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自己已经有一座小铁厂,两个石膏矿,一个石料厂和一个汽车队,每年纯收入近百万,手里的存款已达八位数,五辈子也花不完,为啥还要挖空心思,不择手段的去挣钱?
此时此刻,他恨透了钱。是钱害了他,是钱让他利令智昏,六亲不认,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想起三年前在省政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著名学者,七十多岁了还头发乌黑,牙齿完好,看上去比五十多岁的人还精神。他向他讨教养生之道,老者只是微微一笑,漫不经心的说:“我能有什么绝招呀?只不过一辈子随遇而安。”当他又问起老人的处世哲学时,对方道:“我一贯坚持四好原则:钱够花为好,房够住为好,车能坐为好,饭能吃为好。尤其是钱不可贪多,钱能富人,也能害人。”当时他对老学者的宏论不以为然,认为他是挣不到大钱就说钱不好,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酸。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人家高明。这一夜,赵玉虎始终没有合眼。也就是这一夜,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悔恨交加和彻夜难眠。然而就在这一夜,安宁县又发生了一起流血事件。一贯不务正业的陈东东因在歌厅和地痞争一个小姐而大打出手,最后用刀将对方捅死。案情本来并不复杂,只是凶手比较特殊,是检察长王彪的外甥。当刘一浩听完副局长孙永胜的汇报后,高兴得眉飞色舞,连眼睫毛都跳动起来。
他拿出一瓶陈年老酒,又从冰箱里取出几盘凉菜,幸灾乐祸地对孙永胜道:“来,咱们喝上几杯。这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不转天转,天不转人转,这一回,不怕他王彪不上门求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