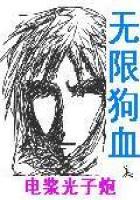那天夜里,欧阳钊被抓走以后,就被直接带进了大牢,关在一个又脏又臭的黑屋子里。屋子又脏又臭,更不通风,漆黑一片,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不时还有红眼的老鼠从脚边跳过。欧阳钊的身体被沉重的枷锁禁锢着,根本就动弹不得。
一个从小生活优渥,养尊处优的人,一下子被扔到这样的环境,欧阳钊第一反应是恐惧,第二反应是很恐惧!那一刻,他好想大喊,想大哭,想叫救命!
但欧阳钊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安静的呆着,任内心千军万马,还是做出平静的样子。因为他知道就算是喊了,哭了,黑暗也不会消除,老鼠也不会跑掉,身上的痛苦也不会减轻半分。
呆了一会儿之后,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欧阳钊看了看周围的环境,不禁一阵苦笑,其实还是看不见更好一些,看清楚了更会觉得难受。
欧阳钊闭上眼睛,把心情调试到随遇而安的波段,然后努力调整了一下身体的角度,让刑具带给身体的痛苦减轻些。靠着潮湿冰冷的墙,欧阳钊的大脑也在不停地运转,他想不明白发生这一切的缘由,后来他也懒得想,只是焦虑不安,还有些愧疚的情绪让他没办法平静下来。
欧阳钊早就听妈妈说过,在这个世界上,让你病的人,给不了你药,给你药的人,舍不得让你病。在乎你的人,风吹草动也心疼;不在乎你的人,坟头草动也无声。
欧阳钊被捕快戴上刑具的时候,忍不住疼得大叫了一声。可转头看见赵敏启像头发了疯的狮子一样,拼了命往自己身边奔,即刻就被几个大汉打得满脸是血的时候,欧阳钊就顾不上自己疼了。他奋力挣扎,他大声呼喊,甚至求饶,求他们不要打赵敏启,求赵敏瑞不要冲动,不要因为自己受到伤害。
此时此刻,欧阳钊的脑海里全是刚才的情景。欧阳钊着急地想:区叔要急死了,爹要急死了,二婶更得急死了……二婶估计还在哭吧?
被捕快带出门的时候,二婶抱着静静追到了大街上,离自己最近。哭着叫自己的名字,求押送自己的捕快放了他,求他们轻着点,别伤了他。
欧阳钊被她叫得心都碎了,他好想安慰二婶,可被人拽着,转不了身,被木伽禁锢得更不能回个头。
静静怕是给吓坏了吧?那样的哭声他从来都没听过,那一声声叫着二哥哥的声音,如夜莺啼血般让人心碎。
静静别害怕,二哥哥没事,一点都没事!二婶呀,你别追着我跑了,你快带静静回家吧!这话他当时好像说了,可她们好像根本就听不见。
还有哥哥,哥哥怕是得发疯了!好在大爷和二叔拉住了他,可那都喊劈了的叫骂声,还有脸上流下的血痕,让人不放心啊!
欧阳钊越想越后悔,当时为什么不跟哥哥说,别着急,别冲动。就算被杀头,不也得等秋后吗?但你这个折腾法儿,要是让人给当场打死了,我怎么办……
就这么胡思乱想着,身心俱疲的欧阳钊竟然睡着了。
醒的时候,天已大亮。光线从高高的气窗射入,让这几平米的囚室有了一线生机。
欧阳钊吃力地动动麻木的身子,浑身叫嚣的疼痛让他有些受不住。好几次都直接摔趴在地上。脸贴着肮脏污浊的地面,欧阳钊强忍着没有吐出来。各种无法形容味道直接往他的鼻子里灌。狼狈不堪地坐起身,大口大口地吐着气,欧阳钊又怕又委屈,但还是不断安慰自己,一切都会过去,要坚持,一定要坚持。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来了两个衙役,劈里啪啦地打开牢门,二话不说拉起欧阳钊就往外走。麻木的身体突然遭到如此粗暴的拉扯,立刻反抗起来。欧阳钊痛得叫出了声。
说时迟那时快,两个衙役中高的那个,抬腿照着欧阳钊的小腿肚子就是狠狠地一脚。毫无招架之力的欧阳钊平扑在了地上,脸都戗破了。就这样,那凶恶的衙役还不依不饶地又踩了他两脚。
“小兔崽子!还敢叫唤!就这小样儿还当乱党,打不死你!”
剧痛!痛得眼泪都差点飙出来,但欧阳钊却咬紧了牙关,再也没吭一声。一边挣扎着爬起来,一边暗暗地鼓励自己:“男子汉流血不流泪,不能让坏人看自己的笑话,要坚强。”
虽然步履蹒跚,但还是少年欧阳钊却没有被击垮。那股子异于常人的坚韧在那一刻被全部激发了出来:人可以被打败,但永远不能被打垮。
……
赵宅。
都中午了,所有出去办事的人都没有回来。
赵敏启、易晓刚、秦氏、区叔呆在堂屋里,如热锅上的蚂蚁。
一大早秦氏就把静静送到了易家,让孙氏代为照顾。孙氏心里有愧,根本不敢去赵宅,如今有了这么差事,简直求之不得。
回到家,秦氏就亲自张罗午饭,早早地就弄好了摆在堂屋。
在秦氏的心里,这桌饭其实不是为了吃,张罗它,其实是用来计算时间的。
区叔在家坐不住,一个人上街大伙又都不放心,易晓刚的工作就是给他当全陪,实在呆不住想去哪儿,就有易晓刚跟着。
无头苍蝇般的乱转的一上午,俩人沮丧地回了家。盼着看见出去跑关系,搭救欧阳钊的人已经回来了,却只看见一桌子饭菜,和跟他们同样心情的秦氏。
三个人互看一眼,叹口气,话都懒得说。
然后就是赵敏启回来了。
电报局一开门,他就把加急电报发出去了。没去学校,直接赶到厂子里,忙忙叨叨安排了给客户出货,然后就在车间忙活,看见活就抢着干。结果全是帮倒忙。
欧阳钊被巡捕房带走的事,伙计们都知道了。少掌柜的失常的表现大伙都理解。所以也就由着他折腾。
赵敏启干得浑身大汗。原本想用消耗体力的办法,来缓解巨大的精神压力,结果却是毫无用处,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喘不过气来了。眼看到了中午,赵敏启放下手里的活,就往家里奔。
过了一夜了!又过了一上午了!钊钊的事办得怎么样了?钊钊怎么样了?!昨天区叔给他熬的药他没来得及喝,他的咳嗽的是不是厉害了?钊钊特别爱发烧,这通折腾之后,会不会又发烧了呢?如果发烧了,如果今天巡捕房还不放人,那怎么办?
赵敏启没进过大牢,可二叔进过!呆了不到十天,放出来的时候,是他们用门板给抬回来的!二叔身体多棒啊!竟然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月!钊钊只有15岁,又不强壮,那么个小身板,如果被人欺负,用了一样的刑,怎么办?!
赵敏启的脑子始终在动,动来动去却全是“怎么办”三个字。行走在路上,他觉得自己的视觉听觉都乱了,被“怎么办”三个字搞乱了,好几次竟然不知不觉地撞了墙,撞了树!
一回家就往堂屋奔。屋里的三个听见动静又一次都往门口涌,看见是他,又失望地退回各自的角落。
饭菜如同不被重视的道具,摆在饭桌上,早已没有了新鲜的色彩,可怜巴巴的,象垂暮的老者,散发着衰败的气息。
大门终于又响了了,几个人再一次同时奔了出去。
这次回来的是赵培荣和易勇。
四个人的眼睛都亮了,死盯着他们俩看,想从他们的脸上看出希望。
赵培荣和易勇俩人是在大门口遇见的,一上午的奔波,让二人疲惫不堪。
听着两个大伯子说话的声音都哑了,秦氏连忙给他们到了茶水,然后站在一边,紧张地盯着他们,生怕漏听了一个字。
赵培荣端起茶杯一饮而尽,然后盯着易勇。
“那这么说,这事肯定跟道上的人没关系?”
易勇的腿越发的显瘸了。赵敏启和易晓刚懂事地过去扶着他坐下,又把秦氏沏的茶给他放在旁边。易勇连点头的空都没有,急着跟赵培荣说:
“应该能肯定。该见的我一个没落下,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咱家在大直沽也算是有名有姓的,这些年也没得罪过人。几个大哥都说,他们不可能找咱们的晦气呀!”
赵培祥一脸的焦虑。
“巡捕房逮人走的时候,说是有人向衙门举报的,咱们家钊钊是乱党,那是谁呢?”
易勇喝了口水,继续说:
“不过他们也都表示,即使不是他们做的,也会帮咱们打听。我给他们留了茶钱,也说了,办成事该怎么谢怎么谢。”
听到这里,区叔忍不住插嘴。
“可是找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呀!如果他有心陷害,也不会这么快就改口啊!赵老爷,易爷,咱们还得想办法,尽快啊!小少爷从小体质就比常人弱些,经不起一点折腾啊!”
区叔说话的时候,赵敏启忍不住点头。刚才易勇说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样不是不行,可那得等到哪辈子呀!
好几次他都差点喊出来,如果要等十天半个月,要是钊钊受了跟二叔一样的折磨,钊钊会死的!
但他不敢说,大爷的腿都拐成那样了,爹的嗓子都哑得快没声了,自己再说火上浇油的话,太残忍了。
赵培荣什么都清楚,什么都看见了,但他也只能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