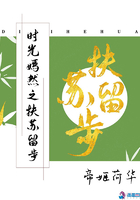筱敏
这是一个陈旧的比喻:树。
我们生活的城市,已经很少东西与人的生命本质相关或者相似,所幸还可以看见树。我非常喜欢林子里蒸腾着潮气的老树和幼树,喜欢高崖上兀立挺拔,成为某种标志的松树或柏树,喜欢在田边村头,洒些许古老的荫翳的榆树或槐树。但还有一种树,因为时常相对,它们进入我的感觉更深一些,那是在城市的逼仄中仍然不死的树,它们大多营养不良,而且时常被粗暴地修剪。
等待一棵树的长成需要时间,等待一个诗人的长成同样如此。这种时间不能以流水线上的计件标准来计算,甚至沙漏也不行,这种时间是看不见的。
一棵树只长它的遗传密码注定了的那种叶子,一个诗人只按照他心灵的质地写诗。风,雨,虫灾,干旱,斧斫痕,工业废气……可以使某一季的叶子肥硕或者枯瘦,使某些叶子残缺,畸形,从而被认为丑陋或被认为病态美,但其本质的构成是不变的。无论如何,松针不可能像垂柳那样倒挂下来,使悬岩上的风看起来柔软。
诗的生长,告诉我们一些很朴素的事情。心灵的感知方式是很朴素的,创造的使命也是很朴素的,就像在燧石上敲击出火花,就像叶子在枝头萌生伸展。我怕读那些很华美很玄妙的诗论,因为在那样浓重的烟霭里,一棵树很难呼吸。我愿意承认那里有许多智慧,但我不承认智慧可以成为诗的本质。
事实上,我们肯定会遇上秋风的季节,满树繁茂一夜之间被扫落净尽。我们生活的时代总会过去,我们的青春总会消逝。那些曾经与阳光和月光都靠得很近的叶子是无力抗辩的,泥土自然会融解它们。幸运的诗人会有一两片叶子恰好被岩层选择了,这未必是那棵树上长得最漂亮的叶子,更未必是那片森林中最出色的叶子,但恰好是它飘落在被选择的位置,从而被岩层拓印下来,成为记载某个时代的化石。
被选择或被遗弃,这很偶然,也很无理。但我所知道的一个事实是:有一些叶子即使适时地落到了最有利的位置,也还是不会在岩层上留下痕迹,比如那些滤去水分便没有自己的形状的叶子。而最终保留下来的,必然是有骨骼的。我们所见过的树叶化石,总是叶脉清晰,甚至比翠绿多汁的时节更清晰,这是树叶的骨骼,岁月使它显现出来。凭藉这个,我们感知它生动的姿态,感知远古的诗人心灵的本色。
我想,我已经学会了等待。在等待中,我明白,诗是一个进入内心的事实,而是否倾泻在纸上倒在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