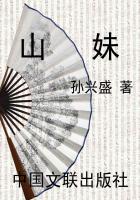当我们在为不能实现卑微的欲望而痛苦时,文学让你看见,在这种卑微的欲望之后是无法回头的人生,而这种用过激方式实现的人其实比没有去做的人更痛苦更可怜。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是我们永远不必尝试的,只要远距离地观察就好。文学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实现了灵魂的冒险而同时不必为这种冒险付出代价,它使你看见每种可能背后的真相。创作是为了表达对生活的理解,虚构文学更多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和存在意识,而阅读正是为了强化这种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文学不能清楚地判断历史,但它力图揭示历史、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它从根本上不是去寻找答案而是更感性地提出人的生存问题。
即使他们给社会开药方也只是发泄对现实生活不满的情绪,而不具有可操作性,认清这一点的人才可能由写手变成作家。所以在表征现实的时候,有人揭示生活内部的难点,有人展示表面显而易见的冲突。这也最终形成了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学,即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但好的文学总是在揭示现实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2)揭示此刻的真实
我们始终在寻找像真实一样的虚构作品,因为文学不仅给我们观看现实提供了多种视角,还给现在提供了一些解释。读者在虚构中看到自己,看到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为认识自我提供了诸多参照。《红楼梦》在开头虚构“木石前盟”的姻缘,在一个神话背景下来讲述现实的人生故事。这样我们仿佛不仅看到了现实,还看到了现实的根据,寻找现实背后的原因。虚构一个过去和将来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所以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故事时能够信以为真。正因为有从西方灵河岸边的绛珠小草,到现实世界中的多情才女,再到太虚幻境中的芙蓉仙子的变化,我们才理解了黛玉,理解了她一生的情感。
于是,无数人在林黛玉这样的女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或者说看到了一种更真实的自我,这就是文学。我们经历最多的是现在,我们无法逃离的也是现在。那么现在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文学给人提供一种更加情感化的理解,也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因此,文学也是最容易感动人心的艺术形式。
(3)追问永恒的真实
艺术可以以虚构的方式对真实情境进行重构,那么我们可以借助文学还原生活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艺术只是为永恒真实提供一种假想。诺瓦利斯说“愈有诗性,就愈加真实”(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3页。),反过来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说越是真实的就越没有诗性,因为真实便丧失了超越与唯美。而文学是借助现在追问永恒,如歌德所说,“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产生一个更高事实的假象”(【德国】歌德:《诗与真》,《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页。),这个高于事实的假象就应该是生活发展的必然性。布洛克也说,“文学真实的特殊性,表现在它从某个角度向我们提出了一种关于真实世界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有时是荒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真实也就是艺术的‘意义’。……
合乎现实世界的真实仅能证实我们观看世界的某种方式是否符合事实,艺术真实则向我们宣示应该如何去观看这个世界”(【美国】H·G·布洛克:《现代艺术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文学以追问永恒的方式直指人的心灵,探讨的是关于人的终极关怀。因此,执着于解决此在问题的作品必定在关于永恒的价值追求上有所欠缺。
可见,虚构的现实不仅揭示了现实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还揭示了现实存在的依据,更重要的在于它暗示了现实的发展趋势,从而具有未来性特征。这一切使文学中的现实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从而令人产生关于真实的幻觉。也是凭着这一点,文学能够以更直接的方式贴近人的情感,从而改变人们对现实的看法。
三、让理想呈现的媒介
充当“让理想呈现的媒介”是文学表征现实的第三种途径,其基本意思是说,人们通过阅读和写作文学可以唤醒心中的理想。这种理想可以成为珍藏在心中的一方永恒的净土,也可以是努力奋斗的目标,还可以是人们借助文学对不可能实现之梦的替代性满足。总之,文学通过对现实的虚构,唤醒了人们心中沉睡的理想。而且它还借助虚构把这个理想表现得有声有色,仿佛跟真的一样。文学和其他艺术一样关注美关注理想,但是它呈现美和理想的方式却有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在艺术的几大门类中,绘画雕塑以线条呈现,是非常直观的。音乐舞蹈以声音形体来表现,是附着于形式的。
而文学表现的方式却是语言,要把握也只能靠想象,语言不能给人以直观的印象却能够淋漓尽致地呈现美和理想。
比如同样是呈现理想,它可以呈现理想的方方面面和前因后果,这是其他艺术形式力所不及的。其特点在于它对于人类理想的满足具有体验性、游戏性和无限性。具体来说,文学可以书写不在场的在场感,也可以预演理想生活,还可以体验可能生活。
(1)不在场的在场感
人类生存首先是借助虚构进入精神状态的。虚构作为一种人类行为,起源于前艺术的原始公社时期,原始人的一切意识和行为都涂抹着虚构色彩,人们通过虚构与外界建立联系。而物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不仅通过虚构与精神世界发生联系还以虚构进入此在的生活,并且现在人类要摆脱物质生活的缠绕还要借助虚构。虚构为我们提供与现实不一样的东西,是生存之必需。虚构远离了来自主体强制的思想或是社会实用要求,把我们从琐碎的现实中解放出来,能够使我们产生一种不在场的在场感。
一方面,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文学为我们提供的各种在场体验,同时我们却可以常常保持置身事外的感觉。文学建构一种理想化的软权力,化解了现实中不堪忍受的生命之重或生命之轻,太轻太重的生活都使人无法踏实地把自己安放于此在的生命。生存需要借助虚构让我们摆脱现实生活的事实性束缚,使我们远离现实利害关系,从而走出自我所包围的物质性关系。虚构不仅可以将主体从事实性中解脱出来,并且与可能性相结合,为人的前途指明了方向,在可能世界给我们以真正存在的感觉。文学通过这种不在场的在场演示完成了人类追求新鲜体验刺激的全部愿望。
(2)理想生活的预演
当我们脱离了为物质生活而奋斗时,理想中的生活就变得更为重要。虚构既满足了内在自我的需要,又提升了人的内在自我。虚构的那些充满诗意的梦想是对生活的假想,这些假想拓宽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巴尔加斯·略萨就说,“小说在撒谎的同时却道出某种引人注目的真情,而这真情又只能遮遮掩掩、装出并非如此的样子说出来。……人们不满意自己的命运,几乎所有的人(无论是穷人、富人、天才、庸才、名人、凡人)都希望过上一种与现状不同的生活。为了(哄骗式地)安抚这种欲望,虚构小说诞生了。小说之所以写出来让人看,为的是人们能拥有他们不甘心过不上的生活”(【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虚构是对自我生活的扩展,也是对生活富于想象力的演出。伊塞尔认识到文学对人的可塑性进行无限的模仿,他指出作为媒介文学显示出的固定形态是虚幻的,它将人类所有属性具体化为一种非真实的幻象,拉长痛苦又对其抚慰。文学探索的不是个体的生活而是有关人类本性和世界存在方式的真理。所以,当人们面对现实的无意义和荒诞性无法理性言说的时候,文学便以感性的方式对其阐释。于是,只有在童话里我们才相信大灰狼会说话,尽管在现实中我们情愿避而远之。文学实现人类与其他物种不可能的交流,从而为与他们相处提供了某种参考。
然而,正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面对大灰狼的恐惧,我们才会在文学中把它们设定为邪恶的、需要防范的对象。文学始终是从自身处境出发,提出了关于未来的设想。“虚构小说描写的生活——尤其是成功之作绝对不是编造、写作、阅读和欣赏这些作品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而是虚构的生活,是不得不人为创造的生活,因为在现实中他们不可能过这种虚构的生活。……
虚构是掩盖深刻真理的谎言,虚构是不曾有过的生活,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人们渴望享有、但不曾享有,因此不得不编造的生活”(【秘鲁】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小说是进行中的生活的生动体现——它是生活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演出,而作为演出,它是我们自我生活的一种扩展”(【美国】布鲁克斯·沃伦:《小说鉴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页。),“虚构不复制生活,它排斥生活,用一个假装代替生活的骗局来抵制生活。
但是,它以一种难以确定的方式完善生活,给人类的体验补充某种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而只有那种想象的、通过虚构代为体验的生活中才能找到的东西。……虚构就已经在帮助人类(他们毫无觉察)共同生活,帮助人类适应那些来自人类内心深处的某些幽灵,以便让人们的生活复杂化,让生活充满难以企及、具有破坏力的欲望。……虚构也是一种泻药。那些在实际生活中根据盛行的道德观被压抑或应该被压抑的东西(有时仅仅是为确保生命的存在),在虚构中找到了庇护所,找到了生存的权利,找到了可以用更有害、更可怕的方式行动的自由”(【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在文学中可以拥有现实中所没有的一切,文学虚构表演性的特点能够给我们关于未来生活真实体验的感觉。生活中我们越是缺什么就越是想得到什么,文学就越是写什么。人世间最需要表演的是爱情,于是文学在无穷无尽的持续性中不停地表演着爱情的经验。文学能够以游戏的方式将人的无限可塑性表现出来,不同时代的文本就构成了人类可能世界的标本。文学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令人获得了游戏的快感。
(3)可能生活的体验
虚构行为打开了一个可能世界。也是在这一点上伊塞尔认为,文学虚构之所以具有人类学意味就因为它通过表演和游戏把那种不可能表现的可能世界创造出来了。王尔德说:“艺术是有想象力的撒谎。”(【英国】王尔德:《谎言的衰落》,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撒谎的艺术便是创作过程。将生活事件转变成艺术谎言,从而令文学具有娱乐性,审美性。正因为文学有虚构性,便会有游戏娱乐的快感,不需要直接对现实负责。文学是以游戏的方式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它只要提供予人消遣的想象就可以了。
弗洛伊德指出,“作家那个充满想象世界的虚构性,对于他的艺术技巧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效果,因为有很多事物,假如是真实的,就不会产生乐趣,但在虚构的戏剧中却能给人乐趣。”(【奥地利】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文学虽然是让人们在没有功利的游戏中得到快感,人却能在实现的可能性中拥有自我,要竭尽可能性空间,人类只有通过虚构潜在无限的变化才能得到实现。文学的人类学价值就体现在对现实世界和对自我的扩展上。被现实限制的我们借助虚构实现了超越自我的人类之梦,从生活自我向审美自我转换。
我们可以在虚构中通过暂时脱离现实,看到自己甚至看到人类的潜能以及实现的可能性。虚构的文字会激起对现实世界的焦虑,会使读者的感觉敏锐起来,在特定时代有可能转化为对现存不合理制度和现实的反抗。文学体现了人类生命的终极追求,是人类情感之归宿。
由此可见,虚构作为文学表征现实的基本方式,体现了人类关于自我,关于真实,关于理想的深刻思考,既是对现实世界的补充更是超越。
“现实表征”的现实尴尬
如今,文学在表征现实的路途中也遭遇了不可避免的困境。在越来越复杂的现实面前,以语言为符号呈现的文学遭遇了言说无效的尴尬,而这对文学知识分子回应现实的能力和方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致使文学在现实面前要实现有效言说变得越来越困难。
一、现实越来越复杂,虚构的对象难以把握
王蒙先生说:“小说之吸引人,首先在于它的真实。其次(或者不是其次而是同时),也因为它是虚构的。如果真实到你推开窗子就能看到一模一样的图景的程度,那么我们只需要推开窗子就可以看到小说了,何必还购买小说来读呢?”(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因此,“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的意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