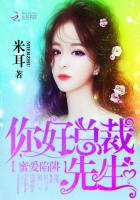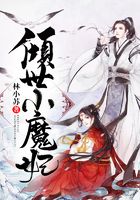读完这篇文章可以发现,张仃在说毕加索,也是在说自己。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有一句名言,叫“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用到张仃身上正合适。这种感性的、主观色彩颇强的艺术批评,其可靠性建立在批评对象与自己同质同构的基础之上,张仃与毕加索艺术人格上的接近,决定了他对毕加索的评判八九不离十,其中许多观点堪称不易之论,比如对毕加索抽象变形的那段话十分精致,与毕加索的权威阐释者、英国作家罗兰特·潘罗斯对毕加索的论述不谋而合:“对他来说,艺术与生活不能分离的,创作灵感来自他生活所在的世界,而不是来自一种理想美的理论。他的作品无论看来多么深奥难懂,但是它的渊源永远是热情的观察和对某一特定物体的热爱。它从来不是一种抽象的预测。”毕加索的变形过去一直被当作颓废的“形式主义”遭到批判,“文革”后时来运转,受到青睐,作为艺术的“形式美”被某些人标榜到极致,吸引无数艺术青年,其实都是对毕加索的误会,前者属于僵化的“庸俗社会学”,后者属于浅薄的“唯艺术论”。张仃的这番知音之论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然而,张仃在忘我地翻译毕加索的时候,也把他理想化、纯净化了,这种理想化、纯净化,无疑是张仃自己的精神写照。是的,张仃太喜爱毕加索了,喜爱到极致,难免“爱屋及乌”,甚至“不及其余”。现实中的毕加索,要比张仃心目中的毕加索更加复杂,更加混沌,在毕加索的一些作品中,善与恶,神与魔,文明与野蛮,人生探索与人生游戏,总是彼此不分地交织在一起,而他自己也不否定这一点。这无疑是彼时彼地的西方社会生活及其文化传统在毕加索心理上的投影。
正如罗兰特·潘罗斯在《毕加索》一书写到的那样——毕加索不满足只看到别人已经看到的地方,他对生活的热爱促使他追问和探究表面现象。在他的凝视下,美才被剥去了一种传统看法所制造的伪装,那种看法曾经假定了美和丑之间的一种对照,并把两者像白昼和黑夜那样区分开来。他从来不做美的敌人和丑的战士,像某些人要使我们认为的那样。
他使我们看到了美的多种多样和存在形式。……在自然界,美与丑是一对难分难解的伴侣,毕加索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表达出他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界的爱。他像米开朗基罗一样,承认自然界的规律。
毕加索对自然的爱是不受限制的,它扩大到一向为人轻视的美点上。正是在那些地方,他常常有所发现,找出具有料想不到的价值的东西。他是从泥里发掘被人遗弃财富的清道夫,他是能从空帽子里变出一只鸽子来的魔术师。他的手中生来就有一块点金石。
要说他赋有弥达斯国王的点金术,那是千真万确的……
对于张仃来说,这种善与恶、美与丑浑然一体的观念,至少在理智层面是难以接受的。张仃的审美理想,是刚健、清新、欣欣向荣,极而言之,就是真、善、美,这充分体现在张仃对毕加索的解读中。他目光所及,并且大加阐发的,是毕加索作品中健康、严肃,符合真、善、美的一面,而对游戏人生、颓废色情变态的一面则视而不见。也就是说,张仃总是强化毕加索人格中的“大我”,尽量回避或者忽略毕加索人格中的“小我”,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张仃对《哭泣的女人》的解读。张仃从这幅作品中读出毕加索对二战的“预感”,并对毕加索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灵魂创作的这幅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杰作表示高度赞赏。然而据西方美术史家研究,《哭泣的女人》的原形是毕加索的情人朵拉·玛尔,此作是毕加索对她实施虐待后画的,也就是说,毕加索不只满足于虐待,还要在艺术中再体验一次虐待的快感。
张仃与毕加索,在人格的雄强、通家的艺术风度和与民间艺术的宿命性关系上,有着特殊的默契。然而,张仃毕竟是中国人,身上还有作为西班牙人的毕加索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精神气质,那就是他的儒家圣贤气质,体现在艺术风度上,就是它的严肃性、纯粹性和强烈的人文精神。放眼张仃的艺术世界,无论他的漫画、壁画、彩墨画、装饰画、焦墨山水以及书法,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种精神内涵。
这种精神的纯粹性,在毕加索的世界里是看不到的,那是一个受“自然法则”支配,善恶相济、美丑并存的混沌世界。其实,两位艺术家截然不同的情感生活历程,足以证明这一点。毕加索一辈子追求女人无数,纵横无忌,绯闻不断,浪漫历程在其作品中历历可见,这方面为后人留下许多争议的话题,而张仃一生只与两位女性(前妻陈布文与现在的爱人灰娃)相爱相伴,用情专一,在物质生活方面,过的是近于清教徒式的生活。这与毕加索形成极大的反差。这大概就是张仃与毕加索相去最远的地方了。如果说毕加索是一个天真的顽童,天才的精灵中兼有恶魔的成分,那么张仃更像一名无私的战士,天赋的艺魂里更具中国圣贤的素质;如果说毕加索的艺术是以“真”为最高目的的话,那么张仃的艺术,就是以“善”为最高目的。
这种差异,归根结底,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需要说明的是,张仃对毕加索的理想化、纯净化中,含有更顺利地“洋为中用”,发展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策略性考虑。
事实上,张仃对西方现代绘画的关注,从一开始就抱定这一宗旨,正如他表白的那样:对于毕加索、马蒂斯“只是学习其中对发展中国绘画创作有启发的部分”,从来不搞什么形式主义。而作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家,张仃对东西方艺术近代以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趋势有敏锐的洞察,因而更加清楚中国应当向西方学习什么。张仃有过一段重要的论述:“我特别重点地研究了后期印象派画家吸收东方艺术的特点,在油画中重视线的运用,注意抓住对象的结构,减弱明暗关系等等,使得西方绘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现在回过头来,着重地研究这段艺术,就可以发现,欧洲的艺术家是如何保存他们绘画艺术色彩,外光运用的优点,而又吸收了东方艺术的长处,使西方艺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革。这段历史,对我们如何保存我们传统艺术的精华,吸收西方艺术的某些长处,是有启发的。”可惜的是,历史为张仃提供的空间实在有限,张仃对毕加索的吸收,充其量也只能停留在“形式”上,即使这样,时代也不允许。张仃以命相搏,为新中国的美术留下一道原来也许不会有的风景。他的卓绝,正体现在这里。
然而“真”也罢,“善”也罢,关键在于丰沛的艺术天赋,超常的生命能量,否则一切谈不上。张仃与毕加索都是这样的艺术家。这决定了张仃每次遭遇厄运、受到打击时,都能坚强挺立,于无声处,另辟天地,开拓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张仃的不凡在于,作为一个革命的艺术家,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艺术的立场,以自己的全部真诚与生命奉献,与这个严酷的时代保持着积极的互动,在“艺术”与“革命”之间走着一条迂回曲折的漫长之路,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左奔右突,不断地形成自己的河流,通向世界艺术的海洋。
张仃有一个令人心动的比喻:画家在宣纸上运笔作画,好比斗牛士斗牛。将笔墨与斗牛连到一起,说明了画画在张仃心目中的神圣地位,那决不是文人骚客无聊时的消遣和得意时的游戏,而是性命相搏的较量,是勇气、力量、技巧与激情的通力合作。这是何等大气的想象!中国画论里,关于笔墨的论述汗牛充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说法。张仃何以会有这样的联想?是否从毕加索那里得到的灵感(因为毕加索也是个超级斗牛迷,并且画过无数斗牛图)?我没有问过张仃。不过我敢肯定:张仃与毕加索,都体验过与斗牛相似的兴奋和快感,他们都是以画笔“斗牛”
的艺术家。
画坛怪杰——黄永厚其人其画试说
不久前,收到黄永厚签名赠送的《黄永厚画集》。我迫不及待地翻阅一过,感觉确实很是大气,很有分量,不只是形式上既厚又重,内容也称得上“厚重”;于是拨通电话,向远在通州的黄永厚表示感谢:“谢谢赠送这么厚重的画册!”
我话题一转,说:“不过,画集有三个缺陷:一、书脊没用印刷体,许多读者认不得你的草体字;二、画中跋语没加释文,读不懂跋语更没法欣赏你的画作;三、没写篇“后记”,谈谈自己作画的感想和编画的情况。”我也像扳道岔似地直来直去。
“前两条有道理,可已没法挽回;《后记》不写是因为一写就骂人,不写也罢。”
“你的画本来就是骂人的,还怕骂人?!看了画集,我想写篇文章,写你怎样骂人。”
“向你磕头了。你写的二十八宿,一个个能从纸上跳出来。”
“你是第二十九个。聂绀弩以杂文风格写诗,你是以杂文风格作画,都成了怪杰。我称绀弩为‘人间怪杰’,那就称你为‘画坛怪杰’吧。”
“我怎能和绀弩相比呢,虽然我和他都只读过小学,但他比我聪明多了。”
“都很聪明。不过,你这个人比绀弩还难写,太怪啦。”
超前的寂寞
乃兄黄永玉先生在画集序文《暮鼓晨钟八十年》中说,“厚弟几十年来的画作选择的是一条‘幽姿’的道路”,“‘幽姿不入少年场’自然是不趋附,不迎合,而且不羡慕为人了解”。(作者按,“幽姿”句出自陆游《朝中措·梅》。)又说,“幽姿不免寂寞,以至如明星之光年,施惠于遥远的后世”。哥俩虽然有时也会斗气,但相知却莫如手足,大哥真是从骨子里看透了二弟的画风。
永厚的画,岂止是“不羡慕为人了解”,简直是不想让人了解。钝根似我,自然不能完全读懂他的画,虽然喜欢他的画,却总是如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
就是当面看他作画,也是如此,不甚了然。有些人作画,不让人看;永厚不然,他不怕人看,相反,有人看,画得更来劲。所以我有幸三次当场看他作画。记得十几年前,他还住在西罗园的时候,四益兄拉着一起登门拜访,虽然初次见面,却是一见如故,谈笑风生,真是豪爽,留我们在他家吃狗肉,自己不喝酒,看着我们喝,比他自己喝还高兴。饭罢,他挥笔为我们各作一幅画。后来,我又带几位新加坡朋友去拜访。他曾到新加坡举办画展,认识华裔诗人潘受,潘曾赠送自己的《海外庐诗》和为潘伯鹰编印的《玄隐庐诗》,所以对潘受的朋友格外热情,我又看他当场作画奉赠远方来客。他迁居通州潞河时,我和两位老同学到他新居去喝酒,他搬出各种好酒,让我们任选;我们选了他大哥设计酒瓶的酒鬼酒。在喝酒过程中,他为我们三人各作一幅画,三张画同时进行创作。陪我们吃几口饭,又跑到画室涂几笔,来回不知跑了多少趟,我们也总是跟着到画室观看。酒喝完了,三幅画也作完了。我取回他赠送的画作,不知读过多少回,虽然一次比一次多懂一些,但仍是如雾里看花。四益兄和永厚文画联袂登场,合作多时,该是比我明白多多;但从他为永厚《头衔一字集》所作《前言》(《读画》)看,似乎也没读得太明白。四益兄比我聪明,尚且不能全读懂,那么广大读者和观众有几个人能看明白,也就可想而知了。
永厚是个自由职业者,以画谋生,画卖不出去,岂不得喝西北风。有一次到荣宝斋,我问在那里管书画鉴定的萨本介:
“黄永厚的画卖得怎样?”小萨回答说:“不怎么样。他的画好是好,并不比乃兄黄永玉差,但一般人看不懂,所以不好卖。”于是我突发奇想,由我做东,拉本介同永厚到酒桌上通通气,了解了解画市的行情,希望能借此打破僵局。我们就在和平里太白酒楼小聚,席上摆开龙门阵,话题的主旨却很明确,无非是劝永厚画些好卖的画。然而却远没有达到所预期的效果。
永厚回到通州后,立即来电话:“老弟,你的好心,我领情啦;但你们别劝啦,我黄某人就是饿死,也不能改!”他那凛然的气概,真让我倒抽一口冷气。这次电话里的声音长久地在我耳边回响,在我胸中回荡。我不得不承认,是我错了。我终于明白,真正的艺术家是把艺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的。永厚就是这样的人。正如刘海粟书赠永厚的立轴所云:“大丈夫不从流俗”。
但凡人之处世,落伍固然会被时代所抛弃,超前也可能寂寞一生,乃至可能被时代所湮没,真正能适应时势的识时务者,恐怕不多,也未必成为“俊杰”。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其实,孔子并非圣之时者,不然怎么会到处奔波,栖栖遑遑,累累如丧家之狗呢?
所谓孔圣,是后代才认可的。也犹如星光之施惠于后世而未被湮没,虽非时者,却是幸者。在画坛上,这种非时而幸者,国外有凡·高,国内有吴昌硕,都是典型例子。荷兰画家凡·高,是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人物,因为画法超前,以至终生潦倒,若干年后,才被世人认可,为后来的野兽派和表现派所取法,他的画作在拍卖会上竟然以天价成交;中国近代画家吴昌硕以篆书入画的大写意,直到年逾古稀,还没被世人所认可。齐白石在吴作《观景图》上所题跋语,说吴昌硕七十岁以后,“放开笔机,气势弥盛,横涂竖抹,鬼神亦莫之测,于是天下真当叹服矣。然见画而知下拜者,万人中不过一二;耳食称道者,或十之三四;骂者乃十之五六。虽再多,人无效也。”其生前知音之少,足以令人扼腕叹息;可如今连他的门弟子,也都享誉世界了。因超前而罹难而湮没者,中外古今,不乏先例。哥白尼掉了脑袋,伽利略关进牢房,这是众所周知的。英国罗素《西方哲学史》中有这样一段话:“一般讲,最早想出新颖见解的人,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以致人人以为他无知,结果他一直湮没无闻,不久就被人忘记了。后来,世间的人逐渐有了接受这个见解的心理准备,在此幸运的时机发表它的那个人便独揽全功。例如达尔文就是如此;可怜的孟伯窦勋爵成了笑柄。”孟伯窦勋爵,本名詹姆士·伯奈特,苏格兰人类学家,在达尔文之前就提出猿演变为人的进化论观点,因为超前,却成了笑料,而达尔文则成了“圣之时者”。我们不指望永厚成为“圣之时者”,但愿他不至于成为“笑柄”,也不至于被“湮没”,而是以超光速的速度,让星光施惠于当今画坛。
返祖的变异
之所以说永厚的画超前,就因为其审美观念不同流俗,走到我们时代的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