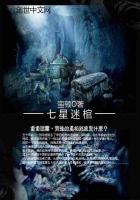我欲要休息,吕明打来电话,说省委机要局发来机密电传,路小莺已到市委机要局,马上就送我处理。我看看表,是晚11点45分,就打开纯净水机,准备泡杯咖啡以提精神做持久战的打算。每每遇到这种时刻,大多是要求连夜部署上级指令的。
大约过了20分钟,路小莺匆匆进了我的办公室,将一沓电传递过来,说吕秘书长在值班室等我指示,就站在一边等我吩咐。
我集中精力阅览了电传,就拿起电话通知秘书长,立即把有关精神传达到周边的五个县市和四个区。然后拿起笔在电传上页批道:请诸位副市长、公安局长传阅。这是有关社会稳定的一个机密信息,上级要求传达不过夜的。这时我方转过头面对站在一边的路小莺。路小莺身着一件款式新颖的米黄风衣,里边是蓝绿相间的高领毛衣,那高领一侧是一排晶莹的绿扣子。随意简单的装束,使她亭亭玉立的躯体散发着青春的生机。一般情况,待我在公文上批示后,她就取过文件夹匆匆离去,她还要照我批示的传阅名单逐个递送。这会儿已很晚了,政府除了我,还有在值班室的秘书长,其他的领导都在家里做梦了。每遇到这种时候,路小莺就不再回家休息了,机要室里边有一个小卧室,起居设施配备俱全,也是考虑到她工作的特殊情况。
“辛苦了,小莺。”这时候,我才发出一声客套的问候。
“市长才辛苦呢,深更半夜还不能休息。”
“坐——坐,小莺,咱们聊聊,小莺。”小莺听着我的话,并没有立即坐下,她有点受宠若惊。我来政府的时间不算短了,可是,与部下还是很不融合。“其实,我是很愿意与你们年轻人交朋友的,可是天天都在穷忙,没有时间与你们沟通交谈,哪里能交成朋友?哈哈,看看你连坐都不敢坐,是吧?”
我的话很有作用,她微笑着坐在了紧靠办公桌的皮椅上。
“来,你也来杯咖啡。”我去拿杯子,她却敏捷地夺去了。我把雀巢咖啡放进去,她接了热水过来,随意地说,这屋子真热。
她的话提醒了我,今天是11月15日,照政府规定,是开始送暖气的日子,政府的暖气烧得很足,天气又不是很寒,当然就显得热了。
“咳,你还穿着厚厚的风衣,能不热?哈哈。”
她信手脱去风衣,把它挂在屋门后的衣架上,就回到刚才坐的位置上。两只手抱着热腾腾的散发着咖啡豆香味的杯子,她试探性地说:
“其实,我对您很崇拜,俞市长。自从我看到《中国市长》杂志上刊登了你写的那篇文章,我就想拜您做老师。”
“怎么,我怎么记不得,是哪篇文章?”我曾经在这本《中国市长》发表过几篇小文,我深知那都是些“雕虫小技”的应景文章。
“就是今年夏天那期杂志刊登的《城市要有文化底蕴》那篇文章,真是写活了。文化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纸上行走跳跃,嬉笑歌唱,谈情说爱,温馨愉悦。那篇文章,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现在都会背了。你信不信?俞市长。”
“噢!我信——我信,嘿嘿。”想起来了,那是一篇谈城市的缔造和发展的文章,我把文化比为城市的灵魂。那篇文章着实下工夫了,也是我对城市多年积累认识的一种感悟。这会儿听到小莺的赞美,真是遇上知音了。我兴奋极了,再看她,果真可爱动人。我来雁鸣市这么久了,竟然没有认真地看过小莺一眼,眼前的她一下子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去了,我愈看她愈像早已飞跑的红粉知己欧阳瑞丽。大约是三四年前,她因故飞往了国外,从那以后,我们再没了联系。也是从那以后,我没有再正面注视过女性。我以为,没有比欧阳瑞丽再好的女人了。也许是她在我心中太完美了,无论从躯体还是心灵,从言谈举止还是风度气质。这时刻,我的眼光进入了路小莺的世界——啊,面前的她不正是飞跑的“爱鸟”再现吗?
无论是她的气质,她的神情,她眉宇间散发的一种“味道”,尽管比不得欧阳瑞丽的成熟,那是因为她比欧阳年轻吧。我终于从遐想中回到现实,微笑地说,“只是你的错觉吧?小莺啊,把这篇文章看得过高了,它没有你说得那么金贵的,哈哈。”
“真的——俞市长,我读文章时就有那种感觉。你不知道,年轻人对领导都有一种定势的看法。”
“什么看法,说说看。”
“不敢,哈——”她真的有点放不开了。她知道,我想听的是真话。她肯定也知道,说假是蒙不住我的。
“有什么不敢呢,小莺,其实我很想与年轻人交成好朋友,刚才我就说了。”
“我哪敢——俞市长,别说朋友,我刚才说了,想做学生,还怕您不收呢。哈——”
“做学生,真不敢收呀!你毕业的那所名校是重点大学,我连个副教授职称也没有,哪敢当高才生的老师?哈哈,做朋友吧,小莺,咱们就算是忘年交了,是吗?”
“那可是,我只怕不够格吧,哈——”
“相互讲真话,讲心里话,就是够格,是吧小莺?哈哈,这点勇气都没有吗?哈哈——”
“好,就说我们年轻人对当官的看法。现在的官,我们觉得都很没意思。不知道啥原因,讲起话都是那些干巴巴的官话、套话,一肚子虚的东西,假的东西。许多做官的,我们一看,就看出他们很浮躁,很虚假,很势利。走起路,都是匆匆忙忙的,都跟赶飞机航班一样。
在大众场合,连停一步、慢半拍都不可能的,别说与一般人平心静气对话了。你别笑,这都是真的。也是因为当官的走路少,距离短吧,只是从餐厅出来,到餐厅大门口就上汽车了;从办公楼下来,到办公楼门口又上汽车了;从会议室出去,到会议室楼下的出口又上汽车了。别说写什么文章了!大会上的报告呀,年终的总结呀,包括个人学习‘三个代表’的心得呀,还有一年一次的述职报告呀,哈哈,都是秘书科的人代写的。所以,我看到你发表的文章,就特别惊讶,哈——”
“你知道那文章是我写的?你不是说,做官的文章都是秘书写的吗?哈哈——”
“我知道,秘书还真写不成你那样的文章。真的,俞市长,秘书的文章也都是老套路了。
况且,你文章里有许多东西,不做市长,没有亲身体会,根本悟不出来的。只是许多市长都白做了,做了市长,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所以,我就喜欢上你的文章了。”
“好——好——小莺。”我有感而发,又兴奋起来。是遇到知音,又找到一面镜子,能照出政府官员面目的镜子,我应该好好珍藏这面镜子,应该把蒙在镜面上的灰尘污垢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应该使镜子与我之间没有隔阻,没有障碍,没有距离。
“你真是个有思想的好姑娘。小莺,我对你有个要求,从今以后,对我要讲真话、讲实话,别说那种客气话,中吗?”
“我不是讲了吗?刚才我就说了原先不敢对当官的说真话。不过,我也有个要求。俞市长,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您要认真地教我,别敷衍我,行吗?哈哈——”
显然,先前的距离已经拉近,隔膜已开始融化。她能这么直率地要求我,我很高兴。
“那当然——只要我能回答的。”
她微笑着站起来,拿起我的杯子去纯水机边添加热水,而后送过来,轻轻地放在桌面上。突然,她凝视着我的台历上的一首题名为《寄人》的小诗,眼睛贴过去,去读那文字: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有意思。俞市长,你能对我解释一下这首诗的意思吗?这可是我请教您哩,哈——”
她的军将得很是时机。这会儿我已有了兴致,就信口答道:“当然可以,但不是解释,是与你切磋。哈哈,好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此刻我和她的距离缩短得几乎没有了,我忘了我是市长。对这首诗,我很厚爱,自欧阳瑞丽离去之后,我就把它放在案头,常常以它寄托对远方情人的念怀之情。
我从笔筒取出一支铅笔,站起来指着这首七绝。小莺从桌子对面绕过来,站立在我的右侧,面庞和目光随着我的铅笔而东西左右:
“这是唐人以诗代柬的表达感情的方式。诗的题名为《寄人》,是用它替代一封信札。诗人曾经与一位姑娘相好,而后来不知何故又分了手。”
小莺的身躯不知什么时候已紧贴在我的一侧,她柔嫩的面庞与散发着清香的鬓发不时地摩擦或碰撞着我的面孔。我不知是在解说纸上的诗句,还是在对早已飞走的欧阳瑞丽倾诉衷情。
“他们为什么要分手?”小莺好奇又认真地问道。
“这正是诗人留下的悬念。小莺,懂吗?”这时,我把她拉到身躯的左侧。这样,我右臂的挥洒空间更宽松了。此刻,我不自觉地伸出左臂轻轻地搭在她柔软的颇有弹性的左肩上。只有真正的少女,才会使男人有这种感觉。此时的小莺像一头温顺的小羔羊,她的躯体贴在了我的左侧。我感觉出来,一种感情潮水开始涌动了。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可能会发生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压住心头的烈火,压住炽热的火焰,讲下去:
“诗人对离去的姑娘深深眷恋,不能忘怀。那个时代不像现代,是不好直接痛快地倾吐爱情心声的,只好借用诗的形式以寄托对情人,不,是对恋人的炽热情爱。单看这诗,小莺——”
我有些激动得讲不下去了。因为我的面前只有一名听者,又是如此漂亮的女性。久别的欧阳瑞丽,在这深更夜半,她那一双专注深情、热烈渴望的眸子射出的光芒,已变幻成我心中的指挥棒,心灵的乐曲欲要随那指挥的手势奔腾跳跃抒情叹息……
蓦地,我似被什么惊醒,方发现站立的两个躯体已靠拢无间,我的左手不知什么时候已搂住她的腰肢,她的脸蛋正轻轻地搁在我的左肩上。我慢慢地抽回了左手,镇定一下情绪,方把自己拉回到诗的世界:
“诗是从一个梦境开始的。诗人大概在姑娘家停留过,对那里的曲径回廊都寄予着深深的恋情,爱屋及乌嘛,这样,诗人在梦中又走到了这方当年定情的地方——”
“俞市长——你讲得真好,比语文老师好多了,真的。”不知是诗句打动了她的心,还是她对我的偏爱。但是可以肯定,她的话语是发自内心的。我看着一双燃烧的“火眼”,那是心灵的窗子,比什么都透明,此刻的向往,此刻的欲望,已被诠释得淋漓尽致。心中的波涛被一种力量推动起来,一时间,整个躯体晕晕欲醉、飘飘然地升腾出一种欲望。不,这种欲望一直被压抑着,压抑使它不得不潜伏下来。然而,只是那么一瞬间,我下意识地走了出来,拉住她的手从办公室走进了里间。许是我的大脑还醒着,它提醒我得马上换一种状态。我们在通往卧室的小房停住了,这里一侧放着一个长长的沙发,沙发对面的墙上镶嵌着一方高大的镜子。每当我从卧室出来,或从办公室进去,都要在这方镜子前边照一照,看一看自己的仪表、衣服,我是市长,我不能使自己的仪表不端、衣服不整。我们并肩坐在沙发上,这时她已满头是汗,我也汗流满身,是暖气太足,也是心情激动吧。我脱去了外衣,只留下贴身内衣了。室内的温度太高了。我示意她,嫌热就脱下毛衣,这样谁都不再说话。我们静静地坐着,整个政府静谧得像一个金色的梦幻。
“俞市长……”
好久之后,她发出这样的呼叫。
“小莺儿……”
“我——我怕——”
“噢——我知道——”
电话突然响起来,深更半夜,不是有突发事件,是不会有电话的。又是我的加了密的那部座机。我从沙发上滚下去,走过去抓起听筒:“啊!一兰,干什么?这时候来电话,出什么事了?”
“没有事!只是我的左眼一直跳,从晚8点跳到现在。我怕你那里有什么事,你不知道,我的左眼跳可灵验了,一跳就有事。”
“没什么事,睡觉吧。”
“没事就好,俞阳,没事就好!休息吧。”妻子的这个电话一下子叫醒了我。
一瞬间,我想了许多,和小美,尤其昌,还有许多许多……
“是大姐来的电话?”她很聪明,她把我妻子称大姐,而不称嫂子。
“是的,是你大姐的电话。这么晚了,还乱操心。”我抱怨着,心绪又有点乱,“她说她的左眼一直在跳。唉,女人啊!”我不知所云地说。我们不再说什么了,屋子与凌晨的夜空一样静默。就这样地静默了足足一刻钟。
“你在想什么?”小莺看着我,终于耐不住这种寂静。
“我在想,怎样处理这种关系?既能成为知音,又要光明磊落。”
“这很重要吗?”
“很重要的,小莺。处理不妥,危险啊!”
“处理好呢?”
“当然好了,不仅是无话不谈、无事不说的知音,更重要的是能天长地久,友谊与爱慕长青。”
“我听你的,俞阳大哥。”
“注意!小莺,千万不敢在大庭广众下叫大哥。哈哈——”
“那可不敢说,叫顺嘴了,说不准啥时候就滑出了嘴,哈——”
我拉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她穿好毛衣、风衣,我郑重地说,“路小莺同志,今晚什么也没发生,懂吗?什么也没有,去机要室休息吧,祝你做个好梦。”
她凝视着我,两只眸子射出两道炽热的光,打在我的面庞上。我没有说话,同样凝视着她。她终于说:“我懂——俞市长,放心吧。”
她轻轻地闪出了屋门。机要室在三楼的那一头,现在整个三楼只有我和她醒着,那个小通讯员早已进入梦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