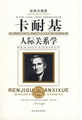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来了。风暴也吹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郭沫若也受到了震荡。
过去,他对北洋军阀政府还认识不清,现在,他终于看清了它的面目了。原来它是一个卖国政府,与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中国要独立、要富强,首先不是什么振兴实业,而是首先要推倒这个腐败的卖国政府,赶走侵略中国的列强,脱胎换骨地独立自主地重新创造。
他在想:“学医有什么用!我把有钱人的病医好了,只会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榨取穷人;我把穷人的病医好了,也只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受富人的剥削。学医有什么!有什么!像这样我宁肯饿死!”他决定放弃医学,转向文学,用文学去拯世道、救人心。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是使郭沫若走向新诗的第一步。1916年泰戈尔访日,日本的泰戈尔热达到白热化。沫若又继续读了他的《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王》和《加皮尔百吟》等诗集,深深被他那种清新的诗情所吸引,好像探得了生命的清泉一样。每天一下课,他便跑到幽暗的阅览室里,捧书面壁默诵,感受着诗美的欢悦,涅槃的快乐。
但是,当他读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后,又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惠特曼那种雄浑、豪放、不拘一格的诗风,震撼着郭沫若的灵魂,这更合于郭沫若的性格。他个人的郁积,中华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一个喷火口,也找到了一种喷火的方式。他心中的烈焰和溶岩,立时化为斑斓、灼热的诗的篇章。他歌颂旧世界的叛逆者,歌颂革命领袖: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这就是他的《匪徒颂》。他诅咒旧世界,诅咒一切邪恶势力: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凤凰涅槃》
他歌颂地球,歌颂这位伟大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
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知你爱我还要劳我,
我要学着你劳动,永久不停!
地球,我的母亲!
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
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
《地球,我的母亲》
他眷恋祖国,他要为祖国燃烧自己,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唯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炉中煤》
他用文学的生命力去唤醒国人,以新诗的感召力为这个时代呐喊。他把这些诗搜集成册,以《女神》为名出版。在该书的《序诗》中他说: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的问世,震动了当时的文坛,拨动了“五四”时代一代青年的心弦,开创了中国的新诗时代。郭沫若也因此成名。
1920年4月,郭沫若决心休学和成仿吾一起回上海创办纯文学杂志。经过3天海上航行,船进了黄浦江口,沫若那欢快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啊,祖国,你的儿子回来了!”
他看着那晴朗的清晨,看着那淡黄色的黄浦江水,看着那海鸥一样的白帆船,看着那两岸漾着青翠的柳波,他的诗潮澎湃了。几年来他所渴望的故乡,所苦想的“爱人”,终于见到了。他头脑中形成了这样一首诗:
和平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岸草那么青翠!
流水这般嫩黄!
我倚着船栏远望,
平坦的大地就像海洋,
除了一些青翠的柳波,
全没有山崖阻障。
小舟在波上簸扬,
人们如在梦中一样。
和平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可是,当他愈朝前进,他眼中那幅美丽的风景画,渐渐改变了模样。嫩黄的水变得浑浊肮脏,煤烟、纸屑到处飞扬,香烟广告,接客先生,乞丐样的码头苦力,黄包车夫,还有那耀武扬威的高鼻子洋人成了一个大的垃圾箱。在街上,满眼的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都呈现着营养不良的烟火色。那些汽车、电车、黄包车,怎么看也好像似一些棺材。沫若的眼泪又不禁地流了出来。他写道:
我从梦中惊醒了!
幻灭的悲哀哟!
游闲的尸
淫嚣的肉,
长的男袍,
短的女袖,
满目都是骷髅,
满街都是灵柩,
乱闯,
乱走。
我的眼儿泪流,
我的心儿作呕。
我从梦中惊醒了。
幻灭的悲哀哟!
他带着一种失望的心情,进入了上海。
1921年6月,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人发起、组织了“创造社”,出版了《创造季刊》。这是中国文艺园圃中的一朵鲜花,是中国浪漫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
1923年,郭沫若出版了他第二本和第三本诗集《星空》和《前茅》。由于中国革命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也逐渐摆脱消极影响,克服那种低回的情绪和虚无的幻影,看到了光明。
1924年,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傍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他感到,过去那种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个人自由,未免太狭隘了。他说:“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他认识到现在是两个阶级血淋淋斗争着的时代,只有推翻反动统治,推翻黑暗社会,才有大多数人的自由,大多数人的个性;也才有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于是,他在文学上便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他主张文艺应是“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郭沫若在上海南京路上,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凶横残暴,激起了他无比愤怒。他曾为“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起草了一个《五卅案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面目,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认为中国人若不想沦为亡国奴,非反对帝国主义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