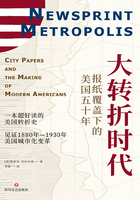不速之客
优秀的人物永远不会被历史的潮汐湮没,尽管历史的潮汐起伏不定。
若干年前某日,和唐振常先生一起出席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要话题,是上海的历史。唐先生对上海的近代史了如指掌,会上,他谈起20世纪初一位上海实业家资助教育的事迹。这位实业家在发家之初,便很慷慨地向北京大学捐银5万两,资助一批年轻学子去美国留学,而且言明,不需要任何回报,只要一条,要选送培养真正的人才,学成后报效祖国。得到他的资助留学后成才的学者中,有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周炳琳、汪敬熙等。这些学成归来的学者出于感激,也为了纪念,又集资设立以这位实业家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第一批得到奖学金的学生中,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这位上海实业家的名字,叫穆藕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穆藕初这个名字。对这样一个有品格有见地有魄力的人物,我很自然地产生了兴趣。会后,我向唐振常先生打听,能不能找到有关穆藕初的资料。我想了解这样的人物,了解上海的历史乃至中国的现代史,大概会很有收益。
后来有一天,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打电话来。他在电话中用上海本地口音自我介绍道:“我从外地来。我姓穆,叫穆家修。我的父亲是穆藕初。”在电话里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很震惊。在我的印象中,穆藕初是上一个世纪的人,他如果健在,大概有120多岁,他的儿子,想必也是垂垂老者了。他从哪里来?怎么会找到我?还没有容我表示惊讶,这位穆先生已经在电话里回答了我:“我从唐振常先生那里来,听唐先生说,你对我父亲的事迹很有兴趣。我手中有一本介绍我父亲的书,想送给你。”
半小时后,穆家修已经坐在我家客厅里。他比我想象的年轻,虽然白发满头,但神态和声音都不见老,脚上一双白色运动鞋更使他显得精神健朗。他赠我的书是《穆藕初文集》,厚厚一册,是他和经济学家赵靖、叶世昌一起主编的。其中有穆藕初50岁时写的自传《五十自述》,还有他的不少论述经济、企业管理和文化教育的文章和书信。有这样一本书,就把穆藕初的事迹和言行大多记录下来了。
我和穆家修的话题当然只有一个——关于他的父亲穆藕初。穆家修是穆藕初的幼子,他原是东北的一位气象工作者,一位科学家,和他当实业家的父亲干的是完全不同的行当。穆家修很感慨地告诉我:“以前,我并不了解我父亲,只知道他是大老板,还当过国民党的高官,他的经历给了我‘官僚资本家’这样一个家庭出身,这个家庭出身曾经压得我几十年抬不起头。我当年想的是如何和这样的家庭出身划清关系。”在编父亲文集过程中,穆家修访问了很多了解他父亲的长者,阅读了所有有关他父亲的文字,穆藕初在他心目中有了一个全新的形象。“想不到,我父亲竟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为国家做了这么多好事。”虽然只是三言两语,然而我能理解,认识上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在精神上对他的震荡有多么巨大。值得庆幸的是,迷雾已经消散,历史人物终于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实业救国
穆藕初是上海浦东人。他的祖父在浦东种棉花,他的父亲开过棉花行。后来家道中落,穆藕初曾到棉花行当学徒,当小职员,饱尝人间辛酸。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落败那年,穆藕初19岁,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耻辱使他痛苦不已,决心求西学,“有朝一日能与他国竞争”。他用工余时间上夜馆学英文,后以流利的英文考入上海海关当办事员。在接触西方文化、开阔眼界的同时,他也深感当一个国家丧失主权的贫穷中国人的痛苦和羞耻,于是发誓要以“实业救国”。在经历了很多坎坷周折后,他终于在1909年那年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那年他34岁。在美国,他攻读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五年后得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他依靠先进的科技和科学的管理,成功地建设了德大、厚生、豫丰三个大型的纺织厂,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纺织工业家。在发展工业的同时,穆藕初还创办了中华劝工银行、上海纱布交易所,并经营着大规模的棉种试验场。当时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经这样评价他:“在自己本身和工业这两方面的建设性进步中,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大王要想超过穆藕初的这个记录都是值得怀疑的。”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了穆藕初的企业管理思想和方法后,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或者想做的,正是穆藕初当年提倡实行的,他是中国企业科学管理的先驱。”把现在很时髦的“开拓者”和“改革家”这样的头衔给他,实在是当之无愧。穆藕初在创建工厂、企业管理这些方面的作为,可以供经济专家研究后写出专著来。
然而穆藕初的人生目标不仅仅是当一个实业家。他为的是“救国”。如何救国?他用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穆藕初认为,国家要富强,重要的前提是要提高人的素质,要大量的人才。而要提高国民素质,培养真正的人才,则必须注重教育。一个不重视教育、没有优良教育的民族,决不可能是一个进步、强盛的民族。穆藕初对教育的赞助,可以说是倾尽了心力。在“五四”运动前夜,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为此捐巨款。他无偿捐银5万两给北京大学送学生赴美留学,在当时曾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举动,无论是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还是对那些急功近利的政客,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育。上海的位育小学和位育中学,在开办之初,也曾得到他无私无偿的援助。教育成功的试金石,在于能否培养有用之才。穆藕初在《惜人才》一文中这样说:“国无人才,国将不国,才而不用,或用违其才,非爱惜人才之道。”“人才为国之元气,惜才为培养之原。”穆藕初一生爱才如命(不是爱财如命!),他捐巨资送优秀学子出国留学,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他选择人才的标准,也是不拘一格。当年出资北大资助学者留美,在挑选留学者时,他不主张用死板的考试,而是请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三位学者推荐,不限地域,不限学科,只要道德、学问、能力诸方面都出类拔萃,得到这四位大学者认可便通过。结果选送的五位学者果然都是第一流人才,其中有经济学家,也有法学家和文学家。令人感慨的是,穆藕初出资送人才出国留学,不求任何回报,既不要他们为自己评功摆好,也不要他们回来后为他工作,连一个谢字也无须说。只要他们学成后报效国家和民族,便算达到了目的。穆家修给我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次,穆藕初收到企业中一个年轻的勤杂工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向穆藕初借阅有关棉纺工业技术的书籍。第二天,穆藕初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会见了这个小勤杂工。他问神情紧张的小勤杂工,为什么要借这些书。小勤杂工回答,想自学。穆又问:你为什么不去上学?小勤杂工答:家里没钱,只上到初一,便辍学来当学徒了。穆藕初想了想,说:“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小勤杂工一惊,以为老板要解雇他。穆藕初笑道:“放你三个月假,你准备一下考高中吧。如果你能考上,不要担心学费,都由我来负担。”三个月后,这位小勤杂工很争气,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南洋模范中学高中部。第一个学期结束,穆藕初检查了他的学习情况,发现他的各科成绩优异,便决定在第二年暑期后送他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七年后,这个年轻人在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归国,成为闻名世界的经济学家。这位勤杂工出身的经济学家,就是方显廷。方显廷感激穆藕初的知遇和提携培养之恩,毕生把他奉为恩师和慈父。穆藕初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然而他还是对中国的艺术情有独钟,琴棋书画,他都有兴趣。李叔同、冯超然、吴湖帆、俞粟庐、吴瞿安这些当时活跃的艺术家,都是他的朋友。在中国的艺术中,他最喜欢的,是古老的昆曲。然而他的喜欢,决不是富豪的附庸风雅,也不是普通票友的痴迷,在中国的昆曲艺术家们的心目中,穆藕初是一个响亮而亲切的名字。他喜欢听昆曲,也学着唱几曲。在剧场里,他却和一般的观众不一样,除了听戏,他还关心着这个古老剧种的未来。他发现,唱昆曲的演员都是鸡皮鹤发的老伶工,而且听众寥寥,一片惨淡之相。如果不培养新人,这古老的剧种必定难以为继。于是,他在1921年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由他出钱,为昆曲大师俞粟庐(俞振飞之父)录制三张唱片,使一些传统名曲能够传之于后人。在出唱片的同时,还印制昆曲的唱词和曲谱。第二件事情,由他投资,创建昆剧传习所。为了办昆剧传习所,他先联合江浙两省的昆曲名家,组织“昆曲保存社”,然后由他亲自张罗,在上海发起昆曲义演,这样既能为昆曲传习所集资,又能在社会上扩大昆曲的影响。那时昆曲在社会上已没有多少影响,上海的戏院都不肯出租给昆曲班子。穆藕初便亲自出马,来到英大马路上的洋商戏院“夏林配克”(即后来的新华电影院)。外国经理认识这位大名鼎鼎的“棉纱大王”,当然很客气。他向穆藕初要演员名单,穆藕初回答:“我自己就是演员。”外国经理一听有这样的名人上台,便答应出租戏院。义演时,穆藕初真的自制行头,袍笏登场,和项馨吾串演《辞阁》和《拜施分纱》,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台演出。那年,俞振飞21岁,在义演中演《断桥》中的许仙。义演连续三天,观众如潮,场场客满,上海滩掀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昆曲热。在穆藕初的全力赞助下,昆曲传习所终于办了起来。传习所办在苏州城西大营门,占地五亩,所有办学费用,都由穆藕初承担。传习所招收了70个从十岁到十五六岁的小学员,由名家任教。在学唱昆曲的同时,还教他们学文化。这些学员,后来成为昆曲艺术家中承上启下的“传字辈”,他们是昆曲得以维系流传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这个传习所,没有这一代新人的培养,昆曲完全可能在中国失传。俞振飞在怀念穆藕初的文章中曾这样说:“我国戏剧自清末皮黄崛兴,昆曲日益式微,经先生竭力提倡,始获苟延一脉,至于今日。”传字辈的昆曲艺术家们则发出如此感叹:“热心昆曲,使此一线不绝如缕之雅乐,不致湮没失传者,舍我穆公其谁!”我相信,这样的赞辞,是这些受惠于穆藕初的昆曲艺术家们的心声,穆藕初受之无愧。
独留清白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衡量,穆藕初绝对是富豪和大款。而他在资助教育和文化时,也确实挥金如土,不知吝啬为何物。然而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个极其俭朴的人。对私人的花费,他锱铢必较。在当纱厂总经理时,他的月薪有400多块大洋,然而他每月的伙食费仅控制在6元,从不过一日奢侈的生活。在穆家修的记忆中,他的父亲身上老是穿一件旧长衫,总也不换新的。那是抗战时期,弃商从政的穆藕初从上海到了重庆,他当过国民党的工商部常务次长,后又任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是部长级的高官。然而他过的是简朴的生活。有人觉得他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老是穿一件旧长衫和他的身份不符,劝他做几件新衣衫。穆藕初却不以为然,他说:“国难未已,抗战还没有胜利,我怎能奢侈?”一直到他在重庆患病去世,也没有换一件新衣服。正如他的老朋友黄炎培所语:“黄金满筐,而君萧然,不以自享。”我问穆家修,他父亲有什么遗产留给他。穆家修笑道:“什么遗产也没有,我们兄弟姐妹中,无人经商,也没有一个是富翁,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这也是父亲的愿望。他把自己的钱都花在了他认为该花的地方。”
其实,穆藕初的财产,在他生前就差不多已经散尽,这些钱财,千丝万缕地融化在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中。这样千金散尽不传家人的实业家,在中国又有几人?穆家修告诉我,他的老家在法租界的太原路襄阳路口,并不是什么豪宅,他就在那里出生。现在,穆家的老屋早已拆除,被改建成一所地段医院。那地方离我现在的住所很近,我经常路过那里。那所新建的地段医院面貌新颖,很漂亮,而穆家旧址,却再也无迹可寻了。
穆藕初是在抗战后期逝世的,他逝世后,国内各界都对他作了很高评价。1943年9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在头版上发了这样的消息:民族工业家穆藕初先生逝世。消息很短,却对穆藕初的一生作了精辟的总结,不妨抄录如下:“实业家棉纱巨子穆湘玥(藕初)患肠癌不治,于19日上午6时,在陪都寓所逝世,享年67岁。穆氏早岁毕业美国农工专科学校,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沪创办新式纺纱厂,改良技术产品,注重员工福利,实行三八制,并以私蓄资送青年出国留学,设藕初奖学金,为国家作育人才,沪人称棉纱大王,而自奉菲薄,布衣素食,待人和蔼亲切,对青年爱护培植,竭尽心力。抗战后,主持农产促进委员会,创七七纺纱机,三十年出长农本局,卸职后即以体弱多病闻。”在这条消息的旁边,还配发了报社的短评《悼穆藕初先生》,对他的逝世深表哀痛。在雪片般的悼诗和挽联中,董必武挽联引人注目:“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浑浊日,独留清白,堪作楷模。”我想,这也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为一个爱国实业家作出的最高评价了。
穆藕初有言:“世人咸知获利难,不知有钱而能施用于正当之途为更难。”这“正当之途”,就是如何对国家和民族有益。他已经用卓有成效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这句话。
穆家修先生赠我的《穆藕初文集》只印了1000本,能够读到这本书的人大概不会很多。不过我相信穆藕初这个名字不会在历史的海洋中消失,他不是飞扬的泡沫,而是坚定的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