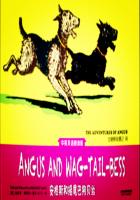下午上班以后就听到了安高管的消息。消息说,今天上午没来上班的安高管今早被人发现昏迷在一块西瓜地内,身边还发现了几件女人的胸衣底裤之类。消息传得神乎其神,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传消息的人脸上都溢满了幸灾乐祸的神情。安高管在单位按理说人缘不坏,可当他落难后天维的人也居然会这样嘲笑他,这让我感到一阵心寒。刚来到天维时认为的平等公正的环境原来只是一种表象,而真正的现象实体比我尽最大可能想象到的还肮脏。不过司徒堂和法医的栽赃也十分到家,这一切似乎做的天衣无缝,面对这种事情,安高管为保全名誉计,肯定不会报案,我们也就相对的捡了个便宜。
半个小时后袁源走了进来。他的脸上保持了寻常的镇静,看不出有什么情绪波动的迹象,但皮鞋敲在地上紊乱的声音还是折射出了他心里并不好受。他径直走到办公桌前,放下了公文包。在这个习惯性动作前他问了我一句:“小张,今天上午没人找过我吧?”我答道:“没有。”他点点头,不再说话。
正当他在桌边坐下来,准备开始下午的工作时,门口忽然想起了敲门声。我站起身为来客打开了门。门口站的竟然是老徐。他表情激动,一张红润的脸涨得发紫,额头上条条青筋毕露,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情绪这么不稳定。他见到我之后,勉强点点头:“小张,董事长在么?”
袁源已从自己的办公桌旁站起身来:“呦,老徐来了!”
老徐瞅见袁源,也不说别的,大踏步走了进来:“董事长,你要是不愿意我干的话尽可以直说,干嘛用这么卑下的手段?”我听他说话的语气不对,便悄悄退了出去。其实凭借这一句话,我已大致猜出了他为何而来,甚至想出了那个为他提供消息的人。但我却不能在这个时候进行劝服,否则两方面都会对我有相当大的意见。最近据可靠消息说老徐的小舅子是市委秘书长的司机,在他面前能说上话,别看老徐平时蔫了吧唧的,到关键时候还是有几分能量的,袁源对这种事并不能太过张扬,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叫别人去瞧热闹。
站在门外我仍然能清楚地听见老徐大声吼出来的语调:“怎么回事?哼!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不是最清楚不过么?你与爱荷达公司签订的那个合同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就打算亚城那边的事落空好看我笑话?!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你越是着急想赶我走,今儿个我还偏偏不走了!”听到这里,我很奇怪老徐为何连这都知道了,转念一想也不奇怪,美国一位社会学家不是做出断言“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与人最多只隔了六个人么?”也就是说,只要你找对了人,你朋友的朋友就有可能是希拉里的亲戚的朋友,反正不会这中间经过的人不会超过六个。更何况是在通讯极为发达的本市。听到这种激烈的措辞,袁源却仍然用平静的语调道:“公司与爱荷达一向没有经济上的往来,这点你是清楚的。你听到的那些纯属谣言,我劝你也不要太当真。对于你做亚城置业的买卖公司一向是大力支持的。你看,公司在资金如此短缺的情况下还拿出进货款让你投入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么?老徐呀,干什么不要那么冲动,制造谣言是要受到处罚的!”虽然在门外,我仍然能想象得到袁源的悠闲。但我知道,他此时的心情没那么轻松,安高管的事件对他的精神引起了很大刺激,不说别的,单从公司实力派的纷争上面来说,安高管是袁源的铁杆,只要他有一个星期不来袁源所处的位置就要受到别人的威胁。老徐或许正是瞅准了这一机会才敢到这里扑腾,但袁源故意装出的平和一定也很让他生气。
老徐也不再多说,走之前撇下了一句话:“咱们董事例会上见。”他的这句话用意是很明显的,天维公司实行董事制,如果有两人或两人以上提出申请要撤换董事长,那么董事局就要考虑全体董事的意见,以便做出适当的考虑。老徐的用意就在于将袁源彻底的挤出天维公司,达到自己称霸天维的目的。确实,现任公司高层中,也只有老徐才有资格上这个位置,他是这个公司的元老重臣,很多人都是他从基层上一步步提上来的。用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他群众基础很好。
袁源却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此刻高声叫道:“小张!徐总要回去了,你开着我的车去送送他。他年龄大了,理应多受到些照顾。”袁源很熟悉我的性格,知道我在这个时候一定不会走远。我于是也就大踏步地走了进去。老徐听到袁源的这句话,回过头去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一字一顿地道:“我现在还不想回去。”其实袁源这句话的理解应当是“你这个老不死的,以后在公司中少管我的事。”但老徐也不是善茬子,别看他平时不声不响,关键时刻还真能做得了主,跟袁源当场顶撞起来。
袁源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可是他习惯于将微笑表现在脸上,平时并不太严厉地批评别人,所以老徐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得很被动。
但这样也绝不意味着袁源会在这件事上绝对占据主动,因为老徐所说的公司董事例会毕竟不是虚构出来的。天维的董事十三四人,倒有八九人是老徐的旧部嫡系,亲戚故旧,想跟袁源过不去简直太容易了。但既然是例会,就必然有它的弊病。例会是每月的一号召开。今天是7月7日,这个月的例会刚刚开完。董事局不会因为老徐的一个请求而单独为他加一次会,所以老徐想要扒拉掉袁源至少也得等到8月1日。
袁源在几天的时间内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举动,满脸仍是堆满了笑意,在员工间跑来跑去监督工作,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喊他称号的人少了一些,另一些人喊得时候底气也不十分足。袁源浑不在意,每天就是呆在办公室内工作。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他叫我开车带着东西去医院探望了一下安高管。安高管没受什么皮肉之苦,只是受了些精神刺激,但这已足够他疗养一段时间。趁袁源不注意,我从侧面打探了一下主治医师安高管近来的表现,知道他们并没了解到刺激物,只是用普通的心理疗法在治疗。我心里暗暗佩服司徒堂,这件事可真办的滴水不漏。
在平静中度过了几天。12日的午后,天气十分闷热,从十七楼望下去,高速公路像条死蛇一样瘫在大厦下方,明晃晃地反射着太阳的炽热,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虽然办公室的空调已被我调到了20摄氏度,可我还是能查觉出空气中的不安和躁动。袁源今天中午有事出去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打开靠背椅,半倚在椅子上,打算闭目休息一会儿。
正当我有如此想法的时候有人敲门走了进来,竟是李部长。自从那天我去过他家里以后,他虽然一再坚持说那个工人不应该被开除,但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相信这样的结论:那个小个子工人已经彻底地毁了他的前程。虽然处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想要再往上爬很难了,但他肯定也不希望丢掉现有的位置。早在那天在大鸿源医院,我就看出来了。而那天在他家里,他更是求着我为他多想想办法,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从侧面试探了一下袁源,他是坚决想要撤掉这个对他不忠实的人。我知道袁源向来做事说一不二,言出必践,任你怎么活动也是无济于事。而且,从安高管那里得来的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不过有一点是袁源不该忘记的,他也是董事局的董事之一。
看见他有些落寞地走进,我将他迎了进来。他瞥见董事长座位上的缺失,却没有说什么。我见他一双愤懑的目光只在袁源的座位中踅来踅去,担心他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来不好收场,于是问道:“李部长还是为上次那事来的吧?”他冷哼一声:“上次?什么事?”我知道他不愿再提,也就没有多问,对他道:“您是来找董事长的?那您坐一会儿,我去给您泡杯茶。”对于他这种非实权人物,我仍然不敢太过开罪。天知道哪棵大树下面可以乘凉!
他的目光从袁源桌上那只美仑美奂的玉龙上面收了回来,用拉长而讽刺的语调道:“不必了,不见他正好落得个心地清净。你回头告诉他,就说我跟老徐站到一根绳上去了!”说着将胳膊向后用力一甩,连声招呼也没有打便气哼哼地走了。
李部长这人我熟悉。他这人纯粹直率,一根肠子通到底,为人热情,就是有时做事有点欠考虑,也是人们通常说的那种“胸无城府”的人。他被抬到今天的高位上,不是依靠运气,也很少有个人能力的成分,倒是他那一帮受过他恩的穷哥们硬把他给架了起来。他的群众基础好,对高层领导的有些命令就敢于抗旨不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单位中反抗最激烈的人之一。他今天的到来,火气并不是冲我来的,这些我再清楚不过。接下来我该考虑的问题就是,我是否应该把这个问题报告给袁源,如果报告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