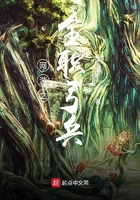“我要做的正是证明本案存在合理怀疑,”萨拉坚持说。“在我看来,这两个证人的证词,加上布罗迪本人的证词,确实构成了合理怀疑。”
“嗯。”穆克基法官若有所思地听着,然后翻看桌子上的文件。萨拉和菲尔·特纳站在法官面前,讨论着辩方证据是否可以采纳。桌上的文件是两个证人——环保斗士曼迪·凯特和护士伊恩·金克斯——提供给露西的证词梗概,萨拉打算传他们出庭作证。
经过长时间的劝说,曼迪·凯特终于同意在她所谓的“猪猡法庭”上证明,在贾斯敏被杀前两天,布罗迪和她有过激烈的争吵,在她被杀当天的早晨,布罗迪威胁着要收拾她。凯特还会指出她有一次和贾斯敏一起时曾经被人跟踪,那人可能是西蒙,但同样可能是布罗迪。
护士伊恩·金克斯是拉里和艾米丽找到的证人。他准备在庭上证明布罗迪与贾斯敏交往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心理变化:起初,布罗迪兴高采烈,欣喜若狂,然后日益担心忧虑,因为他开始怀疑贾斯敏仍与西蒙见面。据金克斯所言,贾斯敏被杀当晚,布罗迪显得恼怒沮丧,无心工作。而就在下班离开之前,他曾说想“将某人的脑袋割下来”,表现明显异常。
“法官大人,我这位博学的朋友只是想利用这两个证人来指控布罗迪,”菲尔·特纳坚持说。“这和他的儿子清白与否没有直接关联。”
“这话有几分道理,”法官低声说道,“纽比夫人?”
这话不仅有道理,而且一语中的,萨拉很清楚。而这恰恰就是她想做的。她要解决的问题在于菲尔说的后半句——这两个证人和西蒙的案子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法官大人,他们的证词紧密相关,”萨拉急切地说道。“这场审判就是关于我儿子是否谋杀了贾斯敏·赫斯特这个问题。如果我能证明凶手可能另有其人,那么这显然就是陪审团应该考虑的证据。如果布罗迪可能杀了贾斯敏,那么我儿子就可能没杀她。本案就存在合理怀疑。”
菲尔皱着眉头,“如果你能提供布罗迪与本案有牵涉的可信证据,合理怀疑才算存在。但目前为止,没有证人证明他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任何地方……”
“你也没有证人,”萨拉反驳道。“没人看见西蒙出现在尸体附近的任何地方,但布罗迪就住在距离尸体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
“是的,但我们有法医证据,精液、运动鞋上的血渍和刀子……”
“菲尔,我在盘问中已经对血渍和精液作出解释了,这你是知道的。”
“那只是你的一家之言,”菲尔干笑着。“这要看陪审团是否相信你的说辞。话说回来,布罗迪有什么理由要杀她呢?”
“当然是出于嫉妒!”萨拉急切地看着法官,“这个女孩脚踩两条船,他们都有理由恼羞成怒。控方解释西蒙杀死贾斯敏的原因时,全凭这个动机,也就是性嫉妒。那么这两个证人恰恰证明了布罗迪有同样的动机——实际上,他们可以证明他的嫉妒心比西蒙的更强烈。控方并没有证人指出西蒙曾经威胁要将她的脑袋割掉……”
“但西蒙打了她,不是吗?”菲尔插嘴说,“在众目睽睽之下。”
“是的……好吧,西蒙打了她,但有人看到布罗迪冲她大喊大叫,还发出威胁……”
“但不一定是在威胁贾斯敏,”法官指出。“我读了金克斯先生的证词,布罗迪好像是在威胁要割掉西蒙的脑袋,如果他真有这个意思的话。”
“法官大人,我们并不清楚他在威胁谁,”萨拉绝望地说。“我只想请求传这个证人出庭,菲尔可以尽情盘问他。一切都交给陪审团来裁定。”
“特纳先生?”法官交叉双臂,身体靠向椅背。
“法官大人,我朋友的热切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总的说来,我认为她的理由不充分。这个审判是要裁定西蒙·纽比是否有罪,而不是其他人。如果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表明布罗迪到过案发现场,那么为了公平起见,我会同意将此证据向陪审团出示。但现在没有这样的证据。萨拉提出的证据仅有动机之说,坦白地说,这证据不够充分。依我看,布罗迪也许是真心爱这个女孩,为她的死而伤心欲绝。在缺乏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若继续指称他就是杀人犯,似有违反诉讼程序的嫌疑。另外,也是相当残忍的做法。”
萨拉内心的希望在破灭。“但我有证据,法官大人。证人的证词和对他盘问的记录……”
穆克基法官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了。“纽比夫人,这些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我同意控方的观点,两个证人的证词和被告西蒙·纽比的行为以及是否有罪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因此我要将他们排除在外。”
萨拉对此无能为力。她起身离开,穿过大街,回到了事务所,看到露西一手握笔,一手拿着奶酪三明治。
“运气怎样?”她询问道。
“不怎么样。”萨拉厌恶地将假发套扔掉,“还没开始抗辩,就失去了一半的证据。”
特里和哈瑞将车停在加里公寓的外面,当加里回来时,他们从车里出来,跟着他来到门前。加里转身看到他们。“哦,不,又是你们。”
“不是来逮捕你的,”特里说。“至少这次不是,只问几个问题,我们能进去吗?”
“如果我说不行呢?”
“那我们可以在警局问你。”特里微笑着。“你选吧!”
加里脸色阴沉,带他们进了屋里,房间里堆满了啤酒罐和残留着咖喱的盘子。“雪伦那个贱人又投诉了?”
“不,”特里小心翼翼地寻了个椅子坐下。“是关于我在警局让你看的那些照片,你哥们儿肖恩的照片。”
“他不是我哥们儿。”加里打开冰箱拿了罐啤酒。“谁说他是了?”
“嗯,实际上很多人这么说,雪伦是其中之一。”
“她能知道他什么?”他小口喝着啤酒,面露敌意。
“比你想象的多。”特里端详着加里的脸,好像看到上面因焦虑冒出了亮晶晶的汗珠。“哦,行啦,加里,不要糊弄我,你强奸雪伦那晚,这家伙可是你所谓的不在场证明,记得吗?”
“我被判无罪,警官。”加里将啤酒罐摔在椅子上,泡沫从罐口溅出。“上帝啊,我要说多少次?我没有强奸雪伦,明白吗?”
“是啊,是啊。”特里叹了口气。“我想你也没和肖恩一起蹲过监狱?”
“我和500多号人关在一起,我难道都得认识他们吗?”
“你和这个人同住一间牢房。肖恩·墨菲,监狱记录上是这么说的,看这里。”加里没有理会特里拿给他看的那张记录。“还有他的照片。”
“行,我们曾是狱友,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需要和他谈谈,加里,涉及一些严重的性侵犯案件。这是我们来这的原因。”
“我们需要你协助我们找到他,”哈瑞补充道。
“你们一定是蠢到家了,你们两个。”加里嘲笑地摇着头。“你们不能将我定罪,所以现在想将罪名安在他头上,就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协助,”哈瑞说道,“下次你遇到什么麻烦时……”
“嗯,好吧。”加里喝了一大口酒。“好像我是可恶的告密者。是什么罪名,说来听听?”
特里心想,他要上钩了吗。他尽量不动声色地说道:“你还记得那个被谋杀的女人吗?玛利亚·克莱顿?你们在她家里干过活儿。”
“你认为我杀了她,不是吗,贝特森先生?但我没有,你看吧。”
“是的,好吧,”特里盯着自己的双手。“肖恩在罗伯森公司时曾往她家运送过砖瓦。”
“那又如何?”
“肖恩也占了她的便宜,就像你一样。差不多。”
“她会为钱和任何人上床,也许除你以外。”
特里看出,一贯傲慢的加里开始透出对此事的兴趣。
“你对此不感到惊讶吗?”
“不,为啥惊讶?婊子就是干这个的。”特里注意到他脸上没有一丝意外的神色,明显是不知道肖恩性无能这件事。
“他之后又将一些建筑材料运送到卡伦·惠特克住的学生宿舍。你还记得她吗,加里?”
“拍裸照的那个?记得啊——你还以为在森林里追她的人是我,是吧?笨蛋!”
“你发现照片的那一天是肖恩送的货,加里。你给他看那些照片了吗?”
“也许吧,那又如何?”加里的脸上浮现出狡诈的神情。“哦,我知道了。你们又怀疑到他身上了,是吧?还有谋杀的罪名,是吧?”
“有可能,”特里谨慎地承认道。“一些证据显示他有杀人嫌疑。”
“就像指控我的那些证据,啊?”他狂笑起来,“那么,现在那些证据都到哪去了?”
特里犹豫起来。这是个无从回答的问题,但如果一言不发,加里突然就有很多说辞了,当意识到特里默认了这一点时,加里怒不可遏,脸涨得通红。
“你们这几个月一直把我当作这两个案子的嫌犯,紧咬着不放,现在却改变想法了,就那么一了百了啦?他妈的不道个歉吗,狗屎贝特森督察?就是‘对不起’,没听过这个词吗?你道歉时最好把那个婊子雪伦也拖来,一起给我赔不是,那样她就不会因为我想请她喝一杯该死的酒而抓破我的脸了!”
“哦,行啦,加里,你确实强奸了她!我的想法并没有改变,从未动摇过!”
加里怒视着他。“你这个蠢货!你狗屁不通,不是吗?”
情况像特里担心的那样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多亏哈瑞在他身边。“你瞧,加里,我只需要你帮个小忙,帮我找到肖恩,我们调查的是重案。如果他是无辜的,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哦,是的。”加里朝壁炉吐了口唾沫。“说得轻巧,你当初可把我折腾得不轻。”
特里叹了口气。“他在哪里,加里?在约克郡吗?”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他妈也绝不会告诉你。”加里神情蔑视地喝着他的啤酒。“如果没什么事,贝特森先生,我建议你带着你的跟班儿这里滚出去,好吗?”
从萨拉家中的客房可以俯瞰到拉里停在车道上的老式掀背轿车。她也听见艾米丽的卧室中传出音乐声。法官的裁决让两个年轻人十分沮丧,是他们找到了伊恩·金克斯和曼迪·凯特,并且坚信布罗迪才是杀死贾斯敏的凶手。萨拉知道自己应该抽些时间跟他们聊聊,宽慰一下他们,只是她此时必须争分夺秒地为出庭做准备。明天,萨拉将传唤她唯一的证人西蒙出庭作证。他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搞砸了,他们必败无疑。
这曾是西蒙的房间,萨拉坐在他们以前买给西蒙写作业的书桌前,检查明天将要提出的问题,想象着西蒙的回答,苦思什么是庭上辩护的最有效方式。她做着笔记,手中的铅笔狠狠地按在纸面上。
令人气恼的是,笔尖断了,萨拉打开书桌抽屉翻找卷笔刀。自然是一无所获。第一个抽屉空荡荡的;第二个抽屉装着摩托杂志——封面是全身上下只穿靴子的女摩托车手的那类杂志;第三个里面有个棕色旧信封。萨拉不经意地将信封中的东西倒在桌面上。
里面装的都是老照片。萨拉惊讶不已,将它们一一摊开在桌面上。这都是西蒙小时候的照片:5岁的西蒙去上学;西蒙在西克罗夫特公园玩球;在少有的合家出游中,西蒙在布莱克浦摆弄玩具桶和铲子;脸上沾满巧克力的西蒙在鲍勃母亲的厨房中做蛋糕。萨拉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些照片了。
她身后的房门被轻轻推开了,鲍勃走了进来。“你在干什么?”
萨拉叹了口气,“我在记笔记,然后就发现了这些照片。”
“什么照片?”他的视线越过她的肩膀。
“在西蒙抽屉中发现的,一定是他以前放的。”
“照片上都是他吗?”
她又翻看了其他一些照片:西蒙抱着婴儿时的艾米丽;西蒙和鲍勃一起读书;西蒙穿着利兹联队的队服。
“是的,看起来都是他的照片,”萨拉说,“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么多照片。”
“因为他都放在这里了,那时他可能很看重这些照片。”
“是的。”萨拉痛苦地意识到了一点。“只有屈指可数的照片上有我的存在。”
这是真的。西蒙的单人照有很多;一些是他和祖父母或者和鲍勃的合照;只有两张是和萨拉的合照。一张是穿着迷你裙的萨拉怀中抱着婴儿时的西蒙,她看起来比现在的艾米丽还要年轻;另一张是瘦长的少年西蒙,闷闷不乐地站在容光焕发的母亲旁边,她头戴学位帽,身穿长袍,刚获得法律学位证书。
“其他照片在哪里?”萨拉烦恼地喃喃自语。“一定不止这些啊?”
“也许他带走了。”
“也许只有这些。我总是忙于学习,没有任何闲暇,他不久前在监狱里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所以现在你正在作出补偿,”鲍勃轻声说。
“是的,只是迟了很多年。”萨拉将照片塞回信封,拿起她的便笺本,然后又厌恶地将它扔在一旁。“这还有什么要紧?我能做的准备都做了。”
萨拉看见便笺本下面有张落下的照片,伸手将它抽出来。照片上是躺在两根球门柱间的鲍勃,未能阻挡住10岁西蒙的胜利射门。
“那时,都是你陪着他。”她转身看着鲍勃,“后来怎么了,鲍勃?”
“他长大了,我帮不了他了,现在只有你能帮他。”
“但愿我能,”她低声地自言自语,感到灰色的绝望浸入了她的灵魂。“鲍勃,关于今天……”
“别说这些了,我不应该多管闲事。”
“我是为了西蒙着想。”
“我能理解。你是律师,我不是,只是……”他摇摇头。
“只是这对布罗迪来说很残忍。这就是你想说的吗?”
“萨拉,拜托,我不想争吵。”
“你当然是对的。我还没傻到连这个都不明白,鲍勃。只是身为律师,对道德的看法……会比常人复杂。”
两人坐在那里,陷入一阵沉默。艾米丽的房门开了,传来了下楼梯的脚步声。
“嗯,你这是承认了,你也认为根本不是布罗迪干的?”
“没有证据表明是他干的,不是吗?”
“那么,如果不是西蒙干的话,凶手是谁?”
“只有上帝知道,但我们目前所知的就是西蒙坚持说自己不是凶手。明天,他要尽力让陪审团相信他。如果西蒙失败了,他就完蛋了。”
他们又陷入了更长久的沉默。窗外传来拉里和艾米丽的低语声。然后拉里关上车门,驾车离开了。艾米丽上楼来,回到自己的房间。
鲍勃将手放在萨拉的肩上,轻轻地按摩她紧绷的肌肉。“我可做不了你做的工作。你把全世界都扛在自己肩上,不是吗?”
萨拉记得按摩是他的拿手活儿,后来他们都太忙了,孩子们的出世使他们彼此产生了隔阂。她向鲍勃靠拢,享受着他的按摩,让手臂放松。
“你不必睡在这里,”过了一会儿,鲍勃说。“这让我也感到孤独,跟我回卧室睡吧?”
“好的,也许我会。”萨拉摸着鲍勃的手,让他停止按摩,吻着他的手指,然后挺直身子。“我完事后就会过去。”
两个小时后,萨拉蹑手蹑脚地爬上了床,躺在熟睡的丈夫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