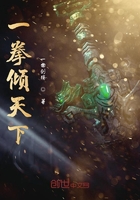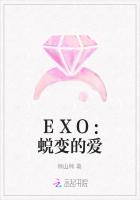独有三起案件,叫人难以理解。连史学家孟森也说:“雍、乾间文字之狱,有最难解者三事。”
这三事,便是谢济世、陆生枬、尹嘉铨案件。
第一件,给“四书”作注的谢济世
谢济世为广西全州人,十九岁中解元,二十三岁中进士,学养是极为深厚的。他陷到文字狱里,原因很简单,就是给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中的《大学》作注释。他作注时参考的资料是《礼记》,而不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也不是程子的《格致传》。
没有按程朱理学的经典版本来进行注释,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要知道,所谓的《礼记》版本和程朱理学版本,都是经过雍正先生批准实行的。这就是说,不管你按哪个版本来作注释,依当局的文化法例来说,都是可以的。
可是,那时的朝廷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比较多。这次,一件合法的事情,又被当成非法的事来处理。他们说,谢济世诽谤程朱理学这门伟大的学问,犯了极为严重的罪行。结果,谢济世被判死罪,且是斩立决。好在谢济世命大,居然逃脱一劫,充军到新疆阿尔泰做了一阵子苦力了事。
这当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也是清朝文字狱案件中的一个奇迹。但回过头来看看,不得不承认,谢济世还是当了冤大头。
为什么会冤枉他呢?原来,谢济世这人书生气较浓,见到不平之事,喜欢说三道四。当时,他刚当上浙江道监察御史,就上书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列举了田大官人十大罪状。这个田大官人可不是一般人,而是当朝圣上雍正皇帝的宠臣啊。
所以,圣上得找个貌似正当的理由,把谢济世这种“不识时务”的人干掉。恰恰,谢济世这家伙喜欢搞点学问,那好,就在文字上找点茬子得了。——这才是谢济世被治罪的本因。
如果单纯从文字上去研究谢的罪因,那实在是比较奇怪的。
第二件,写《通鉴论》的陆生枬
与谢济世一样,陆生枬也是广西人,也爱做学问。谢济世充军到阿尔泰时,陆生枬正好因罪发配在阿尔泰。这位陆夫子喜欢钻在故纸堆里用功,写了一本《通鉴论》。就是这本书,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说实话,单纯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说,这本书也没什么。不过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按一般道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不了来一场学术争论,也犯不上杀头的罪名。
问题是他碰上的不是别人,而是心胸有点狭隘、脾气有些峻急的雍正。
试摘陆夫子的几个观点,比如,他论当皇帝:“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翻译成白话大约就是:人越尊贵,权力越大,则处身更危险,所遇灾祸也更猛烈。因为皇帝可以随意地让人活、让人死、奖赏人、处罚人,则志向必疏,而怕他的人越多。人们即使想朝他发怒也不敢说,想报复他也不敢轻易表现。所以这些人隐藏得必然很深,一旦爆发就不得了。)又比如,论当宰相:“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这话的大意是:听取意见可以了解人,轻信意见也能误解人。听意见要尽量广泛,广泛的话就不会有壅塞;采信意见的时候要尽量审慎,审慎则可以尽量避免失误。)这些观点,很有哲理,完全一片忠君爱国之心,可以说一片赤诚溢于言表。但不知雍正怎么想的,他硬是把这些观点看成是反动的,不但加以驳斥,而且还说:“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将陆生枬军前正法。”这实在说不过去。史学家孟森很想不通,他同情陆生枬,说,“今试由读史论鉴者平心论之,有一语可致杀身否”?所以,这一件事情从判死罪的理由来说,也是比较奇怪的。
据说,本来,朝廷打算是将陆生枬和谢济世一同处死,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
一人赴死,不知陆生枬当时到底是何感受。
第三件,想出名的尹嘉铨
尹嘉铨的案件似乎要明了些。
这个人,对名气的追求,是有些狂热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理学方面小有名气的尹嘉铨退休回到老家。
大概是不甘于寂寞吧,第二年,乾隆到他老家巡查时,他上了一道折子,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请皇上给自己曾经受过褒奖的父亲尹会一封谥号。二是请皇上将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和他的父亲尹会一一起从祀文庙。这的确是一番光宗耀祖的美梦。但乾隆不这么看,他一拿到这个折子,就十分不高兴,命人抄了这位尹大师的家,并将大师拿交刑部问罪。
罪怎么来呢?就从大师所著的文字上来。尹大师写道:“为帝者师。”乾隆对此的批注怒形于色:“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联师傅否?”言中之意十分明白:你尹嘉铨这个水平,怎么能当我乾隆的老师呢?尹大师自称古稀老人,乾隆则说:“联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以自号。”仔细地想一想,这些理由当然不能成为理由,乾隆的驳斥显得差强人意,甚至强词夺理。但话语权掌握在他手里,虽然尹大师作为一代名儒,且作过大理寺卿(大约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可也没有办法,只好以死抵罪。
尹嘉铨这场祸端的起因,只是他的名利心太重,想得到朝廷的表彰,想得到家族的最高荣誉。也许,他递上折子时,乾隆的心情不好。但无论怎么说,从乾隆对他的反驳看,也不至于被处以极刑。孟森为此愤愤不平。这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七十称古稀,从杜甫时就有这样的诗句,人们都习惯于这样称呼,怎么能作为帝王的专利?乾隆去年刚到七十,自称“古稀天子”。尹嘉铨之称古稀,是不是在他后面,还不得而知,姑且不说。此外尹嘉铨日记中的一些家庭琐语,即有迂腐可笑,怎能说犯了杀身之罪?
为此,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个案子也是奇怪的。
实际上,说这些文字狱奇怪,到底是史学家们太善良了。
处于封闭禁锢的皇权时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杀几个文人,对于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又算得什么?
何况,这些自作聪明的皇帝,从这些文人的笔下解读出了“反动”的气息,那更是杀你没商量了。
呜呼,在清朝文字狱兴盛时代,和那些心理有些变态的皇帝去讲道理,史学家们确乎显得有些天真了。
嘉庆的修正主义
颙琰(嘉庆)登基的时候,乾隆身体还很好。虽然禅位仪式举行过了,但乾隆作为太上皇,实权仍然握在手里。作为一个有点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退休君主,乾隆不愿意看到皇位继承人对自己的思想和权威稍有忤逆。——终究当了几十年的皇帝,余威不会因为退位而熄灭。对于他的指示和命令,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所以,嘉庆虽然名义上有着人世间的极权和尊荣,实际上好多事情都不能自主。当时朝鲜驻北京的外交官李秉模在一次拜谒乾隆之后,听和珅这样传乾隆的话,“联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朝鲜实录》)言下之意无非是接班人虽然上台了,但我还把着总方向。这种境况下,嘉庆要按自己意志办事,实在有些难度。
好在嘉庆并不是一个急着夺权的人。至少,在乾隆活着的时候,他做到了韬光养晦、中规中矩。据外国使臣观察,嘉庆当时“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朝鲜实录》),这份修为和定力,着实叫人钦佩。
嘉庆三年(1798)正月初三,乾隆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此之时,嘉庆有些悲痛,心头也应该有些快慰,压抑的日子终于到头了呵。这时候,他看到了先皇传下来的遗诏。这份遗诏以貌似谦和平淡的语调,对乾隆一生作了相当盛大辉煌的描述。比如,诏中有言:“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作不靖者,悉所殄灭。”这是对乾隆“十全武功”的概略式回忆,说乾隆治理国家时,一片升平景象,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平定了伊犁、回部等叛乱,凡是哪里有不平安的地方,都全部搞掂。这些武功如何,读史之人心知肚明,此处不过又一次让人领略到乾隆好大喜功的心理而已。
诏中还说:“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计日成擒,蒇功在即。”这里说,四川一带白莲教起义已经差不多平息和完工,那些头目和要犯,接连被抓获,胜利指日可待。而实际情况是,这场反对朝廷的战争才刚刚开始。遗诏的描述,不过自欺欺人罢了。
嘉庆对遗诏中所说之事很有些不以为然,大有进行“修正”的意图。可遗诏一经公开,想再重新改写颁布,已经不可能了。嘉庆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做事也很有意思,为了“响应”遗诏,他在乾隆崩逝当日就下了一道谕旨,充分肯定了乾隆的伟大业绩。可第二天,他又下一道谕旨,专论川、楚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军事较量,中间的意思与乾隆遗诏中有很多抵触的地方。——他的“修正”在谕旨中展开了。
比如,乾隆遗诏中说,川、楚的白莲教起义已经镇压得差不多了。嘉庆的上谕却说,从没有哪场战争像这场战争一样,经历好几年、费了几千万两银子还打不完的。“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心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即如在京谙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穷乏之员,家计顿臻饶裕”。这话说得特明白,责骂特重。你们这些带兵大臣,根本不想打仗,只知道玩兵养匪,冒功邀赏。哪里有一点战事,在京的官员们就千方百计谋求前往。等到回来时,连那些穷得叮当响的人,也把家里搞得很富裕。原来,仗老打不完,全是这些大臣、将领一心只想搜刮民财,没有认真出力的缘故。
上谕还说:“试思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大意是说,大臣们那些钱财,都是从地方索要的。而地方官吏,只得从老百姓那里搜刮。老百姓没有多少钱,哪里满足得了上面的需求。最后只得铤而走险,参加“教匪”,反抗压迫。这里分析了白莲教起义的原因,根本在“官逼民反”。不过,一个新上任的皇帝能看到这一点,也真不容易。
可奇怪的是,乾隆也算聪明之人,怎么会不知道战事的真实情况呢?上谕接着分析了原因,说,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在一线战斗的将领们,有了小小的功劳,就铺叙夸报,碰上战败的情况,则采用粉饰的办法,不按实际情况报告上来。这些说完之后,嘉庆开始声色俱厉:“伊等节次奏报,杀贼数千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特此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将领,均当涤虑洗心,力图振奋,期于春令,一律剿办完竣,绥靖地方。若仍蹈欺饰,怠玩故辙,再逾此次定限,惟按军律从事。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意思很明白,你们这些大小将领,如果仍然虚报战功,不按时完成任务,那我就对你们军法从事。不要以为我年纪小就好欺负啊!
分析嘉庆的上谕,有这么两个特点:一是对乾隆所下的结论,即“川、楚教匪起义很快将平息完工”进行了修正和反拨。二是由于为尊者讳的缘故,这个板子没有直接打在乾隆身上,而是打在大臣和将领们的身上。
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策略。为什么这么说呢?站在嘉庆的角度来说,乾隆即使再不行、犯的错误再多,作为儿子,他也不能说出否定的话来。但压抑多年之后,终于找到一个表达的机会,自然还是要说一说的。只是不能说得太露骨,所以只好骂大臣。凡是乾隆肯定过的大臣,就骂他、处罚他,这实际上就是对乾隆的拨乱反正。
同时,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立威”。——正如他自己在上谕中所说,不要以为我年幼就可欺啊!
这道“修正主义式”的谕旨公开后不久,乾隆宠信的大学士和珅被革职并赐死、户部尚书福长安被革职,新皇帝的权威由此树立起来。
“修正”的目的和本意,大概就在这里了。
就这样走上巅峰——清代几位皇帝继位的趣事与秘闻
皇位的传承,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从康熙开始,清朝就废除了立长子作太子的规矩。常用的方法是,待到一定时候,由皇帝把自己确定的继位人选写下来,放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或是写好后“缄藏鐍匣”放在身边。等皇上驾崩时,再由相国等重臣打开这些秘旨,明确新的皇帝人选,举行登基仪式,颁布新的年号,翻开历史新页。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传承都是这样顺利的,这种模式化的交接常常发生插曲,其间难免会发生一些秘闻和趣事。
一
在位60年后,康熙一朝归天,四皇子胤禛(雍正)当上了皇帝。这一过程,表面看似常规演绎,实则波谲云诡,暗含许多惊涛骇浪。康熙儿子很多,多至35个,虽然有几个没有带大便死了,但到他崩殂时,超过20岁的儿子还达12个。
到底谁来继承大统,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