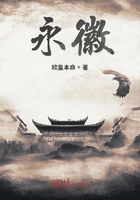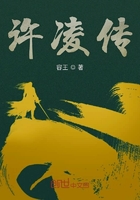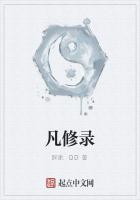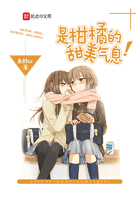比如,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同治帝下旨责备恭王召对失仪,降郡王。光绪十年(1884),慈禧太后下旨责备恭王委靡因循,罢军机大臣,停双俸。总结他的起落经历,可以发现:起,是因为他的能力;落,是因为他的狂悖。
史学家吴相湘认为,恭王性格开明、临事敏决、能力富强,“若能懔功高震主之古训,以多尔衮为前车之鉴,稍自敛抑,固可以持盈保泰,享荣华于久远”。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恭王的故事说明,在最高当权者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里,作为臣子还是恭谨些才好,一旦得意而忘形,跟随而至的可能就是灾难。
曾国藩的人才观
深夜读史,掩卷长思,颇感慨古之成事,都与延揽人才人和量才器使有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代帝王中凡是有建树者,无不都是重人才、用人才的明君。就拿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论之,其从一书生起家,最后位极人臣,成为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亦与他礼贤下士、爱护人才有莫大的关联。
竭力揽才,才尽其用
在晚年写下的名著《挺经》里,曾国藩专设“英才”一章,细述他一生关于人才的认识,可视为他人才观的总纲。
他说:“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这实在是一个平常的道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人才要用在适宜处。曾国藩的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身体力行了这一简单的用人原理。
首先是他评价人才不拘一格。“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每到一地,他都是极力寻访延揽“一技之长者”。他手下的优秀人才,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武,真可谓“英雄不问出身”,有才即能为我所用。
曾公的用人,却并非见之就用,而是多能用其所长。有胆气者令其领兵打仗,谨慎者用其筹办粮饷,有文字功底者让其办文案,学问深厚者校勘书籍。
梳理一下曾国藩麾下的人才,即可看出他的“量才器使”的眼光。在曾氏幕府工作过的谋略人才有郭嵩焘、李鸿章、薛福成等,军事人才水上有彭玉麟、陆上有李元度等,吏治人才有李宗羡、赵烈文等,文教人才有俞樾、吴汝纶,制造人才有李善兰、容闳等。这些人,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者,堪称一时之人杰。
不用有才无德者
有些所谓的人才也有不为曾国藩所用的。
据记载,曾国藩在安庆时,有个同乡来投奔他。这位同乡朴讷谨厚,颇有才能。
曾国藩经过一番考察,准备委以事情,先试用起来。
就在这时,曾国藩和这位同乡共进晚餐,当时饭里有些秕谷,那位同乡很细致,先把秕谷捡除,才开始吃。
这一切,被曾国藩看在眼里。饭后,下完棋,曾国藩叫这位同乡去领几十两银子,卷铺盖回家。
同乡大惊失色,急忙请曾国藩的表弟去打听原因。
曾国藩说:“这位同乡家里本来很穷,但刚到我这里作客就这样讲究,吃饭还要去除秕谷,看来他平时也是这样的吧!我恐怕他以后见异思迁,所以让他走算了。”
由此可知,曾国藩擅长从细微处观察人的品德,——这也是他用人较准的重要原因。
注重培养人才
当然,人才不是天生的。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故而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对李鸿章的培养。《清史稿》为李鸿章立传,中有“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从国藩于江西”的叙述。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教诲极尽心思。
为了打磨李鸿章这个少年得志的富家子弟的锐气和棱角,在李鸿章去江西九江投奔他的时候,曾氏对他很是冷淡,甚至“拒收”,给心高气傲的李鸿章一个“下马威”。
曾氏在军中极讲规矩,每天定时吃饭,李鸿章散漫惯了,经常不能按时赶到,特别是早饭很难按时去吃,曾国藩大动肝火,当着所有幕僚的面大声训斥,吓得李鸿章心里打鼓,从此小心谨慎。
对于李鸿章的文书处理能力和其他优点,曾氏注意褒奖和鼓励,认为李天资过人,必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正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使李鸿章很快成才,终成一代名臣。曾氏死时,李鸿章作联挽之:“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上联抒尽对老师栽培的感念之情,亦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曾氏善于培养人才的事实。
善用长远眼光看人才
如果只是一般使用和培养人才,那最多也只能算是个伯乐而已。
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从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来观照人才,别有一种怀抱和寄托。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这种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才观,使他在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上,格外用心用力,格外具有长远眼光。
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许多同时代官员。在他治下,众多人才是“徒步数千里从公”,“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
这正是曾氏成就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斯人寂寞谁复知——关于晚清外交名臣郭嵩焘的漫语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一个惯于早起的人,或许有这样的经验。想一想,在乡村,在晨曦初露的时刻,从逼狭的房间走向苍茫广袤的大地。你能感觉到什么呢?
空气如此清新,大地如许旷远,天空如斯澄澈,世界确实是美好的。
但你也会发现,这种美丽的感觉如同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一会儿就消逝了。在你四周,空无一人,没有人分享你的感受,没有人理解你的喜悦。你是寂寞的,也是惆怅的。在这一刻,你无疑有些悲哀。这是过客和独行者的悲哀,也是先知们的悲哀。
晚清开国之时,国人中也不乏这样的先知。他们孤独地行走在黎明前凄清的路途上,没有赞同,没有喝彩,只有无尽的冷眼和寂寥。
近代外交家郭嵩焘(1818~1891)的遭遇,就生动地诠释了那个世界对先行者的冷漠。
一郭嵩焘的清醒与僧格林沁的鲁莽
(一)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这句烂熟了的名联用在郭嵩焘身上倒也合适。郭嵩焘系湖南湘阴人氏。年少时以才气闻名乡里,曾在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游学,与曾国藩、刘蓉等闻人有同窗之谊。
中举之后,赴浙江给学政罗文俊当幕僚。在浙江,他有幸参加了鸦片战争,目睹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如何轰开中国的大门。这场战争中,朝廷“和战不定”、“举措失宜”和在外交方面的“懵懂”,令对世界潮流有初步了解的他感到了震惊,当然还有丝丝心痛。
浙江之行,对于郭嵩焘漫长的洋务生涯而言,仅是一个序幕。直到中了进士、并率湘军攻伐太平军积累了大量应敌经验之后此时已是咸丰九年(1859),——他才与洋人有了真正接触。
(二)
这一年,他奉皇上之命,到天津辅佐当时的名将僧格林沁王,抗击来势汹汹的英法联军。
甫一接触,他就发现僧王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从武功上来说,僧王孔武有力,算得上一员骁将。但在对敌的谋略上,却简单得可笑。
在僧王眼里,区区英法蛮夷,与强大的天朝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轻蔑使人鲁莽。对于侵略者,僧王打算以武力驱除了事。而郭嵩焘知道,环顾世界大势,一旦拉开战幕,就意味着了无宁日,用谈判解决问题,或许是更好的策略。现在想想,这两种考虑都不无道理。可从当时实际情形看,拼死一战固然能赢得民族主义情绪的尊敬和拥戴,但实际上,谈判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至少可以换得片时的宁静。
然而,其时民族主义情绪正如火一样燃烧,郭嵩焘主张谈判的想法,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更为吊诡的是,面对强大的英法军队,僧王居然打了一场胜仗。这场来得太快了的胜利,对常在败退消息中煎熬的国人来说,及时送上了一剂兴奋的良药。僧王更是被冲昏了头脑,连说话都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洋兵的鬼把戏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呢?”
尤为可笑的是,僧王这次攻打英法联军,动用了最精锐的部队。但对外界,他却说,只用了民兵(乡勇)就把敌人解决了。以此来博得民众对他的盲目崇拜和称颂。
他还扬言,要充分利用这次胜仗,恫吓一下那些在英法联军和清廷之间的调停者——美、俄公使,让这些西洋鬼子都知道清廷的厉害。
(三)
胜利容易使人昏醉。
在举国欢庆胜利的光景下,郭嵩焘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他知道,强大的英法联军后面还蕴蓄巨大的力量,绝不是一次小小的胜仗就可以击败的。此时,如果不采取些措施,加以弥补和挽救,清廷面对的将是更猛烈的炮火。
这样的先见,使他极力主张借美、俄调停之机,乘胜进行谈判,尽量和平解决。
僧王是狂傲的。他听不进郭嵩焘的开出的药方。他要的,是简单的战争与胜利。谈判这种啰嗦事,他怎么会看在眼里呢?
郭嵩焘和僧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举国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支持僧王的情况下,这是需要勇气和代价的。
真理,有时候真的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可是,世界给予这些少数人的待遇却并不公平。连一度支持郭嵩焘的咸丰帝,也不得不对主战派作出让步。
郭嵩焘的被处理显然在所难免了。
这位湖南蛮子面对这一切,显示出很大的蛮劲:“吾道之不行也,遂浩然以归。”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你们不按我的思路办,老子不干了。
(四)
带着一片伤心事,郭嵩焘离开京城,南归潇湘。
就在南下的路途中,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咸丰帝急急惶惶逃到热河,稍后,京城被攻陷。
郭嵩焘不是先知,但他预见到了放弃谈判的后果。
对于这个预言的应验,他没有感到高兴。相反,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作为一个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士大夫,他心中只有一片山河破碎的悲痛。
他指斥不谙时事、不懂外交的琦善、耆英、叶名琛与僧格林沁为办理夷务的“四凶”。对那些不知世界大势、一味盲目主战的大臣,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像僧王这样的人,杀了都还嫌轻。
当然,这种深度悲情里,有他的意气之争,可就当时清廷的战备状况来说,与其让狂热的、虚荣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着国家去以卵击石,倒不如先坐下来谈判调停,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只可惜,在那个几乎“唯天朝独尊”的时代里,谁都以为华夏是正统、洋人是蛮夷,谁也不愿、不敢和洋人打交道。谁主张和洋人谈判,谁就是卖国贼。
郭嵩焘这样清醒看待洋人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找不到同行者。他的痛心疾首又有谁能理解呢?就连自己的好友曾国藩、刘蓉等都不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还有谁能明白他呢?
他,只能处在寂寞的迷雾中。
二瑞麟这样的旧官僚无法理解他
(一)
人生充满了起起落落。
郭嵩焘被重新起用,已是同治皇帝任期内的事情了。经过一段时间与洋人的接触,朝廷已经知道了厉害,社会上小觑洋人的人也逐渐少起来。这种风气逐渐成长,慢慢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一些官员、民众见了洋人常畏缩如鼠,发生什么纠纷,即使有理也不敢力争。如此一来,助长了洋人们的嚣张气焰,与他们讲外交、讲规则,反而有些难了。
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赴任广东巡抚。广东近海,是洋人较早通商和侵占的地方。在这里为官,如何与洋人打交道,就成了一门必修的学问。
那时候,国门初开,没有专门的外交学校,也没有人愿意学和蛮夷交往之学,怕背负“汉奸”的罪名。除了郭嵩焘等几个人之外,真正懂得用外交法则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并不多见。
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是满洲正黄旗人瑞麟。
细讲起来,瑞麟和郭嵩焘是有些渊源的。咸丰八年(1858),英军进犯天津时,瑞麟曾被派去修筑大沽炮台,不久即调任直隶总督。
咸丰九年(1859),郭嵩焘去天津协助僧格林沁御敌时,瑞麟又已调户部任职。
说起来,两人都曾在天津抵御过外敌入侵,只是时间错开,也许并没有正面打过交道。
嗣后,瑞麟被派驻通州,率领京兵万人,应对英法联军的进攻,但屡遭败绩,数次被革职。好在终究是旗人,加之咸丰帝避难热河时,又能伴侍君侧。因而,即便多次被处分,也能多次复起,不断地被重用。——这样一个人,和自己共担治理广东之责,郭嵩焘的心里应该还是有些芥蒂吧。至少在办理外交事务上,他们的意见是不统一的。
一个是懂得世界大势的学者型官员,一个是只知打打杀杀的猛将型首长,怎么能想到一块儿去呢?
(二)
开始时,一切都还将就着。虽然有点不团结,但磕磕碰碰地还能过得下去。
只是,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打破这个局面的,缘起于“引渡森王”事件。
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是强弩之末。许多太平天国的残兵游勇退守到广东境内。太平天国的森王侯玉山在清军的左冲右突中,居然逃到了香港。
香港属英国管辖,森王在此寻求政治避难,可以说找到了最好的护身符。清军这边所能做的,只能是干瞪眼,没有办法抓他。
庆幸的是,这边有个郭嵩焘。他并不畏惧英国的强势威权,当然也不是简单的武力相向。他拿起了现代国际法律、外交武器,和英人据理力争,最终使英人理屈,让清廷把侯玉山引渡回来。
侯玉山被带回广州后,迅速被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