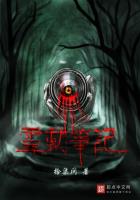老大确实有些不高兴。他说。
嗯,这单买卖赔了不少。他说。
嗯,可能走露了消息。他又说。
嗯,我说。
同样的,我说嗯的意思是,你们快走吧,别烦我。我跟老大的这种关系他和他都知道,明白。但并不说破,他和别人说不说破我不知道,但从未在我面前说破过。
有些事就是这样,大家心知肚明,但这层窗户纸谁也不捅破。
因为一旦捅破了,对大家都没好处。
我站起来,从座位上勾起我的手包,用我八公分的细跟鞋,踩着“嗒嗒嗒”的脚步,在他们俩人的视线里走出了房间。
我知道,他们会特别注视一下由于我走路姿势的缘故撩起的旗袍后摆和后摆下露出的修长的腿。然后,也许会相视笑一下,更也许的是摇了几下头。
他们摇头是为老大。
老大之所以能稳稳当当地做老大,是因为这个集团不是纯老大的,是某机构的下属单位,当然,这只是个幌子。但是不然的话,老大能这么稳稳当当地做老大么?
要不,谁敢做老大?
老大还能活几天哪?
我从未给自己未来做过筹划,直到遇到梅生。
但梅生不买我的账。
那天我踩够了那支香烟,甩手就走了。应该说甩腿就走了。因为我那时心理素质还没现在这么好,我怕继续留在那个房间,会被他看出我的心思,而这心思,对于那时的我,很羞于见人。
我斜靠在床头上,一次次地回想梅生那张脸,那个笑。我心里笑开了花。
我要嫁给他!
想到此,那晚我在漆黑的房间里第一次吓了自己一跳。
那个傍晚我一直朝着夕阳的方向往河边走,路两侧是篷勃的芦苇,郁郁葱葱,每根枝杆都挑动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欲望。
我希望能遇到梅生。
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