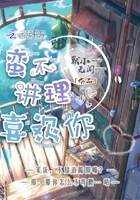“怎么会这样?”三个女人同时惊呼,纷纷凑过来看我的牌。于是我将那些章只理了理,她们这才信服地点了点头,不过看我的眼神却在不断地变化着,由一开始的疑惑到惊异,再到近似乎狂热的崇拜,像是信徒见到耶稣一般的神情。这不禁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点小小的满足。
但我表面依旧是冷冷的,一改往日的风趣幽默,变得不苟言笑起来。默默地码着牌,一边注视着三女的举动,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她们码牌时竟也在记忆。
更让我意外的是她们洗牌时,每只手下都控着几张牌。表面上是将桌上的牌和得翻江倒海,而实际上那几张牌却一直没动过。码时分别垛开,各自安插进自己的那一方中。
我不动声色地看完这一切,终于知道大嫂为何会占庄占到现在了,想不到麻将史上的第一批老千竟会是三名女子。但让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她们是如何控制这色子,好让自己能拿到她俩先前就做好的牌。
于是我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只见大嫂将色子往桌上一丢,我留意了一下:一个三,一个五,共八点。而当二嫂拾起色子时,三嫂却拉着我问道:“风弟,方才嫂嫂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你是如何连牌地没看便知道自己糊了呢?”
我哪里会上当,答话时留了个心眼,余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两只色子。二嫂见我转过头去,迅速地将色子掷于桌面,喊了声七后,又飞快地收起递于大嫂。
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她们哪时控制了色子?只是引开了我注意力瞎报了个数罢了。于是我故作惊讶状:“不对啊,我怎么看着是十一点哦。”呵呵,我也瞎报了一个数字。
“啊?那什么?”二嫂显然是没有想到我会突然怀疑起她掷的色子来,竟慌了神,接口便问道:“风弟你都没看怎知道是十一?”
“你如何知道我没有看?”我步步紧逼,一句不饶。
“我方才分明见你回过头跟三嫂说话来着。”二嫂显然已经是乱了方寸。
“你掷色子看我做甚?”依旧是淡淡的笑,但却是很认真。
“这”二嫂终于被我问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傻傻地看向一旁的大嫂。
“哎哟,我说二妹你也真是,风弟说没看见,你就再掷一遍给他看看便是,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何必当真呢?”大嫂这会儿倒学会充好人了。
不过我听得出来,她那最后一句是说给我听的。于是我忙纠正道:“嫂嫂这话可就不对了,正所谓赌场如战场。平日时在玩玩也就算了,即是带了彩头,又怎能当儿戏?”
“行了行了,二嫂重掷就是了。”二嫂郁闷地拾起色子又重掷了一次,十一,哈哈,这也能给我蒙上?运气太好了点吧。
于是我幸运地拿到了本属于大嫂的牌。细一看,靠,十三张麻将竟有十二张是条子,太夸张了吧。但我依旧是不动起色,淡淡地摇了摇头道:“重掷一下运气好像好了不少嘛?”
此话一出,明显感到屋中的气氛不对了,三女开始有些坐立不安起来。结果不难想像,自然是我糊了,且是清一色自摸。靠,这种牌再不糊那真是天理不容啊。
接下来的牌便好打多了,但我并没有轻敌,而是按步就班,稳打稳扎。生怕这几个女人再玩出什么花样来。
依旧是我那种前卫打法,起牌后推起一看便扣倒,也不整理,拿了牌也只是轻轻一捏,留不留下都不会往中间插,而脸上却始终不动声色,甚至可以说是面无表情。
我知道,这样一来,三女的心理压力一定是更大了。任她们再又天份,又何时见过盲打这等后现代玩法,再加上先前的把戏被我看穿,斗志自然是跌到了最低点。
而我恰恰相反,有如喝了红牛一般,动力强劲,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感。要说牌桌上的事有时还就是这样,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而运气走了留也留不下。此时这话正好形容起我们眼下的四个人来。
终于,在离八圈结束还有三牌的时候,大嫂将牌一推说是不打了。也难怪,虽说三人都还有一个庄,但跟我之间的差距确实太大了,怕是不连糊十牌也不一定能赶上吧。
这样打下去又还有什么意思呢,跟躺在那里让人摧残又有何区别?呵呵,我说的是心理上的,身理上的说不定还真是她们想要的呢。不过我不是雷锋,缺的便是助人为乐的精神,这种事怕是帮不上忙了。
见大嫂放弃了抵抗,我才又恢复了往日平易近人的笑容,恭敬地站起身来:“三位嫂嫂承让,小弟今日如有冒犯之处,还望嫂嫂们海涵。”
大嫂这才撑着桌子站了起来,脸上现出一丝淡淡的疲惫来。不可否认,没了心机的她却更显出一丝妩媚来,虽说我叫她一声大嫂,可细看来也不过才二十五六的模样,甚至比我还要小上一两岁,只见其长长地叹了口气。
“没想到风弟的牌意打得如此出神入化,嫂嫂我不得不服啊!”
“嫂嫂过奖了,其实几位嫂嫂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打得这般精通,倒是实在让小弟佩服啊。以小弟之见,若是在再给嫂嫂多些时日,只怕是小弟我也不是几位嫂嫂的对手了吧。”
我说的是实情,能在短短几月内靠着自己的悟性将麻将练到这个水平的人怕是也不多了。大嫂听我所言之后只是淡淡一笑,已没了先前的风情。
“风弟莫要再取笑嫂嫂了,输了就输是输了,实不相瞒,风弟所要的麻将窑场中就有现货,都是你周兄前些时日赶工烧制的,不想还未等他拉去卖掉,便已”
说到这里,不禁眼眶有些湿润起来。这样一看倒觉得这女人又不似先前那般薄情了。
大嫂顿了顿,等情续平复了才又说道:“都是嫂嫂们不好,明明受了风弟的恩惠还这般为难你,让做大嫂的自己心里也不安。可嫂嫂们也难啊!”
说到这儿,大嫂已是真的流下泪来,再看二嫂跟三嫂,也已是泣不成声了。见此情形,我不竟暗道蹊巧,心想这几个女人是怎么了?
于是我掏出怀中那块梅雨心送我的手绢递于离我最近的三嫂道:“嫂嫂们莫再伤心了,若有何难处不妨对小弟直言,小弟自当尽力相助。”
再看二嫂与三嫂依旧是哭得泪眼朦胧。只有大嫂勉强止住了眼泪,向我倾诉了一段不为人所知怨妇心声。
只见她抬起衣袖缓缓地拭去了眼角的泪水,低声哭诉着:“风弟是否觉得你这三位嫂嫂都是薄情寡义之人?是否觉得嫂嫂们对你周哥的死显得太冷漠了?”
我无声地点了点头,我希望能听到她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呵呵呵呵呵呵”大嫂发出一阵让人心寒的笑声,而看我的眼神也变得空洞起来,直直地,仿佛已穿过了我的身体,看到那未知的境地。接而,那双眼变很死灰,有如一潭死水,却透出无尽的怨气。
这一刻我被这双眼深深地触动了,这眼神绝不应该属于眼前的这样一位少妇,因为,这眼神中预示着太多的磨难。
好半天,大嫂才又开始说话了,声音却让人感到异常的寒冷,有如江南冬季里阴冷的风,“是的,我恨他,我恨不得他快些死掉,我真的不知道,上天为何要这样对我们,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最后那一句大嫂几乎是哭喊着叫出来的。可能是情绪太为激动了,竟变得有些不能言语。
见此情形,我只能再次安慰,突然间我开始有了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成了一名街道办的妇女主任了。不过,我这个妇女主任当得还是比较称职,至少几分钟后,在我的耐心劝说之下,大嫂已经恢复了语言表达能力。
只见其再次拭去了眼角的泪水,向我敞开了心扉。“本已为他死了,我们的苦难就会结束,却哪曾想到,这心里的伤又怎是轻易能抚去的?”
大嫂一边抽泣一边说着,其他两位嫂子显然也已被她的情绪所感染,竟相互抱头痛哭起来。末了还是大嫂比较坚强,第一个抬起头来。
只见其接过三嫂递来的我那条手绢,狠狠地擤了一下鼻子。说实话,当时我那个心疼啊,没得说了。要知道这条手绢对我来说可是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在我看来,那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一种让人怀念的回味,一份深埋心底的情愫
平日里我自己都舍不得用的,不想今日却被大嫂她唉,不说了,全当是捐献灾区了。
无奈地摇了摇头,不再去想那手绢的事,开始专心听听大嫂讲述起来,我也急于想知道,周道到底做了些什么让他这三个媳妇深恶痛绝的事来,以至于大嫂尽会巴不得他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