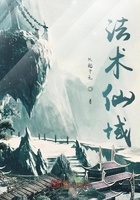落花时节
(一)落花时节又逢君
一个僧人站在树下念法华经,灰色僧衣,映在碧绿的连香木叶荫里有一种万里青空的飒然,连清瑜走过去他亦没有察觉,唯是落叶拂在经卷上他微微顿了顿,伸手拾去。
“凌尘。”,清瑜唤他。
他抬起头看见她,却并不惊异,只微微一笑道:“施主,贫僧法号智空。”
清瑜心头一恸。逆光看去,他的眉目依稀,经了剃度,人如小孩子的新鲜洁净。
“蒲凌尘,你不记得我?”
“记得的。”他微笑,“佛法不是教人忘记。”
他转身带清瑜进禅院,在高悬“洪椿坪”大匾的台阶上停下来,将崖边两棵新叶葳蕤的树指给她看。
“是椿木,”他安静地说,“洪椿晓雨,若是有缘,明早施主离开的时候或许能够看到。”
从前他带着她一起给公司跑业务,吃泡面,夏天办公室热得像蒸笼,他就坐在唯一的一台电风扇前给大家讲洪椿坪,说山上有多么凉快,说那是夏天有急雨的早晨,椿木浓绿的叶子在雨里面闪闪发亮,一山的树都在唱歌,下面看不见的深谷里满满都是涨水的声音……
那时候大家都没钱到这么远的地方,但他说的话她马上就相信了。而现在她站在峨眉山上,他却只这样安静地跟她说原来洪椿坪的雨是像雾一样的没有声音,是夏天里的杏花春雨,沾不湿行人的衣衫。
“你那么聪明——为什么要相信看不见的东西?”
“贫僧智空,”他耐心地向她解释,“我相信世间总有能让我相信的东西。”
下午六、七点的天光依然明亮,清瑜转过身去。那个穿银灰色西装打丝领带的蒲凌尘呢,那个不露声色微笑着和刁钻客户周旋到底的蒲凌尘呢?——如今站在她面前的是谁?这样安详,和他背后的青山一样温和宁静,又无情……
很久之后天才慢慢黑下来,前院子里有人唤开门,是一群游山晚归的学生。
清瑜换了长衬衣下楼吃饭,木楼梯“咯吱咯吱”的响,迎面有僧人上来,一路拉开昏黄的电灯。清瑜让到一边,头顶的灯光洒下来她才确定那并不是他。
可是这样让她如何分辨呢,他们都是一色的僧袍,一样的低着头,一样的谦卑,把光芒全都收敛。
“不去吃饭么?”清瑜问。那时候他们在公司加班她也这样问,他总是说不饿,然后在画完下一张图纸的时候匆匆跑到楼下去,买上来两大碗鸡骨粥。
“过午不食,施主。”那僧人抬头看她,合手在胸前,年轻的脸上带着一个腼腆的笑。
清瑜也向他微笑。这样清冷的地方连微笑都可以是莲花般洁净无尘,可她宁只要从前,他满脸都是狭促,捉弄了人便忍不住得意地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眉梢都是不能掩饰的璀璨。
斋堂在前庭,傍了鱼池假山,门口两大盆碧桃已经快开过了,逢人从旁边过,便簌簌地落下粉红的花朵,仿佛一些垂死的蝶。
正是吃饭的时候,可是人并不多。大竹蒸笼蒸着饭,乳白的蒸汽“噗噗”地冒出来,一抬头,连白炽灯都模糊成晕黄的一小片。清瑜要了客饭,端上来只一碟粉丝,一碟笋,另有半碗汤,小方块的豆腐沉在碗底,葱花不多,却切得极细,仿佛是早春山坡上刚才遥遥可见的那一点绿意。
他现在也不过吃这个。可是在从前,他是肯为了一碗桂花酒酿开两个小时车的人。
清瑜叫住一个端菜的僧人。
僧人怔了一怔:“施主是说智空师兄?”
“是。”她有一点不安。当然现在他已叫智空,可是蒲凌尘三个字又如何能够忘记?
“师兄去了仙峰寺。”僧人微微一笑。
“仙峰寺?”
“师兄去讲法华经,讲完便回来。”
清瑜并不知道仙峰寺在哪里,回到房间把地图找出来,才惊觉原来那样远——
蒲凌尘讨厌黑暗,可是智空从来都不。他发了愿,白天要在洪椿坪台阶旁的连香木下面念诵法华经,所以他只在夜里去讲经,一个人提着风灯走长长的寂寞的山路。他是智空,所以有佛法护佑,步履之下能生莲花,比蒲凌尘更加无所畏惧。
(二)儿需成名酒需醉
所有人都知道蒲凌尘无所畏惧,所向无敌。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很小,只在城南偏租几间民房。可是小也有小的好处,竞争激烈的业内无人注意,几乎等于有了保护色。
然而他似乎并不专心广告业。
清瑜和他去郊外拍外景,拍完了他不肯走,说是看到路边种植园的蟹爪兰好。
其实那间种植园已经处于半歇业状态,数千盆蟹爪兰都只奄奄一息,叶片上蒙着厚厚的尘土——清瑜只觉他孩子气得好笑,花市里多少鲜花他都不肯多看一眼,偏跑到这样远的地方来看蟹爪兰。可他终于还是买了两盆花,和园主拉家常,兴致勃勃地要参观其它的花房。
离开的时候园主特地送他们到门口。他一手捧着蟹爪兰,一手揽过清瑜,笑呵呵对人家说,多谢,我女朋友只喜欢白色的蟹爪兰,其它地方都买不到。
清瑜只觉得脸烫得要烧起来,可是他浑若无事般把她揽得更紧。在旁人面前清瑜不好努力挣脱,然而渐渐也仿佛忘记了要挣脱。直到走出去很远他才松开她,戏谑地欣赏她的脸。
“你要做什么?”清瑜心慌,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他大笑:“不这样说他怎肯将这两盆花卖得这样便宜?”
蒲凌尘不只买了花。
一个月之后,他以低于市价百分之三十的价格买下了那个占地三百多亩的种植园。
那时公司的状况并不好,职员议论纷纷,甚至有两个人提出了辞职申请。
可是他并不愿意解释。有一次清瑜晚上回公司拿东西,看见他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领带半松着,没有什么表情,只是默默地吸着烟。他身后是一大幅才完成的地产广告,古石桥上累累垂垂的青藤红花,祥云缭绕——明明该是现世静好、岁月无惊,可灯光下看去竟只是寂寥……
第二天他下令公司财务拨款,联系建筑商修厂房,把种植园的牌子换成了公司的名字。
清瑜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那地段交通不便,也不是规划的工业区,修起厂房来也不会有人问津。然而不知为什么她并没有去问他,只是将那两盆蟹爪兰细心地洗去了灰尘,然后悄悄放在了他的写字台上。
当然有更多的人辞职了。小公司每离开一个人都是一场大地震,清瑜独立支持人事部,应接不暇,唯有努力安抚,几乎精力交瘁。
次年春节之后,市政府宣布要开建城际列车,图纸上的铁轨笔直的穿过蒲凌尘修起的厂区,政府派车将他接去商谈,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地价已经翻了好几倍,但蒲凌尘婉转地表示他并不想卖出那片地,除非获得列车、车站以及铁路沿线的广告代理权——
他再一次胜利了。公司业务部的人早已经在他的授意下将计划详细拟定,手续完善,标书完美,滴水不漏。
人事进行了彻底的调整,清瑜这时候才明白他坚持不肯解释的原因:那是一场时日持久的试用期,现在留下的人都已经通过考验。
蒲凌尘的公司一夜之间声名远播,业务云来,同行望尘莫及,悔恨竟然忽略了如此的劲敌;而他就此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并且和他的公司一样,坚不可摧,无惧他人觊觎……
搬进新写字楼的那天晚上,公司包下一间酒吧庆祝。香槟开了一瓶又一瓶,舞池里有人笑有人哭有人大声欢呼,所有人都等待得太久——
他端了一杯酒来找清瑜,清瑜正接了电话从外面进来。
“怎么?”
“预约明天看样品的客户。”
她穿的白色绣花小旗袍让灯光照成了荔枝红,可是面孔看起来显得更小,有一种孩子般的端肃。
蒲凌尘忍不住笑起来:“你总是比旁人沉稳。”
“并不是。”她嫣然一笑,“他们是惊喜交加。”
“你呢?”
清瑜望定他:“当然不惊——从一开始我就参与了你的计划,不是吗?”
他知道她指什么,再一次大笑,就像那个时候,仿佛天下山河都在掌握之中。
“我们是最佳搭档。”他俯下身来同她碰杯。
“双剑合壁,天下无敌?”
“是,”他微笑,“双剑合壁,天下无敌!”
水晶杯子里的香槟酒不断释放出苹果味的气泡,仿佛那里面有一小串一小串“噼啪”作响的爆竹。清瑜想自己一定是醉了,居然会想起小时候过新年:初一早上落大雪,她总是很早就起了,穿着新棉袄坐在火炉旁边等着母亲煮饺子。窗户上面贴着的福字,玻璃盘子里盛满了红枣朱橘和圆胖的花生,令人看着便觉得欢喜,因为有无限大好光阴在前面。
(三)分付西风此夜凉
半夜里清瑜突然醒了,出了一身大汗,人只是软弱无力地伏在枕上。
有人在敲门。
水一般的月光将那人颀长的身影投映在窗纸上,敲门声极清晰,一下接着一下,寂静的夜里那钝重的声音仿佛直落到了人的心上。
清瑜颤了声音:“谁?”
“我。”
“智空?”
“不,蒲凌尘。”
清瑜突然泪如雨下——是否他在讲法华经的瞬间里突然悟透,割舍不断的是山下十丈红尘?
她拉开灯,走去给他开门。
“蒲凌尘?”她问。
然而他并不回答。光影交错里只看见他嘴角的微笑,那样熟悉,带着戏谑不羁,却能够让人信任臣服——
然后她突然醒来了。
头顶悬着白蒙蒙地蚊帐,她仍然躺在床上,梦里醒来原来还是梦。
她微微侧过头:窗户外面正透进来橘红色的光,佛鼓一声一声不紧不慢地敲着,诵经的声音呢喃如低语。
对面床铺的女子喃喃地抱怨着翻了一个身。清瑜等她衣被摩擦的簌簌声都停歇了,方才轻轻从床上起来,披上衣服走出门去。
并没有月光。中庭只铺着大青砂石的地砖,连香炉都不曾有,唯被正殿上照出的灯火烛光映得一片空明。殿中的僧人正在做早课,皆是低眉闭目,白蒲团托着流云般的僧衣,点点莲花灯盏灿若星辰。
清瑜没有看见他。楼下有小小的佛堂,虔诚的信众在那里随着正殿上的僧人同做早课,她便慢慢走下去,跪在最外面的蒲团上。
前面一位老太太梆梆地敲着木鱼,檐下梅枝翩翩的影正落在她的膝旁。
从前每到冬天天气极冷的时候,他便会去买一枝梅花来给她插在办公室里。旁人欣羡,唯她只微微一笑——人比花瘦,分明是取笑她的孱弱。可是惯了他玩笑的态度,觉得便是他的玩笑也比旁人的漂亮有趣。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她慕清瑜和蒲凌尘在一起,多么理所当然,同经患难,必将偕老。并不是没有片刻欢愉、也尝恨春宵苦短,然而他是戏里面的才子风流——华光横溢,如风流转,沉迷于世间的各样美丽,却从不肯为什么真正停留。
她唯有当他的一枝梅花。
修得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她原来读了只觉得好笑,很久以后才明白其中的艰难。
曙色微亮的时候,僧人们鱼贯从大殿里出来,散入菜园厨间。
他也在其间,僧衣的袖口翻出雪白的里子,颊上一道醒目的擦伤,见到她时却安然若素。
“怎么了?”
“昨晚回来的途中有一点小意外。”
“意外!”清瑜惊极。洪椿坪到仙峰寺经过曲折的九十九道拐,栈道极窄,一面临着深谷溪涧,容不得分毫差错。
他全然看透她的心意,微微一笑:“我一路念诵着法华经返回,所以并没有死。”
清瑜听到末一句,心头一震,猝然道:“你不会死!”
他仿佛料到她要说这样孩子气的话,却只是微笑,并不分辩。
朝阳映照下青砂石地洁净若琉璃,他明明就站在面前,却仿佛隔着云端,千载相逢犹如旦暮的寻常——究竟是谁负了谁,原来他早已经不想知道……
(四)锦瑟无端五十弦
第一次见到秦思绾是在衣香鬓影的酒会上,主人介绍只说是留学归国的画家,又遮遮掩掩,吐露了她显赫的背景。
年轻画家本人就像一幅画,简单的黑色长丝裙,人似照水的柳,不颦不笑也有一种楚楚的风致。她一出现立时就有人失手打破了杯子,红酒溅湿了白西装。
清瑜在侧,笑道:“你看,果然是红颜祸水。”
蒲凌尘一笑,仿佛漫不经心地低下头:“天底下哪个女子不是祸水,就是小龙女隐居在活死人墓,也能让霍都为她打上终南山。”
“你是霍都——或者杨过?”
“我是赵志敬!”他拉长了脸作势张牙舞爪。
清瑜怕他胡闹,连忙躲到露台上,隔了长长的落地窗笑问:“你不去?”
秦思绾那里众星捧月,蒲凌尘回头看了一眼,眼睛里又是那样狭促的光:“你许我去?”清瑜待要说什么,他已经又笑道:“可我不许我去。”
他真的没有去,自始至终陪伴清瑜身边,倒是清瑜自己有几分歉意,自觉错估了他的心意。
两个月之后公司顺利地和市内最著名的一间“云想”设计室签定了合同,负责新一年春夏时装的宣传。发布会那天清瑜也去了,主持人知她在蒲氏的地位,所以格外殷勤地来敷衍,末了还将她带到后台,为她介绍“云想”新任的首席设计师。
台后衣香鬓影,模特儿们正在换衣。配合江南三月的主题,化妆都是昆曲脸谱的风格,眼睛如同两片妩媚的桃叶子,烟水朦胧。
清瑜被请到大衣架子后面,年轻的首席设计师正好抬起头来,贝齿咬着两枚小小的珍珠别针——
四目相对。电光火石。狭路相逢。
“慕清瑜?”秦思绾不着痕迹地微笑,“凌尘提过你很多次,说蒲氏多亏有你。”
清瑜心头狐疑乱拟,手心里都是冷汗:“秦小姐怎知道是我?”
“人如其名。”
“不敢当。”清瑜渐渐镇定下来,“秦小姐年纪轻轻便进入‘云想’,真正才华横溢。”
“我做服装设计不过是业余,别人看着家父的薄面给我一个机会。”秦思绾笑,“——今天贵公司设计的秀场才是专业水准。”
“份内之事。”
明里春风拂面,暗地绵里藏针,刀来剑往里数个回合胜负不分,唯有天真的主持人不识其中机关,犹在一旁笑道:“原来两位认识。”
“并不。”秦思绾笑:“可我们是诗里面说的,相识未相见,同对一山青。”
原来如此!
清瑜只觉晴天霹雳:他们早已往来,宝剑以赠,丝萝相托——尚不知道的不过是她而已。
终于无可避免的争吵,相识以来第一次在他面前流泪。
而他只是不耐烦:“等两个月,我自然给你合理的解释。”
“怎样的解释能让我觉得合理?”她说:“你不再喜欢我?”
“说什么话?!”又是不耐烦,剑眉拧起来,仿佛全是她的无理取闹。
“那么为什么要和她在一起?”她穷追不舍——真正不舍,这一次她无故地知道,若是追他不上,从此便天涯两隔。
而他并不知道,转过头去声音已经微微恼然:“为什么要告诉你知道?!”
是,为什么要告诉她——郭襄、程瑛、陆无双都曾同杨过患难与共,公孙绿萼更为他舍去性命,可最终谁得与他在终南山下白头?
杨过的小龙女,蒲凌尘的秦思绾。
人世间的故事总是重复又重复。
第二天清瑜递了辞职信,蒲凌尘当然不准。可是他托辞筹备会议不来见她,挽留的话堂皇而冷淡。一天傍晚清瑜在写字楼下远远看见他的车,副驾上的女子衣裙鲜红如火。
最后清瑜是在会议室见蒲凌尘,同法国公司的会谈刚刚结束,宾主尽欢。秦思绾亦在座,慢条斯理地喝着一杯茶。
“思绾同老皮是校友,”蒲凌尘志得意满地笑,“这次多亏了她。”
老皮就是法国公司的老板,刚刚开始筹备会谈的时候清瑜嫌皮埃尔三字拗口,私下里只称老皮。蒲凌尘还笑她,说蒲氏未来就在此一举,怎可如此称呼这个生死攸关的人物?——然而就是那些事,似乎都是很久前的过往了……
清瑜深深吸一口气:“从递辞职信到现在正是两个星期。我现在走,并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
蒲凌尘的表情瞬间凝固:“慕清瑜,我跟你说过两个月——”
清瑜转过身。
她会心软,如果他多说一句话。
可是他竟然没有。
后来有一天,清瑜在古香古色的花梨木书案上用柔软的小白云写过一首词:
双桨浪花平,夹岸青山锁。你自归家我自归,说着如何过。我不思量你,你莫思量我,将你从前付我心,付与他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