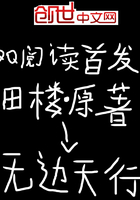室内几人听见鎏夕如此说道,脸上均现出震惊的神色。我侧目望去,却见凰月身躯微微颤抖着,面纱下的脸色已是白的没有半分血色。“你猜的没错,冬哥哥,就是中了那名曰缠绵的情蛊。”
“凰月!”我讶然万分,料不到凰月居然对秦征身上的毒如此了解。我定定打量着她,忽然发现自己对这个一直护着我陪着我的女子一点都不了解。早在居慈斋中,我便诧异她久居深山,居然会认识远在燕京的李渫,又只因为见了我一面便不惜牺牲整个居慈斋为掩护,助我和李渫逃脱藏阙的追杀。再后来,又是她不顾安危,在慌乱中护着哥哥一起逃到绥矽镇中,甚至为他惹上阙影之三的景飒这般危险人物……想起我要揭开她面纱时她那猝然而生的怒火,我不由惴惴联想到我们两人那双一模一样的眼睛……凰月她为何对刺史年府中人如此极力的维护?又为何会对年望冬身上的缠绵之毒了解的如此清晰?
“你到底是谁?”我眯起眼睛冷冷看她,一把护着秦征向后退去,却更清楚的看见她眼中一闪而逝的受伤。
鎏夕、唐三、秦征全都诧异的看着我俩,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骇得愣在当场。许久,凰月忽然轻笑两声,声音中透露的悲凉勾起我几分不忍,犹疑着是否自己反应的太过激动。
“凰月……”我怔怔张口,却不知要说什么,脑中纷乱闪现出众多画面——居慈斋上她和我一同守着火锅说话,握了我的手说“只愿醉过便忘”,又说“我们原不必这么见外”……
藏阙来袭时,又是她盯着我殷殷嘱咐“七日后西面山下离阳村见”,还塞了龟息丸在我手中,助我脱困……
景飒刺杀哥哥的那个晚上,她焦急的冲我喊,“夏儿,是你吗?”接着不顾生死的奔过来将我从屋顶上救回……
……
所有的一切,下一秒便在她缓缓揭开的面纱下有了解答——因为,那副覆面的白纱下,居然是张和年祈夏如出一辙的脸!
许久,室内只能听见几人快速的心跳声,还有那句和我记忆深处渐渐重叠了的空灵嗓音——“夏姐姐……我是知秋,年知秋!”
身躯一动,我踉跄不稳的身形蓦然被一人撑住,顾不得看清扶住我的到底是谁,我只能紧紧的抱着凰月此刻柔弱无比的肩,将她用力按在怀中,颤抖了声音呢喃着,“秋儿……你居然……是秋儿……”
年知秋,刺史府中一个被禁止提起的名字——据说她与年祈夏一母同胎,却在六岁时不幸夭折,与难产而逝的母亲葬在一处。这个谎言骗了年家所有的人,而她凰月公主的身份,更是紧随其后欺骗了所有天裕朝的子民!
“你怎么会……”我搂紧她不住颤抖的肩膀,抬手在她背上轻抚,心中蓦然涌上千般怜惜。初见她时,她是高高在上的凰月公主,那么的圣洁高贵,即使我觉得她与年祈夏记忆中的小秋儿一模一样,也不敢只凭那些残存的记忆亵渎了她的身份。
“我六岁时便被爹爹秘密送进了宫,他把我送给一堆我不认识的人,然后告诉我,今后我再也不是年知秋,我活着,便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天裕朝奉若神明的公主凰月……夏姐姐,那些宫女好凶,她们不许我哭,也不许我笑,只能终日对着不见阳光的佛堂跪拜,我好像爹,好想你,也好想冬哥哥能带着我们一起去放纸鸢,可是她们不准我想你,每想起你们一回,我的身上便要多一道鞭痕……”凰月俯在我怀中低声说着,浑身虚弱的仿佛只有依靠我的支撑才能勉强坐着,但语调却平静的似只在陈述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我心如刀绞,只能将她揽了又揽,恨不能代替她挨下那些鞭子。
十七岁时我和秦征的父母因为车祸身亡,好几个晚上我俩都只能在黑暗中背靠背蜷缩在沙发上,用彼此的体温温暖着对方。那时我们尚且不能坦然以对,更何况凰月当时只是个六岁的小孩子呢?虽然只是自幼失去了母亲,可那个将她送进宫里的父亲,却给她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对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来说,有什么会比强迫她离开亲人身边更痛苦吗?
压抑了十几年的秘密终于在今日一吐为快,我扶着她强撑着虚软立起,握了她的手却一直没有再松开,俯在她耳边重重说着——“以后,你不是凰月,你要记着自己的名字,你叫年、知、秋!”
我所有的心疼,所有的怜惜都融进此刻这句话中,定定的望了她的眼,我抹去眼眶中不断涌出泪水,露出一个不知是哭是笑的表情来,嘟着嘴道了句“幸好幸好,原来与我长得一样,今后我再也不用自卑自己没你漂亮了。”
说完,“扑哧”笑出声来,凰月被我不合时宜的抱怨逗引着自过往记忆中转醒,先是闪了闪神,旋即也轻松的随我笑开,不想这时身后“咕咚”一声,我回头一看,却是秦征不知怎么仰面倒在了地上。
我满脸不耐的走过去,伸脚踢踢他,“喂!起来了!我们一边抱头相认,你不来凑热闹就罢了,又装什么神弄什么鬼啊!”
秦征却没有如我所料般揉着被踢疼的屁股跳起来与我拼命,仍旧一动不动的躺在那。我心中忽然生出几丝不安,又伸出脚去,这回却是轻轻的碰碰他的腿,颤抖道,“起来啊,你别闹了……你怎么了?起来,你起来啊!”
惊惧的用力翻转他的身子,我浑身的力气仿佛在瞬间被尽数抽干,只跌坐下去无意识的抱了他用力摇着,“你怎么了?起来和我闹啊?你别吓我……阿征,别跟我闹了……”
只是秦征再也没有睁开眼,因为,他昏过去了。
一双白净的手指自我怀中将他接了过去,搭在他腕间试探起脉息,公子鎏夕那双温润如水的眸中霎时闪现一抹异样,“缠绵,又发作了。”
身后的凰月闻言忽然大力冲了过来,推开鎏夕便伸手捋起秦征一边的衣袖,我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只看了一眼便被眼中所见惊得说不出话来,因为那条白净的胳膊上赫然自腋窝下绵延出条条黑线,如藤蔓一般密密的爬满整条手臂,相互交缠纠葛,恍如缠杂不清的情丝……
“我去请郎中!”唐三见状飞快起身,却转瞬被鎏夕拦下,“没用的,除了夜蔻香,大公子只能一直维系着沉睡的状态,直到另一只情蛊的宿主死去,或者完全康复。”
猛然抬起头,我眸中霎时射出凌厉微光,定定射在他脸上,“告诉我,另一个解毒的方法!”
鎏夕还是那样温温和和的与我对视,眸中闪烁不清的东西莫名让我一阵心神不宁。回过身去一手揽了凰月的肩,一手与她一起将年望冬紧紧搂着,我轻轻在怀中之人耳边呢喃着,听起来像是在安慰他,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些话更多的是在说给自己听。“你不会有事,我们不是说了要永远在一起的,即使生活的场景换了换,我们还能证实彼此曾经的存在不是吗?”
秦征,你一定不会死!
这一刻请众神原谅我的自私吧,我居然情愿下一秒死去的会是年望冬,而不是我在世间唯一的亲人!
“缠绵之毒双蛊双宿,生同生,死同死。如若另外一只蛊虫依然活着,那么这只蛊虫的宿主便暂时不会有事。”鎏夕蹲下身,探手搭在年望冬的脉搏间,“大公子中毒已久,这蛊食了他大半精血,所以他才会一直沉睡不醒,至于前几日为何会突然苏醒,想必原因也是出在另外一只蛊虫的宿主身上,若我想的不错,那人已经服了第二颗夜蔻香。”
“什么!”我立时从萎靡中稍稍清醒,如此说来,莫非景飒已经将第二颗夜蔻香送给那人服下了?
“时间急迫,另一人身上缠绵尽除之时,便是大公子的极限了。眼下之计只有暂且试试另外一个法子了。”鎏夕犹豫半晌,终于在我强硬的态度下缓缓将另外一个方法说了出来。
“这第二种方法,便是有至亲之人以亲身血液为引,蛊虫才会舍弃原来的宿主,转寄入新的宿主体内。可是受蛊之人不出七七四十九日便会被戾性大发的蛊虫食尽精血,气绝而亡。”
原来,如此。
我恍然了悟了鎏夕方才为何一直隐忍着不肯说出,这解毒的方法居然要以至亲之人的性命为代价换取!
“我来。”一个安静的声音忽然低低在我耳边响起,我讶异的与凰月坚定的眸光对视,想不到她会毅然甘愿为此牺牲。我觑见她轻轻用手指抚过年望冬紧紧闭着的双眼,朱唇微启徐徐说道,“只要有一丝希望可以救他,我在所不惜!”
贝齿狠狠咬住下唇,我只觉周身血液翻腾的如炽热岩浆,众多纷杂不一的声音在耳边嘶吼,“不行,不能是她,不能再是她!”
指尖深深刺进掌心,尖锐的疼痛唤回我一丝清明,低低垂着头掩藏起脸上的复杂莫辨的神情,我微弯唇角,口中却以郑重语气沉沉说了一句,“你不行,还是我来吧。”
“夏姐姐……你……”凰月惊惧叫我一声,却在看清我脸上自嘲般的微笑时蓦然窒了一窒,继而握了我的肩与我铮然对抗,“我本来就是爹爹舍弃了的那个,你何必与我争抢,害他再尝一回失女之痛!”
一双细腻素白的手缓缓将她低垂的脸庞托在掌心,我用温和的眸光扫视她面上激动且悲伤的神色,柔声说:“秋儿,是姐姐对不住你,六岁那年我曾偷偷见过爹爹在书房与一个人说话,他说要将我送去太极宫给那人作女儿。那人走后,我生怕与你们分离,便在半夜偷跑出去,于大雨中淋了半夜,于是我病了,病的很重……可是后来,当我再起床时却再也找不到你。爹爹说你去陪娘亲了,我心底总是不愿相信——果然,那个本该被送走的我留下了,你,却被送入了宫中。呵呵……其实爹爹一开始想舍弃的便不是你……而是我。”
一抹震惊自她眉目间漾起,凰月不可置信的看着我,犹疑道,“姐姐……你的……你的记忆恢复了?”
我收回手掌掩在唇边,遮去那个已经没了温暖的笑,“是啊,我的记忆忽然间竟然恢复了,你看,我在居慈斋中就说过我是认识你的,偏偏李渫还不相信。若是你日后见了他,可一定要为我讨个说法啊!”说完神色一转,黑白分明的猫儿眼转了几转,故意神色轻松的看着她皱眉思索,好像真的考虑怎么惩罚他。
只是……那个人啊,我怎么会舍得罚他呢……
强自压抑下心中钝钝的痛,我语带轻笑向她说,“你一定要让他向我道歉,这是必须得!”
我的伪装并没能让她再次笑出来,盈盈水眸中氤氲的潮湿很快演变成一行清泪,顺着她绝美的轮廓慢慢流下,砸在我的脚背上,如重千斤。
我推开了她,缓缓向一旁面色沉静的鎏夕公子绽开一朵笑花,轻轻的,我张口说,“公子,劳烦你助我一臂了。”
鎏夕深深的看我一眼,仿佛也在作着什么事关生死的决定,许久才听他缓慢而沉重的声音在室内响起,“无妨,那在下冒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