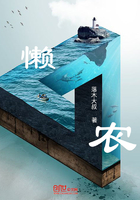方进愿看在杨七和方雪琴的情面上收岳宣为徒,但验看岳宣的双手后,又提出须完成三个条件才可以认他作师父。
岳宣的内心忐忑不安,表情却平静的像是信心满载、毫不畏惧。
“这三个条件是……”方进直视岳宣的眼睛,视线交汇时少年丝毫没有退怯的意思令他很满意,他一直坚信“气定者成大器”的道理,显然面前的少年足以配得起这句话。
杨七看看方进,又看看岳宣,免不了担忧起来。方进这狡猾的老狐狸,在盘算些什么?
“第一、十日之内,你要将这本书熟记,并且每一字皆不能错。”方进从另边的袖袋里拿出一本枯草黄的古本,递给岳宣,又补充说:“你休想找他们来帮你,每一个人拜师入门时的三个条件都不同,你只能靠自己。”
“是。”岳宣将古本紧紧抱在怀里,还好他已经认得许多字。自从与林青平结拜,与方雪琴一同回杨家,他一直都虚心学习,《百家姓》和《千字文》已经默写自如。余光中站在身旁的五个年轻男子,最大的已弱冠之年,最小的估摸着与自己同岁。
“第二、十日之内,你要练就一个本领,双臂平展,双手各提一桶湿米,站五个时辰。”方进提出第二个条件,立即得到杨七的反对。
杨七急说:“五个时辰,便是我们练武的人也很难完成,何况是他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
“兄若心疼他,弟不勉强便是。”方进态度和善,让杨进想要发火也没办法。伸手不打笑脸人,他只好气闷的闭上嘴巴。
“不。”岳宣给杨七磕了一个头,又给方进磕了一个,说:“我离开家为的是学门技艺,盼着日后能养活自己。请师父不辞辛劳,教授我养家活口的技艺,不论吃多少苦我都愿意。”又对杨七说:“七叔怜惜,此情如生身父母之恩,我谨记于心不敢忘。”
“既然你不怕吃苦,依了你便是。”杨七眼眶含泪,抬手示意方进继续。
方进干咳一声,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十日之内,你要将掌心和指腹变得如同手背一样光滑,蚕茧在上面滚动自如,且毫发无损。”
“是。我记住了,师父。”岳宣低下头看着一只手掌,上面层层叠叠的老茧。自从四岁那年跟着娘上山采野山参,双手的茧子像沙漠中流动的沙丘般堆积,新茧覆盖了老茧,老茧变成粗糙坚硬的肉,没有知觉。
“好了,你去吧。”方进扭头对站在身边的大徒弟说:“大虎,你带他去往的地方,别委屈了他。”
“是。”答应了一声,退了三步出去。其他人也被方进屏退,纷纷退出来。
何大虎领着岳宣,后面跟着四个师弟,一群人簇拥成一团边走边问,岳宣羞赧的不知该怎么回答。
作坊的东面被分隔出一个小院,四合院式的格局,建有正房六间,东厢房六间,西厢房四间,南房六间,共二十二间住所。正房六间是作坊里的老师傅的住所;东厢房六间,有三间是留给这些徒弟们的,每两人一间;另三间留给账房先生,外采办,内采办等人;西厢房六间留给技艺高超的帮工;南房六间是一般帮工的住所,大通炕能挤上十来个人。
岳宣被安排在东厢房的第三间房,与方进的五徒弟孙思君同屋。一南一北两张床,孙思君睡北床,岳宣睡南床。两床之间有一桌两椅,方椅粗笨而重。
安排好住处,何大虎厌气的警告说:“十日之内,思君会端饭菜给你,没事别到处乱跑,省得给我招惹麻烦。”
“是,多谢大师兄。”岳宣恭敬的颌首道谢,却招来何大虎的嫌弃。
“等你有能耐过三关,再称呼吧。现在就想当我的师弟,真真是可笑至极。”何大虎丢下一枚铜钥匙到床上,转身离开了。其他人也悄无声息的离开,只留有孙思君坐在自己的床上,好奇的盯着岳宣。
“这十日里的饭菜,你不必端来给我,我自己去取便是。”岳宣不意思的解释,他可不想被同住的室友嫌弃。
孙思君摇摇头,说:“这是规矩,当初我来时,也是由四师兄照顾了十日。不过,能不能过三关,顺利成为方师父的徒弟,可要看你的造化啦。”
“多谢。”岳宣仍觉得不好意思。
孙思君看看窗外,已到了正午时分,说:“你千万别出这屋子,否则过了三关,也会被逐出去。”
“这是为何?”岳宣不明所以。
孙思君站起来掸掸衣摆下的尘土,“你若不信,只管往外跑。”说完便离开了。
“我信你。”望着孙思君消失在小院大门口的背影,岳宣淡淡的说:“我相信你不会害我的。”
一连两日,岳宣日夜苦读、熟记熟背,终于将那本古本倒背如流,每一个字仿若印在他的脑子里。而同屋的孙思君像是故意避开,每天早早的起床离开,晚上很晚回来倒头便睡,一日三餐都放在门外,也不敲门。因此岳宣常常吃下冻成冰渣子的饭菜,可他毫无怨言,反而感激孙思君。
第三日,练习平展双臂提湿米桶,可不能出屋子,哪里去找稻米?寻常百姓家很难吃到稻米,更别提将好好的稻米浸湿放在桶里任由他练习臂力。
愁眉不展的坐在床上,岳宣沮丧的脸埋进双掌里,粗糙的手掌和指腹像锉一样划蹭着皮肤。摊开双掌,厌弃的盯着它们,想到这样的手怎么能变成光滑的?
“你怎么没有练习?”孙思君推门而入,一反常态的回到屋里,边说边脱外面的棉袍,眼睛一瞬不瞬的盯着岳宣。
“思君兄,我已熟记那本书,今日该练习第二个条件,可……”岳宣苦恼半日,亦没有想到好办法。
孙思君换好贴身的短衣,穿好棉袍,说:“给你这个。”说着,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两根粗麻绳丢在岳宣的床上。
“这……?”岳宣不明所以,拿着两根绳子发愣。听得外面有动响,伸头望去,见孙思君站在窗边。
“你这小兔崽子,我的床可不是装湿米的桶。要练习用椅子去,别动我的床!若移动半毫,待我晚上回来不打得你哭爹喊娘!”佯装恶狠狠的说完,孙思君裹紧棉袍,双手环抱在身前,在寒风中瑟缩着走出小院子。
岳宣热泪迎眶,低语:“多谢思君兄!”
感动完,立即行动。抓起那两根粗麻绳,一根绑在南床边的方椅,一根绑在北床边的方椅,岳宣站在中间,将两根绳子的另一头绑在小臂中央,往上一提平展双臂,手臂上青筋暴突,血管清晰可现。
不知数了多少颗树,不知过了多久。窗外黑漆漆的,对面西厢房的廊檐下点亮了灯笼,下工的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无数的门在“吱呀吱呀”的响着。
岳宣咬紧牙关,估摸着才四个时辰,再坚持,坚持……
“吱呀”一声,门开了,孙思君端着饭碗进来,大吃一惊,问:“从早晨我走后,你便一直这样?怪不得门外的午饭一动未动。”贴着床边绕过去,将瓷碗放在桌上,说:“真是蠢!你也不想想,今日站了五个时辰,要多少时日恢复体力?”
岳宣愕然回头,失神时气力全无,两只椅子“咚咚”连声摔在地上。顾不得椅子,追问:“多少时日?”
“勿需多言,快来吃饭。”孙思君用筷子敲打碗边,漫不经心的说:“第一日五个时辰;第二四个时辰;第三日三个时辰;第四日两个时辰;第五日一个时辰;第六日之后,想抬起胳膊都不容易,还谈什么过关?呵呵,你认命啊。”
“不。”岳宣摇头,抓住孙思君的胳膊,手竟酸痛无力,胳膊上的肌肉更痛。他不可置信的盯着自己的那只手,那条胳膊,声音颤抖的问:“为何会变成这样?”
孙思君甩开那只无力的手,“十日之期,你用掉了三日,还余七日。你若全都用在第二项上面,第三项呢?你那双长满老茧的手,能在余下的七日里变成凝脂玉肤吗?”
岳宣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从指尖到手腕没有半块好皮肉,那粗糙丑陋的老茧像一颗颗绊脚石阻挡着他。沮丧,从未有过的感觉在此时此刻像粗麻绳捆绑住他,能感觉到全身的血液凝固在脚底,令他寸步难行。
“你要放弃吗?”孙思君盘腿坐在床上,定定的看着垂头丧气的岳宣。
岳宣怔愣的看向与自己同龄的孙思君,冷冷的问:“你会帮我吗?”
“我为何要帮你。”孙思君皮笑肉不笑,单手拿过桌上的饭碗,举到岳宣面前,说:“吃了这碗饭,大口的吃。”
抬起无力的双手捧着饭碗,岳宣的泪珠一滴滴落在冰冷的饭菜上。几乎是往嘴巴里扒饭,填满的嘴巴没有一丝空隙。
孙思君满意的笑,眯起弯弯的眼,说:“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会帮你的。”
岳宣在心里回味着“乖乖听话”这四个字,他终究陷入一个无底的圈套之中。
“饭吃完了,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孙思君吹熄桌的蜡烛,裹紧棉袍。
岳宣也穿好棉袍,跟着孙思君一起离开小院子,去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忐忑不安,他仅仅能做到的只有埋藏忐忑不安的心情,装作平静的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走在前面的孙思君突然回头,调侃说:“你若是能过三关,可别忘了刚刚的承诺。”
“乖乖听话,我记住了。”岳宣平静的回答,让孙思君很满意。
两人愈行愈远,在离开方家作坊后,延着一条弯延的小路往漆黑的密林而去,隐隐约约间有火光在闪烁……
“看吧,我们要找的人在那里。”孙思君指指那个光亮的方向,拉着岳宣趟着没膝的雪艰难前行。
每行一步,岳宣的心悬上一寸,不知等在前面的人是谁?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