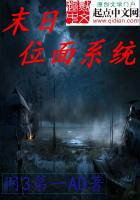靳师良眼见庙堂如此乌烟瘴气,不由大笑几声,“殷相一张好口舌!竟能颠倒黑白是非,卿家一门忠良,竟被殷相说成某国叛乱之徒,可悲啊,可悲啊!”
殷枭冷冷道:“靳尚书如此污蔑本相,安的是什么心!”
靳师良大笑道:“有如此相国,如此朝臣,大永朝危矣!”
殷枭直斥道:“妖言惑众!圣上,靳师良妖言惑众欺君犯上,请圣上明断!”
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君王喜欢听靳师良这样说话的,此前沈浔一再忍让只因为靳师良是朝中老臣,他新即位不久,根基不稳,还要仰仗这些老臣,如今靳师良公然危言耸听,全然不把他这个圣上放在眼里,从前沈浔心中本来不快,现在便是恨了。
沈浔冷哼一声,道:“靳师良妖言惑众,乱我朝纲,即日罢黜靳师良尚书一职,押入天牢,择日处斩!靳氏一族连坐,即日下狱!”
靳师良一生为国,想不到最后却是这样下场,他恨极反笑,在太极殿内狂狷大笑起来,“昏君!先祖打下来的江山,终在你手中灭亡!昏君啊!!”
沈浔已经脸色发青,怒喝道:“还不将靳师良给朕拖出去!”
殿外护卫急忙跑进来,将靳师良架起拖了出去,可惜一代老臣,竟落得如此下场。
殷枭此刻却谄媚,道:“靳师良妖言惑众,心怀不轨,圣上英明!”
朝臣便此附议,齐声道:“圣上英明!”
正好太极殿外斥候回来,“报!圣上,镇北大将军已率军抵达永安城!”
沈浔激动得一巴掌拍案,“好!立即宣他进宫!”
“是,圣上!”
殷枭便道:“圣上,镇北大将军已经回来了,圣上可以安心了。”
沈浔总算是松了口气,“殷相说得是,朕有镇北大将军,定可保我大永朝万年!”
“圣上英明!”
卿府。
卿家自贬为庶民之后便是深居简出,与世无争,尤其是卿浅浅走了之后,卿家更是长年大门紧闭,足不出户。
此次,却因为靳师良再开了大门。
靳师良府上有个门生,名叫尚艺,尚艺腹中有才,却不得志,靳师良看中他才华,将他留在府上,便是等有机会将他举荐给沈浔,不料靳师良却突然逢此变故,尚艺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官府抄靳师良府邸时,他便趁乱逃了出来,靳师良常在尚艺面前提起卿逸,他便跑到卿府,寻求帮助。
长年卧病在床的卿逸亲自见尚艺,卿蒙便也在一侧,尚艺见了卿逸当即跪下,“老卿相,救命啊!”
卿逸长发四散,但神智还算清楚,闻言只沉声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尚艺便将朝堂上的事说给卿逸听了,道:“老卿相,靳尚书赤胆忠心,如今被诬陷下狱,抄家灭族,还请老卿相你出手相救啊!”
卿逸却是苦笑,道:“公子大义,卿逸感佩,我与靳兄同朝为官数十载,靳兄有难,我自当拼死相救,公子且先起来,待老夫思虑周全,方定计谋。”
卿蒙却是面有难色,道:“父亲,如今我卿家已今非昔比,父亲如何周旋?”
卿蒙说的却是实话,卿家早已贬为庶民,别说救人,自保都难,卿逸沉思片刻,道:“蒙儿,去将老父的亢龙锏取来。”
卿蒙道:“是,父亲。”
尚艺闻言却是大惊:“亢龙锏!老卿相所说,可是先帝当年钦此的亢龙锏?”
卿逸点头,“公子博才多学,竟知道亢龙锏。”
尚艺道:“尚艺不才,自小便立下宏愿为国尽忠,所以多年来勤心学习,筚路蓝缕,希图能为国效力,可惜,大道不公,尚艺报国无门,此次恩师蒙难,尚艺已无心仕途,待恩师的事了结,便回乡下耕地种田,做个乡野农夫未尝不好。”
卿逸摇头,“公子此言差矣,圣上虽然昏聩,却是因得无人辅佐,以公子之才,若能辅佐圣上,实是我大永朝之幸事。”
尚艺也摇头笑道:“老卿相赤子之心,尚艺却是已经心冷,圣上非是明君,尚艺留下来也是无济于事,不如趁早归田,免得将来看到山河破碎,心中不忍。”
卿逸细看尚艺不像是轻率之人,便问道:“公子此言,可是三思而定?”
尚艺无奈道:“岂是三思?尚艺到永安城五年,至今连圣上面都没见着,如今的大永朝,已经乱了,我劝老卿相,不要再做多想,大永朝,已经没救了。”
卿逸细思片刻,道:“公子一腔才华,不怕可惜?”
尚艺道:“尚艺身怀绝世珍宝,可是无人识货,又能如何?”
卿逸看了一眼卿蒙,沉声道:“若老夫能为公子寻得识货之人呢?”
尚艺眼中一亮,“如今乱世,老卿相以为谁人识货?”
“南唐国侯,公仪珩。”
南唐国侯公仪珩,尚艺略有耳闻,公仪珩谋略深远,蛰伏多年,如今得南唐,又不主动滋事,确实是个难得的明主,此前尚艺本也有心投效,这还没有来得及向靳师良作辞,却突然遭遇此事,尚艺心生倦怠,真有退出仕途之心。
尚艺道:“当今天下,南唐国侯确有称雄逐鹿的实力和能力,可是尚艺如今已心生倦怠,只想归田,做个山野农夫。”
卿逸却道:“公子此言差矣,若今天下真的大乱,公子以为,在这乱世之中,公子能独善其身吗?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
尚艺猛地惊醒,跪地磕头,道:“老卿相一语惊醒梦中人!待恩师的事了结,尚艺便去赴南唐,大争之世,尚艺空有一腔热血,定要为天下百姓而洒!”
卿逸老怀大慰,道:“好!公子豪义,老夫佩服!”
尚艺道:“老卿相忠义,尚艺一生,定以老卿相为榜样。”
卿逸道:“公子过誉了,为臣者,忠心不二实乃本分,今后公子得政,切莫忘了今日所言。”
尚艺道:“他日尚艺若违背今日所言,天打五雷轰。”
卿逸便摸着雪白胡须,笑道:“好,好!公子有此壮心,实在是天下之福。”
尚艺拜了一拜,道:“老卿相言重,当此紧要时刻,还请老卿相先救恩师出狱。”
卿蒙正好取了亢龙锏进来,卿逸点头道:“公子在府上稍候片刻,老夫这就进宫,求圣上开恩,放了靳兄一家。”
尚艺再拜,“多谢。”
卿逸便道:“老夫还有几句话要对犬子交代,还请公子暂避。”
尚艺道:“恩师一事已有了结,尚艺这便告辞,启程赶赴南唐。”
卿逸道:“公子慢步,公子从尚书府出来得匆忙,想必身上也没有带盘缠,蒙儿,你去取些钱银给公子,公子一路保重。”
尚艺感念无内,堂堂七尺男儿竟热泪盈眶,再拜了一拜,“多谢老卿相相助!”说罢便慨然离去。
卿蒙令府上老管家取了一千两银子给尚艺,这才急忙回到卿逸卧房,卿逸已换好衣服,手里握着那把由玄铁打造的亢龙锏:“蒙儿,过来,老夫有话与你说。”
卿蒙道:“父亲训示。”
卿逸浑浊的老眼看着手中的亢龙锏,道:“此亢龙锏乃是先帝赐予老夫,上打昏君,下打佞臣,老夫本不欲用此物,可如今你靳伯父一家命在旦夕,老夫不能不救。”
卿蒙当然知道此物的重要性,若是遇到明君,卿逸此举可谓是赤胆忠心,可是若遇到昏君,那结果也就不好说了。
卿蒙担心的便也是这一点。
卿蒙道:“父亲,当今圣上昏聩无能,沉溺声色,恐怕……”
卿逸道:“老夫知道你担心什么,为人臣,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靳师良一生忠良,老夫虽知不可为,却要为之,否则,天下寒心啊。”
卿蒙心中沉重,道:“父亲的意思是,要死谏吗?”
卿逸叹了口气,“知我者,吾儿也。”
卿蒙跪地,哽咽道:“父亲如此,于国大义,于社稷大义,可卿家怎么办?”
卿逸伸手扶起卿蒙,“卿家有你,老夫放心。”
卿蒙硬声道:“卿蒙愿代父亲入宫,卿家不能没有父亲。”
卿逸却笑了起来,“老夫年过八十,已经活够本了,你已能撑起卿家了,老夫此去,生死难料,你即刻遣散卿家家丁,带着夫人去南唐找浅浅。”
卿逸如此安排,便是已经想好了退路,他此去死谏,本来就没有给自己留退路了,一则是为了全君臣情义,二则是用自己警示圣上,切不可亲佞臣误国。
卿蒙硬忍着的眼泪便流了下来,悲鸣一声:“父亲!”
卿逸道:“好了,时间不多了,你快去处置,老夫给你两个时辰。”
卿蒙不能言语,卿逸一把将卿蒙推开,“当此时刻,莫作妇人娇态!走!走了就别再回来!”
卿蒙踉跄几步,看着卿逸,万语千言却一个字说不出来,跪地磕了三个响头,再起身一言不发的走了。
卿逸看着卿蒙背影,重重叹了口气,末了,他看着手中的亢龙锏,浑浊的老眼中更是一片混沌。
次日永安城中便起流言,老丞相卿逸趁夜冒死直谏,被圣上当场处死,卿逸的亢龙锏也已被毁,靳师良一家也着即下令处死。
次日一大早,官府便发通缉令,举国通缉卿家,并同卿浅浅,沈浔更直接下旨给公仪珩,若是公仪珩肯交出卿浅浅,便可以既往不咎,若是不交,便等同于谋逆,处死刑!
公仪珩惊闻卿逸被处死,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将这个消息告知卿浅浅,十三月报告完消息,也难得的没有和公仪珩作对,站在一边静等公仪珩回复,公仪珩踱步,十三月耐心很快磨完,“公子,你别走来走去的好不好,我头晕。”
草包十三月,永远都是这么大嗓门,公仪珩道:“你不看就不头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