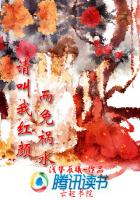呸呸!
她张口吐出一串水泡,恨恨地想:“我能有什么相似?唯一相似的是,我马上就要死了!”
死归死,死前的事不能马虎。曹操还等着她救出去呢。
她镇定心神,按照心中的隐约记忆,摸索着,向那墓顶移开的石板浮去——那里有萧史未乘的蛟龙,还有弄玉遗下的鸾凤。
不知外面的曹操会怎样,一定很震惊吧。
其实就算是她自己,也想不通自己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自己死掉,放曹操逃出生天。
她总觉得自己是个超级现实的人,所以肯如此选择,大概也不是因为崇高,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易地而处,让曹操来关机括?他根本没学过左慈的那本《九液金丹经》上的法门,无法在水底闭气这样长的时间,所以还没等他摸到机括,她就被飞快上涌的水流给淹死了。
再说曹操这样多疑又自私的人,他根本不会下去吧。
还不如自己死掉,总算有一个人能活着。何况活着的那个人,是曹操。他若不在,历史将会改写。而自己,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果死了,历史仍然是历史。
更何况,曹操若是感念她半分舍身相救的恩义,也会好好善待槿妍明河素月及绫锦院中众人。
她是权衡利弊,才作出这样最佳选择。
摸索的手指,忽然一动。她感觉到了指面那微微的突起,一棱一棱的,是鸾凤的翎羽。
身下的水波深处,静静地停放着碧台玉棺。
在幽暗的水底,它们放出淡淡的莹润光泽,仿佛幽远时光深处,一个女子温然的笑容。
万年公主真傻,从来男子只爱做乘龙快婿。何谓乘龙?娶了她,便要能翱翔九天才行。可是东汉末年的驸马们,根本就只能饱食等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卫青的地步。
可是她后来已经嫁给了张衡,连公主的名号都抛弃掉了,甚至不能葬入皇家的陵园,只能在离世之后,一个人孤零零地卧于这烂柯山中。家国都舍弃了,这至少说明了当初她是放下了过去,也舍弃了过去,是真的想要重新开始。
然而曹操是用了什么法子,激得她与张衡反目,带着儿子下山,又失子病逝?
织成按捺住纷繁思潮,用力向鸾背按下去!
脚下水底深处,传来呼呼的声响。仿佛是一只巨兽张大了血盆大口,鲸吞着翻涌的水波。
织成心中却是一松:果然有暗河的出口,此时水波正由此而倾泄出去。
过不多时,织成只觉头上一凉,却是水面已经降下来,与墓顶之间,有了小小的间隙,刚好能容她露出额头。经外面的山风一吹,凉飕飕的。而曹操的叫声,也在此时从上面传了下来:
“织成!织成!”
也不知叫了多久,他的嗓音都有些嘶哑,须发乱披,模样惶急,整个人仍是挂在先前那崖壁上,足尖勉强点在石上的浅窝里,手紧紧扳住一处岩石的尖角,似乎并未向上攀爬分毫。
此时见到织成的头从水中露出来,不禁大喜过望,嘶声叫道:“织成!你应我一声!你可还好?”
“我很好。”织成不敢放开那机括,手指犹自按于其中,甩了甩额上的湿发,尽力在脸上浮起一个微笑,心中有了些微的感动。
不管曹操此人心性如何,至少在这一刻,他是真诚的。而且是真正地为她感到焦急,紧张着她的安危,而不是……左慈和回雪锦。
“我在这里等你!”曹操焦急地回应道:“我想过了,稍后那水完全退去时,墓顶的石板必然会再次合上!你现在就把你的衣带全部解下来,与我的衣带连在一起。稍后你先把这条长衣带掷向我,我抓住一头,一定能将你拉出墓穴来,不会留你一人在此。”
显然他想到了这个办法,才没有独自爬出洞窟逃生,而是在原地等着织成。
看样子这机括的安置,是将墓顶石板与暗河之水连在了一起。墓顶若开,河水便会涌进来。反过来说,如果河水退去,墓顶必然会再次合上!
在河水退尽、墓顶未关之间,还有一个短暂的空隙。此时从墓穴的裂缝里逃出来,看似是个好主意。
但一来是这个空隙必然极短,要求曹操拉动衣带的速度极快。二来,织成有一种隐约的预感:左慈绝不会让他们出去得这样容易!
然织成的原则,是不放过任何逃生的机会。她一边手指仍按住机括,一边用另一只手加上嘴巴帮忙,依曹操之言,将先前烧成两段的衣带,加上自己身上衣带,笨拙地结在一起,又用牙齿咬得更紧些,这才往上抛去!
曹操衣袖拂出,凌空卷住衣带的另一端,紧紧握在手中,只待那河水全部退去,便要拉她出来。
水波此时已退了约有数尺,极目所望之处,那碧台玉棺的顶部,也微微露了出来。整个墓穴干净而寂冷,水波也平静下来,没有先前那样汹涌之势。可是织成就是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忽听一缕笛音,自地底而出,剌透涌动的波涛,清晰传来。
她微微一惊。
是左慈!
曲调熟悉,还是先前在洛川长草之间,左慈吹过的那支曲子。织成不知道曲中何意,忽听啪啪两声,却是曹操击节唱道: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他吟唱的曲调与掌击的节拍,竟与左慈的笛音宛转相合,丝毫无差:“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
织成静静地听着,只觉那笛音清婉动人,简朴之中,暗含无限相思缱绻。然而虽是倾诉相思,却毫无徘恻忧伤之意,只有着期待重见的喜悦: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一阵轰隆闷响,仿佛从地底传来,整个墓室都重重一震!
织成蓦地抬起头来,急向曹操叫道:“丞相,你快爬上去!快!”
话音未落,只觉墓穴一阵剧烈摇晃,无数碎石砖屑,自墓顶、墙壁纷纷掉落下来,密集如雨,有几块大些的打在了织成肩上,顿觉疼痛入骨!她不禁失声尖叫一声,偏偏手指仍按在那机括之上,半分也躲闪不得。
曹操瞧在眼里,不禁失色大惊,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一手紧紧扳住岩角,另一手猛然用力,便想用衣带将织成拉出来。
“不要!”织成另一手紧紧撑住墓顶裂缝边的石板,使曹操无法拉动自己,一边大声叫道:“此时若拉了我出去,机括弹回,那河水再次灌入,你我二人便都要死在这里!”
“可是我也不能眼看着你死在这里!”曹操急得两眼赤红,大声喝道:“左元放!你出来!我知道这是你搞的鬼!你要我的命,拿去便是,为何一定要我二人陪葬于此?”
笛声一顿,居然停住了。
左慈冷淡的笑声,仿佛在隔壁的墓室中,幽幽响起,即使在主墓室的织成,和高悬洞窟壁上的曹操听来,亦是颇为清晰:
“我并不希望织成留在这里,她若能逃出去,当然最好。但是你曹阿瞒既自诩英雄,为何不自己留下来,却要个女子来挡死?”
不等曹操说话,他又是嗤的一声,冷笑道:“若你留下来,我便让你留在主墓室里,隔阿宜最近的地方陪着她,因为你曾是她最爱的人。至于我自己,却甘愿陪葬在外面的耳室中,如同她一个随从、一个侍卫,甚至是一个厨子般。我左元放自问才华不逊于你曹阿瞒,死后却屈居你之下,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曹操一怔,面上浮起复杂的神情,竟然不知如何应答。
左慈似乎也并不打算曹操回答,只听隔着墓壁,那厢笛声又起,清雅悠然,仿佛不是穷途末路、守在这危机四伏的阴冷墓穴里,而是轻裘鲜马、纵放于旷野之中。
曹操全身颤抖,忽然大喝一声,如春雷舌绽:“好!”但见他身形一动,便要往墓穴纵落!
“且慢!”织成疾喝一声,止住了曹操方动的身形:
“丞相,你不能下来!”
她脑中念头疾转,口中滔滔不绝:“你若下来,我体弱力疲,根本无法爬出这洞窟,还是两人一起死在此处!不如丞相……丞相你……”
她深吸一口气,叫道:“外面都是丞相你的人,不如你快些跑出去,将他们都叫来,或许还能救我出去!”
“你骗人!”曹操厉声道:“稍后河水退去,墓顶闭合,左元放又开启了摧毁墓穴的机关,你根本就……就再也……”
他猛一咬牙,忽然放声叫道:“左元放!元放!我这一生,从来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我从未向人认过错!可是现在我知道,是我错了!我对不起阿宜,也远不如你!”
他声音嘶哑,似有真情流露,对于左慈也不再有敌意,“元放”二字,叫得自然而急切,一如当初他们游侠江湖之时:
“我只求你放了织成!若是她能安然无恙,你什么要求我都答应!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与阿宜当年之事,始终耿耿于怀!是我对不起阿宜,生未能同衾,令她含恨而终!眼下江山未靖,我亦尚有雄图未完,但我可以答应你,百年之后,我定会葬于此墓,永永远远,都陪在阿宜身边!”
他居然许下这样的承诺?须知古人最重的,一是生前名,二是身后事。无论皇帝宗亲、权臣贵人,更是在年华鼎盛时便精心营造百年后长眠的陵园。
万年公主倒也罢了,她本是女子,且汉室衰微,身后陵寝能否保住尚在未知之数。但以曹操目前的势头,隐然便要代汉而立,算是新朝的开国之主,难道不要自己的宗庙陵寝,竟肯葬于这偏僻的洛川之下、烂柯山中?
不仅织成大为震惊,但是左慈的笛音,也不由得再次顿住了。
“呵呵,真想不到呢,那样骄傲自负的曹阿瞒,也会有这样哀求我的一天……”
话虽如此,可是左慈感慨的话音中,却没有丝毫的得意,有的只是难以言明的苦涩,和饱含沧桑的唏嘘:
“晚了……织成出不去了。曹阿瞒,如今你可明白了?纵然你能权倾当世,志压群豪,但这世上有些事、有些人,你一样无能为力,晚了就是晚了,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比如阿宜,比如……织成。”
“不!”曹操目眶欲眦,喝道:“我要你放了织成!若是她……她……”
他目视织成,声音竟然哽咽,再难说出任何言语。
“机关已启,你看不到么?你知道这样的陵墓,一旦启动自毁机关,必是沉入地底深处,我又岂能与之抗衡?”
左慈幽幽道:“不过你放心,稍后我只会将阿宜之棺椁沉入地底,却会将织成留在这处墓穴之中。若你有心,不妨过些时日,再由这洞窟掘下来,将织成……带出去罢。”
曹操如雷亟一般,凝固在了岩石旁的虚空之中。但觉脚下又是一阵剧烈摇晃,想必那些自毁的机关,正在运行之中。
而从那墓顶的裂缝中望去,是更多的碎石土屑纷纷掉落,织成额上、脸上、皆被划破,数道鲜血披流而出。此时水又退去尺许,织成要奋力纵出半个身子,才能借着水的浮力,令手指刚刚按住墓顶的机括。
但她咬紧了牙,手指始终没有放开机括!
似乎整座大地,都在往下坍陷,甚至是曹操所处的洞窟之间,也有许多岩石被巨震晃松,纷纷落了下来。
织成用尽所有力气,向着视野中渐渐模糊、却一动不动的曹操,高声喊道:
“丞相!快走!快走!”
“好一个重情重义的女子!这样的女子,当年有阿宜,现在有你织成!是阿瞒无福,竟然全部错过!从前我只想着要你陪葬于此,其实是我错了!孤家寡人,抱憾终生,纵有江山万里,亦无人同赏,这才是对你最大的折磨!哈哈!哈哈哈!”倒是左慈的长笑之声,在隔壁墓室中响起,那笑声,清如鹤唳,亮如磬音,绝望之中,满是欢喜,厉声道:
“阿宜当年名满帝都,喜欢她的人中,陆文若是风雅名士,曹阿瞒是威武将军,张衡是道门之主,这些人无不是龙凤之姿,名重一时,可是到了头来,守护她到地老天荒者,却只有我左慈。”
他又长笑数声,高呼道:“人生至此,纵死无憾!快哉!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