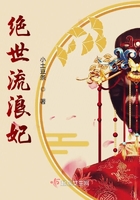“荞荞,我很生气,真的很生气,却是生自己的气,你这么难过的时候,我却还跟你发脾气。”
呃?什么情况。
面对如此急转而下的情况,唐荞不禁有些傻眼,谁来告诉她怎么回事?
周澍说完这番话后又是一阵静默,久久未有言语,直至唐荞受不了这安静,开口唤了一声。
“周澍?”
他怎么了?
“别说话,荞荞,别说话,你听我说就好了。”
唐荞困惑,不明白眼前的情况源自于何。
他想说,好啊,她听,问题是……他倒是说啊。她真的是忍不住了。
“周澍,你这是怎么了?”
终于,周澍抬起眼,目光中闪动的含义,唐荞不知道那是什么,她令他烦恼,令他伤心了吗?
“荞荞,是不是我逼着你了?是不是我把你给逼着了?所以你今天才特别激动。”
周澍问完,却没有给唐荞回答的机会,又自顾自的说道:“一定是,一定是我把你给逼着了。”
唐荞的心里有些微微酸楚,不,应该是她把他吓着了。
“荞荞……”
将唐荞的手执起,放在唇边,细细的吻了一遍,再开口,却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心底有太多太多想要说的,却又不知道该要怎么去说,到了嘴边,只有缱绻缠绵叹息一声。
“周澍,对不起。”
唐荞想了想,这声对不起总是要说的。
她如何不明白周澍的爱,所有的问题都出自她自己,那一点一点积压下来的问题,压的太深太厚,岂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
“不,荞荞,别说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把你逼太紧了。”
原本以为,他将她所有后路斩退,逼到她无路可退,所有一切都会明朗化,他也不必一等再等。然而,今日之事,想想却是后怕。
唐荞的脸有些扭曲的别扭,直觉的认定,一定是她小舅跟周澍说了什么。而她的这种直觉,从基本含义上来讲,是正确的。
伸头一刀缩头一把,不如把头伸出去好了,免得周澍手上那把刀钝,砍着脖子就不好了。
“周澍,你想知道什么?我可以全部告诉你。”
她将心拿出,双手奉上,心甘心愿。
在某些时刻,她真的是心甘情愿的。然而,她的苦楚在于,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一直觉得自己不正常,也一直将自己当作是病人看着。她不知道自己的病哪天就没得治了,到时候星火燎原。
上帝知道,这种感觉,像是被人绑上火堆上焚烧一般。
周澍的心脏狠狠的跳动了几下,但没有吭声。
他虽有很多事想知道,却不想太过逼他。可能这些年,他们相处的时间久了,他依着她的习惯去生活,在某些方面,他也许正在向唐荞靠拢。她愿意二百五的活着,只要她快乐,那他陪着她一起二百五好了。
他觉得难过。但他是男人,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形容这种难过,心被谁狠狠的捏过一般。他虽贪心于占有她的一切,让她对他依靠、依恋,至死方休,但他更加在乎的是她的感受,是她的快乐与否。
“如果你不想说,可以先不说,等哪天你愿意了,你再一点一点的告诉我。”
这次他愿意配合她的脚步,再慢也没关系,只要她好好的。
“不,我想说。”
唐荞摇摇头,她虽觉得周澍的步步紧逼令她烦躁,但她也是有欲念之人,她的欲念来自,她不想放开周澍。
“小的时候,我觉得周渝好了不起。”
唐荞开始慢悠悠的开口,而周澍则一直盯着她,生怕错过她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
“因为她所说的每句话都跟圣经似的,完全正确,她说我爸爸妈妈有了妹妹就不要我了,我起初不信,天天端着小板凳去院子门口等着,然而事实只证明,周渝的话果然是圣经。”那是不可抗拒的真理。
周澍记得,那时候她很烦她跟周渝,因为她们总在一起“无恶不作”,更是以惹怒他,弄哭虞舟为乐,然后有蛮长一段时间,一到落日黄昏,唐荞就端着小板凳与院子门口坐着,周渝怎么诱惑她,她都不理。
那时候虞舟还非常高兴的跑到他面前说,这恶魔姐俩终于闹掰了。
“那时候晚上我都不太敢睡,每天都有人哄我睡觉,姥姥,舅舅,甚至是姥爷,虽然那时候觉得姥爷哄人睡觉的脸臭臭的。”
那么多哄着她睡觉的人,却没有一个是她的爸爸妈妈,她才七岁,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那么狠心。她大学的经济法老师曾经说过,每个人在这世上存活着,都是件不易的事,生活的每每,都是痛苦的原罪。
这话不假,生活确实如此,她能体谅他们的不易,真的。只是每当她看新闻或报纸,看到谁家的小孩被父母怎么样,或是因父母怎么样时,她不免冷嗤出声,既然如此,当初又为何要生他们下来。难道就只是为了让他们来到这世上去体验那些不易么?
唐荞窒了窒,继续开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不通为什么。那时候还小,至少还有哭闹的权力,白天整天跟周渝腻在一起,上学放学,欺负欺负比我们小的同学,日子也还过的去,只是每当晚上的时候,总免不了要哭闹一番。”哭又有什么用呢,她的世界从来不是哭泣换来的,也换不来的。
那样日复一日的日子伴着她成长,一直到高中。
直至她父母将她接回H市,那时候她真心以为,只要她爸爸妈妈还疼她,以前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只是,当她躺在医院,她姥姥坐在床边一个劲的抹眼泪的时候,她觉得,父母的爱,她大可不必再肖想了。她还有更疼她的人,她不能让他们难过。只是,心中酸涩仍是难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