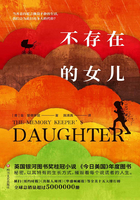1
妹妹亚纱开车前来松山机场接机,她这样向我汇而报之:
“这次你要在‘森林之家’住上一段时间,‘穴居人’剧团那些年轻人为此而欢天喜地。我知道剧团女干部的莽撞行为……她倒是曾来我这里商量过……她直接到东京找你谈话之后,剧团团长好像担心此前他们按照自己的行事风格谨慎准备的事情是否会彻底泡汤……“另外,关于镇上以前就来探询的那件事,就是哥哥获奖时修建的纪念碑妨碍新道路的建设,该如何处置那块碑的事,就像千樫嫂子所说的那样,我转告对方,没必要移动到应该放置的地方,请毁弃掉纪念碑的台座就行了。只是我想取回碑石主体,那上面刻有哥哥从妈妈写的诗句中选出来、并续上自己诗句的诗文。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自从立碑之后,哥哥一次也没有见过实物吧?那就去看一次吧。从这里到碑石所在的本镇大河滩需要一个半小时,你不稍微打个盹儿吗?”
随后,只见亚纱显出紧闭嘴巴的侧脸,缄口不语地驾驶着车辆,大致在她所说的时间内赶到了已将河沿建为公园的地点。经由新建的桥梁驶过河川,再穿越公园,就在国道辅路将由此笔直延伸而去的处所,一个角落暂时停下了道路扩建工程,据说是母亲种下的石榴树和山茶花已被清理一空,在裸露出的地面上,放置着一块据说是陨石的圆形石块。一旦走下河岸往上面看去,便会发现显出植物般淡青色的石块上只有五行文字,我知道那上面镌刻的是将自己用钢笔写下的字句放大后的字体。
让古义攀上森林的准备都没做,就如河水冲走般一去不还。
在不降雨水的季节里的东京,从老年及至幼年时期,我颠倒时序 回想起往事。
“并不像听说后想象的那么糟糕。”我说道。
“母亲开首的那两行诗句,从一开始评价就不好。”亚纱说,“有人讲坏话,说那既不是俳句(〖注〗 日本传统诗歌体裁之一,由五、七、五共三句十七音所构成的短诗),也不是短歌(〖注〗日本传统诗歌体裁之一,由五、七、五、七、七共五句三十一音所构成)……这倒也没办法,只是让纪念碑之会的顾问先生给叫到松山去, 被他责难了一番,说这诗是对美空云雀(〖注〗美空云雀(1937-1989),原名为加藤和枝,享有“歌坛女王”之誉,广泛活跃于影、视、歌、剧等领域)所作之诗的滑稽化模仿……“云雀写的是如河中的水流般,而我们的则是如河水冲走般。我对他说了,家母没有剽窃。我们本地人,把淹死在河里的,以及虽被救助却仍然被大水冲走的人称为河水冲走……一旦被河水冲走,淹死的人自不待言,就连得到救助的人,也会被大家视为其不久后将要离开村子。我当时还这样做了说明。
“哥哥当年承诺,只要让你去东京学习,将来就一定回到村里,却如同河水冲走般一去不还,就这一点而言,毋宁说这该是讽刺诗吧,我还曾这样告诉对方。建起纪念碑且了解哥哥情况的本地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当时倒是向对方表示‘第一行也许确实难以理解’,却因为对方是大学教师,还表示自己也曾写过关于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传说的书,因而无法接受我们的解释。尽管如此,还是按照哥哥寄来的底稿刻在碑石上了……“毋宁说,我怀疑那位教师是否真的理解了第一行。在我们家里,哥哥小时候曾被称为古义,而且,我的这位哥哥曾认为自己与同样被称为古义的分身一起生活,那位教师肯定不知道这些情况吧?我觉得他对哥哥的小说知之甚少……“假如那位教师通过研究传说来进行调查的话,是有可能知道所谓攀上森林,就是祭祀死去之人的意思,可是……”
“爸爸的遗体被挡挂在从这里延伸至下游的河中沙洲的哪里?你肯定不知道吧?”我说道,“说是遗体被送回来后不久的情景,是你人生最初的记忆……”
“古义哥哥当时对我说,你过来看看,围绕死去的爸爸躺卧的被褥转上一圈,有个死去的孩子躺在那旁边呢。在那之后过了大约二十年,从哥哥那里听说做了这样的梦,听上去如同笑话般,也如同悲苦的实话般,我觉察到这也许与你从爸爸死去的那条舢板上逃开的往事有关吧……“在脸上蒙着布躺着的大人四周转圈,绊倒后伸出的手触摸到了湿透的发束。由于回想起这个情节,我就相信哥哥坚持说的‘爸爸是被河水冲走而死的’。”
“在村子合并之前的、这个镇上的新制高中里,我不是只上过一年学吗?
“上美术课的时候,我们来到那座沙洲上写生。出身本镇的美术老师面对沙洲顶端的褪色柳树丛支起画架,画起油画来。我溜溜达达地走动着,那位老师招呼道,这里从过去就被称为‘长江先生被河水冲走后打捞上岸之处’,这与你家有关吗?爸爸水死在我们家里遭到否定,在外面却是谁都知道的事情。母亲在那首短诗中写入河水冲走的字样,恐怕就是出于这个缘故。”
从街道旁郁暗、繁茂的成排樱花树(说是已决定将砍伐一空)下走过,我们回到车子里,由这里向林中峡谷行驶大约二十分钟后,亚纱对我说起像是此前就一直在心里思考着的事情:“我呀,也是因为古义哥哥要了结‘红皮箱’这个悬案,细说起来,那还是我先说出口的,哥哥还说要在‘森林之家’住上一段时间,我听了后很高兴……不过,我也想到哥哥毕竟上了年岁。所谓上了年岁,虽说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件事地不断善后处理,在这个年龄上思考死的问题也是很自然的。
“同你一样,我也是老年人了,所以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可是呀,最要紧的问题,不就是在那之前吗?即使如此这般地对死亡有了心理准备,从现在开始直至那一天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的问题也还存在着。死亡这东西,即便你置之不理,它也照样会到来,在那之前的存活期间,自己就必须承担起责任来。
“结合妈妈那像是诗一样的句子……嗯,暂且称为俳句……来综合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那该不是留给回到这里观看碑石的哥哥的信息吧。让古义攀上森林的准备都没做,就如河水冲走般一去不还。
“比较之下,哥哥那三行倒是显得温和,表示自己确实没有回到这里,更是用(大概引用了艾略特的诗句吧?)这就是我,无雨月份里的一个老头儿的身份在思考各种问题。不过,与妈妈那两行比较起来,仍然是一种悠闲自在的应答。
“在妈妈来说,即使在作这个俳句的时候,哥哥依然还是古义,妈妈一直在操心该如何让阿亮攀上森林。不如说,我呀,觉得哥哥决心在‘森林之家’小住一段时间,就包含着这各种用意在内的、为让古义攀上森林而做的准备之一。”
随后,亚纱沉默着驾驶了一会儿车辆,便将汽车停靠在道路旁边:
“从这里沿着野兽小道般的坡道上山,就是通往‘森林之家’的近道。哥哥也还没忘记吧?今天比较晚了,你就在这里下车,我要直接回去,稍微休息一下就送晚饭过来,哥哥的行李也会一同送来。
“另外,曾在东京跟古义哥哥交谈的那位女性呀,明天,要和剧团的穴井将夫……你知道吧,这个人曾是塙吾良的弟子……到‘森林之家’来。她说呀,在哥哥于此地逗留期间,想要和哥哥你一起做的许多事情,她对你只谈了开头。明天,首先是剧团那些年轻演员也会前来为先前说过的纪念碑做善后处理。工作结束后,就与你商量今后的合作事宜。他们对此非常期待。那就拜托你了!”
2
亚纱叮嘱的所谓纪念碑的善后工作,就是只将被废弃的纪念碑上镌刻了文字的圆石,搬运到“森林之家”后面狭小的庭院里来,好像在和我一同前往观看那石块之前,她就已经决定了这程序。准备周到的亚纱似乎大清早便让小剧团那些年轻人从现场把圆石运了出来。
千樫从东京家里的庭院移植来的名为“大酒盅”的枫树和四照花以及我从岳母那里要来的石榴树,全都长成与后院规模相适宜的大小。对于将圆石安放在紧挨着庭院这一侧的方案,我表示同意。
箱形客货两用车到达了这里,车体上描画着请塙吾良写下的剧团名称“穴居人”放大后的字体。将森林中岩鼻(〖注〗由崖头凭空向外探出的部分)处砍伐一空后仅仅铺撒了砂石的前院里,同车前来的亚纱向我介绍了穴井将夫。我仿佛见过这位四十来岁的男人,他的确像是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朴实工作的戏剧工作者。身穿工作服般成套西服、此前曾见过的那位姑娘,正稳稳站在他的身边微笑着。亚纱应该知道姑娘与我的那次怪异相遇,却没有提及此事,只介绍了一句“穴井将夫和髫发子”。寒暄也是匆匆了事,穴井便让两个年轻人将一件用旧毛毯包裹、绳索捆绑的物件从客货两用车里抬出,进而引导那两位年轻人往后院而去,这两人用两根结实的四棱木料抬着包裹。
我刚要为此前之事对仍留在原地的姑娘表示谢意,亚纱便打断我的话头开口说道:
“她的髫发子这通用名字,可是与千樫嫂子有关呢!”
“最先把我们剧团团长穴井将夫称为‘穴居人’的,据说是塙吾良导演。我从亚纱这里听说,老祖母说是导演的妹妹家的千金好像髫发子似的,听说那位千金长得与我相似,也是因为与团长穴井这个姓氏的发音相近(〖注〗 在日语中,“穴井”的发音为anai,而髫发的发音则为unai,故有“发音相近”之说),我就说,那就改名为髫发子吧,那些年轻人就接受了这个名字。”
千樫为让母亲与孩子们见面而第一次把孩子们领到峡谷里来的时候,大女儿真木留着与眼前这位姑娘相同的发型,母亲认为这更像是女童的模样并为此而赞叹。我也从千樫那里听说过此事,据说母亲感叹道:“非常相称呐!过去呀,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只要留着这种发型,据说都叫髫发子啊,真就有了这种感觉呐!”
“妈妈与千樫嫂子说这话时,我也在旁边。”亚纱说,“妈妈还高兴地对我们说起有关髫发子这个名字出处的和歌,说是‘子规掠夏空,反复啼叫不歇停,髫发子小童,披发低垂遮项颈,梅雨霏霏天蒙蒙’(〖注〗 这段和歌出自《拾遗和歌集--夏》),她因为孙辈前来看望自己而心情愉快……”
为了让已经回到我们身边的穴井也能听懂,亚纱补充道:“由于这个缘故,千樫嫂子在峡谷期间就这么称呼小真木了。后来,我把这一切告诉了这里的髫发子。
“那么,我们去餐厅看看后院那些年轻人工作的情形吧……”
然而,当我们在餐厅的餐桌旁坐下来时,石块已经安放妥当,几个年轻人也还在小憩,似乎透过镶嵌在窗框里的玻璃打量着正在观看后院的我们的反应。我对亚纱表示了满意,她便向年轻人做出手势,等他们绕行到大门时,便与他们一同离去了。我们几个人留了下来,目光投向镌刻在石块上的文字。
“我们向亚纱请教了河水冲走的意思,”穴井说道。从侧面看过去,“穴居人”这个绰号固然是对其姓氏的诙谐模仿(〖注〗 在日语中,“穴井”与“穴居”的发音相同,均为anai),却让人觉得这也是来自他那充满野性的相貌--眼睛上方的眉骨骤然隆起,额头则从那里向后倾斜而去(这种富有观察力的幽默感,也是吾良固有的风格)。
“所谓古义,其实是我正思考着的、要纵贯性地把长江先生全部小说改编为戏剧脚本的主题。这实在让我吃惊。
“不过呀,攀上森林的准备都没做这句话,是否与长江先生小说里的神话世界相矛盾?本来,古义是作为幼年时期的长江先生的分身从森林飞降而来,其后自己又飞到森林中去的那个孩子吧?”
“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不过,碑文上的这个古义,却是我在孩童时代的称谓。家母使用这个名字,在向早已长大成人的我发出询问。如何处理自己的身后之事,与如何处理阿亮之事的询问重叠在了一起。为你的死所做准备的第一要事,就是安排阿亮登上森林--这就是家母在诗句中所蕴含的用意。”
亚纱回到这里告诉穴井:
“那些年轻人说是要花三个小时开车去小田深山的山里,然后再回来。他们干起体力活儿来精神抖擞,在别人家里也是举止得体,剧团‘穴居人’真是了不得啊。”
“对他们进行这方面训练的,是髫发子。”穴井说道。
即便加上后来的两个青年,餐厅也不显得狭小,我们在这里饮用着亚纱制作、髫发子端来的咖啡。
“穴井君说了,他们希望在哥哥这次逗留期间能够对哥哥有所帮助,与此同时,也期望哥哥协助他们的戏剧活动。就请穴井君说明一下吧。”
“哎呀,与其说我们对长江先生有所帮助,倒不如说我们有一个整体考虑长江先生所有作品的戏剧计划,您如果难得地在这里小住一段时间的话……这都是只顾自己的如意算盘。
“亚纱告诉我们,您将在这里小住一段时期。商量这事时,亚纱提出在此期间能否请您听一听我们一直在推进着的构想。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亚纱说,哥哥似乎要借这次小住总结迄今为止的所有写作工作,应该能够把哥哥的计划与你们的计划协调在一起。
“在那一过程中,打算请您浏览我们此前所有作品的摘要。现在,就先谈谈把长江先生的作品全貌置于视野中,我们想要从事的工作的轮廓吧。
“迄今为止,我们从长江先生的作品中,以自己的视点抽出若干场面,并对其中个别场面做了戏剧化处理。我们现在所考虑的,是要展开这一切。当然,这个想法要以您此前的作品为基础,同时借助这个机会,我们考虑采访长江先生本人,并将这一形式引入戏剧之中。倘若能够得到长江先生的协助,得以多次采访的话,就用我们剧团的手法加以重构。这样一来,接受采访并进行讲述的角色,将由演员(还要饰演其他角色的‘穴居人’演员)扮演长江先生。至于出现在长江先生讲述中的第三位甚或第四位人物,也都由演员们交替饰演。我要说的就是这么一种手法。
“在持续阅读您作品的过程中,我曾将其改编为若干戏剧作品,这次则打算以古义这个人物为基轴进行总结,从长江先生的全部作品中,该如何塑造古义这个出场人物的形象呢?这个构想已经成形了。据亚纱说,长江先生您将整理此前的所有作品并加入新资料,我们剧团如果充分做好目前已有可能的、与长江先生的对话,我们不也就能够为您的这项工作发挥一点儿作用吗?毋宁说,我们哪怕只在查对长江先生此前所有作品这个层面上发挥一点儿作用,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哥哥,你曾经说过,要借这个机会……我对‘穴居人’的成员们也说过已成悬案的那件事……在这个地方,似乎首先要对照‘红皮箱’里的资料,重新阅读自己此前的作品,并且想要把这一切联接在新作上。我对他们只说了这些。
“以前你不也说过吗?虽说试图重新阅读旧作,可是自己独自一人无论如何也持续不下去。于是我就在考虑,假如让穴井君和他的伙伴们也一同重新阅读的话……穴井君和髫发子也积极地接受了我的设想。”
对于借助穴井将夫阅读我的作品,并确定新方向从而把握古义形象的意图,我也产生了兴趣。
“因此,即便不是尝试,即便对于我的采访以古义为主题而展开,这也挺好呐。”我说道。
“即使现在开始工作,我们也是可以的。”髫发子说道。
我将目光朝向亚纱而非髫发子。年轻时,亚纱经常为我岔开来自这种女性的挑衅。然而,亚纱却是无动于衷,一副正等候着的神态,髫发子则从她那对于女性来说过于庞大的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取出录音器材。与最近大家都在使用的小型录音机不同,髫发子取出的是样式古老、却显然是专业的录音器材。不过,髫发子和穴井将夫毕竟没有立刻开始录音。髫发子只是把那些器材放置在餐桌中央,穴井和亚纱则一同注视着器材而已。如此这般,便显示出了“穴居人”与我之间的协作配合的手法。也就是说,髫发子、穴井以及亚纱事先已多次商量并准备好让我接受采访。我虽然有这种感受,却没有产生反感。
3
穴井将夫稳稳当当地说道:
“在尚未得到长江先生应诺的情况下,我们便开始构想戏剧新作(曾与亚纱商量过此事。虽说亚纱认为沿着这个方向构思不会有问题,却也表示一旦进入与长江先生之间的斡旋阶段就要慎重)。您也知道,小剧团的主持人视基金会提供的资助金为自己的目标,为了应募这些资助金,就有必要让上演的作品获得某些奖项。‘穴居人’因戏剧版《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而得到认可一事,尽管您没有亲眼看到舞台上的演出,却也知道这个情况吧?此后,我们将提供新剧作的构想梗概。最初,我们打算选择那部原著的续集,然而,《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却没有续集。于是,我们便转而寻找贯穿长江先生所有作品的符号。
“那就是古义!古义这个人名,是长江先生在作品中分别赋予若干不同对象的名字。不妨举一个例子--与长江先生孩童时代曾一同生活的那个与您本人一般无二的孩子。您把如此认定的对象,称之为古义。
“有一天,古义从空中往高处走去,也就是说,他回到森林里去了。也就是说,这个古义呀,他有着人的身体,却在空中行走,飘飞到高处去了。他超越了实际存在的孩子,是一个超越性的存在。我在向基金的委员会提交的梗概中,试着说服他们,将如何作为具体人物来描绘这种超越性存在。我考虑在演出中寻找最单纯的方式来体现,或者在舞台上赋予角色以实际形状,或者只是让观众意识到即可。至于素材,我已经从长江先生的全部作品中抄录下来。这种制作卡片的方法,是我在学生时代从您的随笔作品里学到的。
“暂且不去考虑最终能否存留至舞台演出,目前,我们在排练场备齐了小偶人。在制作偶人时,髫发子用碎布块拼接起外形,再将内芯塞入其中。我们把偶人放置在舞台上、从观众席所能看到范围内的最高处。我们拥有在其他戏剧中曾使用相同偶人的经验。古义这个偶人从那高处俯视着下面,这将给在舞台平面演出的男女演员带来影响。仅仅如此便可发挥出效果……这次应该说是古义效果……吧。
“有关古义的第一个例子,我记得作曲家簧先生曾表示,在长江的作品中,自己喜欢的是那个形象。我就根据这段话语从长江先生初期的短篇小说(〖注〗 1964年1月,大江健三郎于《新潮》杂志发表短篇小说《空幻的怪物阿贵》,这是作者第一部以残疾儿为主题创作的作品,与半年后出版的《个人的体验》有着显而易见的血缘关系)中找了出来。”
“说的是青年音乐家那个死去了的婴儿如袋鼠般大小,身穿棉布贴身内衣浮游在空中的那段内容,是一个名叫阿贵的……”
“是的。叙述者是一个年轻人,陪同音乐家一起散步……这种设定已经显示出音乐家的心理状态不稳定……那位课余打工的年轻人认为,雇主所看到的幻影只是他内心想得太美所致。不过,正当年轻人因为工作关系而陪同音乐家散步之际,却在狭路上与驯兽师领着的十多条杜伯曼犬……说到这十多条的数字,倒是显露出年轻小说家的夸张癖,缺少真实感……不期而遇,总之,由于音乐家过于沉浸于袋鼠大小的婴儿,一阵恐慌便袭向年轻人,他担心音乐家本身该不会遭到杜伯曼犬的袭击吧?然而,他却什么都无法做而闭上了眼睛,只是从闭上的眼睛里流出泪水……”
“令人难以置信的温和的、一切温和中最为核心的温和的手掌抚上我肩头。我觉得这是被阿贵所触摸。”
“是的,我重新读了这一段,年轻人觉得阿贵的手掌触摸着自己肩头,我认为那大概是古义的手吧。随后,我将其改编成这么一个场景--古义置身在与浮游于空中的婴儿相同的高度,他从那里俯视着小说家。
“与此相联接的,是您在二十多年后创作的长篇小说《致令人眷念之年的书信》(〖注〗1987年10月,讲谈社出版大江健三郎的长篇小说《致令人眷念之年的书信》)中最后的场景。死去的义兄与其亲友全都在人工湖中的小岛……‘令人眷念之年’的小岛上。这般情景,在岛上,阿亮用的应该是阿光的名字(千樫在故事中则用阿由这个名字表示),古义就变成双重性存在,这情景便能够与先前的场景联接到一起了。我们呀,把刚才所说的那一页复印后带来了,就试着朗读一下。文中所说的有威严的老人,是您引用了但丁的炼狱岛上那位非洲的卡托(〖注〗玛尔库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前95-前46),古罗马政治家,因反对恺撒将罗马共和国改变为独裁帝国而起兵抗击,兵败后被困于孤城乌提卡(Utica),由于不愿被俘,更不愿看到贵族共和国的覆灭而自杀。但丁非但不将其自杀视为罪行,还高度评价卡托为自由而舍弃生命的行为,故此选择其为炼狱监管者并预言其终将升入天国)”:
时间像循环一般不断流变,义兄和我重新躺卧在草原上,阿节君和妹妹一同采撷着青草,如同姑娘般的阿由与阿亮也加入到采摘青草的圈子里来。阿亮由于年幼和单纯,残疾反而越发显得纯朴和可爱。晴和的阳光辉耀着杨柳嫩芽上的浅绿,高大的日本扁柏树的浓绿则更浓了,河对岸山樱的白色花房则不停息地摇曳。威严的老人应当再度出现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所有的一切,全都恍若循环的时间中平稳和认真的游戏,急忙奔跑上来的我们,再一次在高大的日本扁柏之岛的青草地上玩耍……穴井将夫的朗读给我带来强烈的冲击。我觉得自己正在用耳朵确认演出家穴井的实力。
“……透过训练有素的声音,在舞台上表现自己写下的文章以及讲话的记录,你还没怎么体验过吧?”
亚纱话音刚落,穴井将夫便像是获得力量般直率地说道:
“包括这些地方在内,应该存在着古义隐喻的重点。当然,髫发子表示她如果参与的话,也是会下工夫的吧。
“‘穴居人’并不是团结得坚如磐石,不过正因为如此,反而有可能给长江先生这一次的工作带来一些刺激吧。况且,在大学的日本文学专业里,目前好像也没有研究长江文学的团队……”
“这么直截了当地说话,原本顺利的事情也不会顺利了。将夫君,”亚纱接着说,“就把这一切视为能相互为各自的创作活动带来积极刺激,你们就这么缓慢地向前推进吧。将夫君说是髫发子还有其他想法,髫发子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一点的?”
“我在积极关注此事。”刚才凝神听讲时,髫发子仿佛由梳着髫发的女童原样变成了三十来岁的女人,只见她拂去先前听讲时的沉思表情,注视着我说道,“我认为无论对于穴井将夫还是长江先生,这都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合作。我也有些问题想要直接向长江先生请教……”
“你们不停地这么逼问,哥哥可要更加畏惧了,啊哈哈!哥哥本身的工作是要解读‘红皮箱’里的资料。不过,与其立即着手于这项工作,我对‘红皮箱’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嘛,不如不用那么着急,请从容地开始这项工作吧。
“那么,去小田深山转上一圈的那几个年轻人也该回来了吧!今后有关用车的事情还要仰仗他们,不邀请他们一起用晚餐吗?”
4
隔周的星期一上午九点钟,“穴居人”的箱形客货两用车抵达了这里。除了穴井将夫和髫发子,还有上次也曾来这里的剧团两个演员。说是考虑到交通拥堵,六点之前他们就从松山出发了,这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当然是个负担。他们睡眼惺忪地寒暄了几句,然而一旦亚纱也加入着手将一楼部分改建为小剧场的工作,这两人便干劲十足。
他们似乎习惯于体力劳动,而此前也确实有些需要这种体力的工作,那就是在髫发子和亚纱都已同意并做了准备的“森林之家”打造共同生活的基础。亚纱倒是说过,嗯,是暂时的室内调整,可是规模很快就超出了我的预想。把我卷入“穴居人”体系、反复接受采访,这本身就是一种戏剧手法。而且为了这个目的,把亚纱此前一直借给“穴居人”使用的“森林之家”当作这种场所,好像也非常合适。早在星期日,亚纱就独自初步收拾过家里,现在她则在这里指挥着新来的年轻人。
二楼西边的顶端,是我的书库和工作场所兼卧室,此外还有一个房间,这些地方不得擅入。
一楼东边的北半部,原本设计为会客室,却从不曾使用过。南半部是大门和狭小的门厅,还有通往二楼的楼梯和客用厕所。在门厅处用门扉连接起来的,则是北侧的餐厅和低矮一段的客厅。客厅朝向前院,照例用镶嵌着的大玻璃板与前院隔离开来。在更靠西的地方,是为其他亲属来这里时作为卧室而修建的两个房间以及浴室、盥洗室和厕所。
“要让他们把客厅的桌子、椅子,还有可以移动的书架和沙发、电视机等所有物品都搬到会客室去。”髫发子说,“去年,亚纱说是预料长江先生根本不可能回到‘森林之家’来,在她的建议下,就把一楼所有空间都用作‘穴居人’的排练场了。只要把客厅里的物件全都搬出去,南侧那三分之二空间就可以当作舞台使用。再把餐厅的餐桌收拾一下,那里也就可以当作观众席。”
“以往我每年来‘森林之家’的时候,也只在二楼读读书,多少做点儿工作,除此以外,大致都躺卧在客厅西侧的沙发上。只把沙发给我留下就行了,其他的任由你们搬动。过去,亚纱和村里的年轻人组建剧团那段时期也是这样,不过呀,你们也不需要那么循规蹈矩,使用过后,就没必要把家具类物品从会客室搬回到客厅里来了。我也曾一度把这里当作小剧场使用,亚纱对你们说了这事吧?我邀请曾为阿亮创作的小小曲子录制CD的演奏家们在这里举办了音乐会,就让母亲和亚纱以及很少几位客人坐在舞台前和餐厅里,把钢琴放置在客厅玻璃窗下的、用砖块铺垫得高出一阶来的地方……由于这里的天井最高,所以音响效果也不错嘛。”
“我们以后也在这里举行各种活动吧。”髫发子说道,“当前的任务,就是在清理好的舞台空间里,穴井将夫和我要采访长江先生。如果把采访整理成剧本的话,就打算以舞台排练的形式演演看,我们也说到尚未请长江先生观看‘穴居人’的戏剧演出,因此想要把《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戏剧精华版表演给您看。”
说完这些后,髫发子跑到餐厅,将双手撑持在隔开餐厅和客厅的柜子上环视着客厅,还抬头打量了天井的高度并露出满意的表情。
“‘穴居人’的公演,通常都把观众席设置在与舞台同高的平面上,以方便观众从那里往下看。至于这里嘛,如果您能想象观众同时还能从大玻璃墙对面观看着这里,那我们所要表达的感觉也就传达出来了。”
除了留下一条沙发,剧团的两个年轻演员,几乎也只是这么一对,已把客厅里搬运一空。从原先放置家具的地方开始,髫发子用吸尘器清扫着客厅,在此期间,我打开镶嵌着的玻璃板两侧以便通风。将夫和髫发子并肩望着玻璃墙外侧的植被,那里有千樫用诸多花盆和露天栽培植物组成的一小片玫瑰花丛,此外还有长势茂盛的石榴、四照花和挺拔高大的白桦(数年以来,千樫无法前来这里,便委托亚纱代为照料)。
“这里汇集的树木,跟森林中绝大多数树木的品种不同啊。”穴井说,“当然,即使在松山,也可以看到作为行道树而栽种的四照花,不过那都还是些小树,白桦树不也少见这么高大的吗?”
“千樫先是从北轻井泽移植到成城的庭院里,其后又把培育了二十年之久的树运到了这里。也有些树被猛烈的山风吹断了,不过,在这里由种下种子并长成的树,也长到了相当的高度。当时,千樫也还年轻,在这里勤奋劳作……”
“无论是栽种玫瑰的花盆如此之多,还是大胆地把树木培育长大的做法,在她的身上,总觉得有一种与塙吾良先生相似的东西。”穴井说道。
“吾良并没有特别关注过树木吧?”
“即使在培养阿亮的音乐才能的做法上,我也感觉到千樫嫂子有某种与吾良先生相近的东西。”亚纱说,“在我们家的血统里,可没有这种东西呀。在高中时第一次遇见吾良先生,哥哥你不是一下子就被那种东西给迷住了吗?”
“总之,他当时非常特别。另一方面,吾良对我父亲的水死很关注。除了家人以外,我第一个对他讲述了那个梦境。”
“吾良先生也把长江先生视为特殊的存在,他曾说过:‘因为那家伙拥有古义。’也正是因为这样,长江先生和古义这个形象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内心,成为今后想要好好干上一番的根据。
“所以……现在,舞台的基本形状已经成形,为了让您了解我们将采用何种形式推进对您的采访,又打算将其改编成怎样的舞台剧本,我们可以从古义说起吗?塙吾良导演似乎有一个将其改编为电影的腹稿,却由于他没有说出更多,我也就只好通过您的小说来了解了。因此,能请您用自己的声音讲述有关古义的情况吗?”
我为那个自然的流程所吸引。与上次一样,髫发子把录音设备放置在隔开这里与餐厅之间的柜面上,对我说明夹在衣领边的麦克风。穴井则让年轻人把刚刚收拾到会客室里的扶手椅重新搬过来。这把扶手椅随即被安放在了舞台中央。我觉得自己也被这按部就班的流畅所吸引了。
“请您用尽可能让自己舒适的姿势坐在这里。从现在开始,每个场景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做法,我姑且站在您的斜前方,用简单的方式与您对话。假如我感到疲倦的话,会把搁置在那边的椅子搬过来坐下。长江先生坐着说话如果觉得腻了,就请您自由起身或是四处走动。也是出于这个考虑,髫发子在您身上安装了麦克风……“长江先生就那么坐好……您在正前方所看到的,请想象为是我们安放在后院里的圆石。您所思考着的那两行诗……也许应该称之为俳句……就镌刻在那块石头上。其中第一行是:让古义攀上森林的准备都没做。
“较之于出现在您小说中的古义,这个古义具有别的意义,是这样吧……”
“这个句子是我母亲写下的,因此要了解她为古义这个词语赋予了什么意义,就必须解读这个句子。此后我要说的也是我一直在小说里写着的内容--在母亲写下这个句子的晚年间,说到古义,是指头部带着瘤子降临人世的孙子阿亮。
“家母对于将来的阿亮之死放心不下,是认为我全然没有做好准备吧。她当然知道死亡正在逼近自己,也许她还想到,即使对于自己的儿子、儿时被称作古义的我来说,死亡也绝非遥遥无期。因此,那个古义、也就是我本人‘在做着攀上森林的准备吗?’这种忧虑,就被吟入这个句子之中。这其中含有两种意思,家母在批评我,认为需要有人照料阿亮,好让他安全可靠地攀上森林,这一切正是我的工作,可我却忙得连自己的准备都顾不上,狼狈不堪地彷徨徘徊。
就如河水冲走般一去不还。
“续着这两行,我便写出了自己那三行,我觉得被准确地说中了,感到我确实真就是那样。
在不降雨水的季节里的东京,从老年及至幼年时期,我颠倒时序 回想起往事。
“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过呀,还有一点,我想结合这一切说说古义这个称谓对我而言尤为重要的程度。通过阅读我的小说,你们应该知道了吧。
“首先,古义出自于我的真名,我在幼儿时期被家里人唤作古义。然而,我本人却和一个与自己同年同岁、体态容貌也与我一般无二的、也被我称为古义的另一个幼儿非常亲密地生活在一起(是我认为生活在一起)。
“不过,在某个时候,那位古义却独自一人、也就是撇下我而飞上森林里去了。我对母亲说了这事,母亲却不予理睬。因此,我就持续不断地反反复复地告诉母亲,古义是如何离开我们家而远去的。亚纱她们都说,这就成了我后来从事小说家这个职业的原因。
“那一天,古义站在面对河流的里间走廊上(我自己如同因晃动而重影的照片一般,也紧挨着古义站在他的右侧,直至今日,从那个视角看过去的记忆仍未消失),他把碎白点单和服的衣袖搭放在扶手栏杆上,眺望着对岸的栗树林,宛若想起一个小游戏似的,踏着木栏下方防止地板端头翘曲的横木条爬上了扶手。古义张开双臂,像是保持平衡般一动也不动……然后他凭空踏出一条腿,再跟上另一条腿,摇摆着两只手水平地行走起来。
“古义越过家母种植玉米的旱田,越过旱田顶端的石墙,越过低下一截的河滩,一直走到河流中央的正上方,再重新将两条碎白点衣袖笔直展开在身体两侧,宛若大鸟一般乘风而去。从一直站在走廊上的我的位置望过去,古义很快就被屋檐遮蔽而看不见了。不过,当我从走廊探出身子仰望天空时,只见他描画着螺旋形越飞越高地飞走了。
“然后,就看不见了。我曾不断地对母亲讲述这件事,母亲却全然不予理睬,好像那个与我长得一般无二的孩子从来就不存在似的。
“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某一天,我被卷入到一场事故当中。古义前往森林高处之后不久(对岸斜坡上的红叶已是一片鲜红),在一个满月之夜,我感觉到了动静,我走出我家前面的道路一看,背对着我站立在那里的古义沉默不语地开始往前行走。他拐上村公所和神社之间的坡道,沿着洒满月光的狭窄小路一个劲儿地向山上走去。我应该是一直紧随着他的身后行走的,可是醒过神来时却发现,自己正蹲在密林深处那株高大的米槠树的树洞里。古义不见了!天亮了,树洞外面正下着雨,黑红色的红叶林被雨水打湿……“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由于高烧,我身上如同火团一般,正被腐烂的干燥木屑所掩埋,被消防队员从中抱了出来。我被盖上防雨斗篷,在充溢于森林间的雨水气味中被带下峡谷。
“好几天之后,退了烧的我了解到一个奇怪而扭曲的情况(在孩子的头脑里,只有扭曲这种感觉,自己能够用语言如此表述都是后来的事),那就是家母这次也站到我这不可思议的一方来了。我在满月之夜从家里消失后再没回来,从翌日起就一直在下雨,流经峡谷底部的河水已经微浊(〖注〗 原文为“笹濁り”,读为“sasanigori”,在当地表示河水略微浑浊的意思),随后明显地变成大水,轰响着奔流而下,任谁都会认为,孩子是被河水冲走了,一如那块圆石上镌刻的诗句:
就如河水冲走般一去不还。
“就成了这样一种人……与我续写的诗句不同,那是在秋末的雨季,由于是发生在那样一条峡谷里的意外变故,母亲因寻找不到幼儿而跑进消防队,首先肯定会要求‘帮我去河里搜救!帮我沿河而下到下游搜救!’吧?
“然而,家母却恰恰相反,请求‘帮我攀上森林’。由于天降大雨,进入森林的道路已然变成另一条溪流,家母却坚决要求大家逆水而上,进入到森林深处。在此期间,雨也停歇下来,消防队员转而决定深入森林,就把因感冒而发烧、像是精神失常般踢打……或者说像是小猪仔似地抵抗的小东西,从米槠树(这株巨树犹如森林中的神殿一般,无论大人小孩全都知道)的树洞里抱了出来……“不可思议吧?家母为什么不认为我被河水冲走,反而知道我攀上了森林(或是某种直觉吧)?村里的大人经常会奇奇怪怪地对孩子说些捉弄人的话,直至很久以后都在嘲弄我说:小哥儿(就是‘你小子’的意思),你想古义想疯了,就闯进了森林,给消防队找了个天大的麻烦呀。”
5
第一次录音一结束,穴井将夫便兴高采烈地说:
“今天,本来只打算请您体验一下我们的系统,却成了富有成果的采访。当然,对于长江先生来说,今后还有研究‘红皮箱’的重要工作。不过,如果您能用这种方式偶尔与我们交流的话,构成戏剧的基础材料很快就会成形。就您的工作而言,这就如同创作短篇小说般精心推敲,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则是把这一切重新回馈给您……如果您能够让我们如此进展下去的话,那就太好了。下周前来拜访您之前,髫发子会把今天的录音内容输入到电脑里去。到时候先请您阅览其中内容。
“长江先生演讲过后……经常把得到的相关速记登载在杂志上吧。我大致拜读了那些材料。不过,若是以‘穴居人’的做法看起来,那就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了,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面向戏剧。看上去,您在演讲时所说的那些未经加工的口头话语,会反复出现一些无用之处以及不一致的现象……不整理这些地方,可是……也就是说,我打算精心推敲长江先生的口语文体中隐含的肉体性并研究那个方向。”
髫发子则用更为沉稳的口吻接过话头说道:
“在您的协助下所做的这个采访临近结束时,长江先生,关于其后如何讲述下去……您当时似乎有两个思考方向,却在为做何种选择而迟疑不定。”
“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啊。”我赞同地说道,感受到了髫发子所拥有的观察力。
“我习惯于边录音边注意听。”
“正说着话的我设想能够看到玻璃对面那块圆石,就考虑是先把圆石上第一句中的古义与第二句中的河水冲走联接在一起讲述,还是先把话题引往其他方向,在如此思考之间,就显得迟疑了……”
“我还想听听您所说的另一个方向。”穴井将夫说,“那是您在此前创作的那些小说中表现过的内容吗?”
“的确如此。毋宁说,这与你最近从我的作品中引用的部分相近。自己的母亲是怎么想到米槠树洞的?……刚才,我想要说说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她经常对我讲述的森林里的民间传说中最有趣的内容……我已经完全按照家母的语调写在了《M/T与森林里的奇异故事》(〖注〗 1986年10月,岩波书店出版大江健三郎的长篇小说《M/T与森林里的奇异故事》)之中。刚才,我想起了这一切……“家母总是对我说:在咱们这地方,流传着叫做‘森林里的奇异’的民间故事,讲述的方法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不过呀,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穴井将夫并未花费多少时间,便从大笔记本中找到引用之处,并高声朗读起来:
现在,咱们珍惜一个个各自的生命,以往在“森林里的奇异”时,虽说是各不相同的各自的生命,却是一个整体。那里充满巨大的、难以忘怀的怀念。不过那时候呀,我们离开“森林里的奇异”,来到了外面。由于是一个个各自的生命,一来到外面呀,就七零八落地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不过呀,在自己的生命里呐,对我们原本在“森林里的奇异”里的事,不是还感到怀念吗?!
髫发子好像也曾与将夫讨论过有关“森林里的奇异”的解释,她接着刚才的引文这么说道:
“失踪了的幼儿并非落入发大水的河里什么的,而是这个幼儿有着特殊的方向感,眼下正要回到‘森林里的奇异’去。赶在这一切尚未实现之前,令堂对消防队员说出了米槠树洞这个通往‘森林里的奇异’的入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段往事就说得通了。”
“故事倘若如此展开,就完全吻合我们正要创作下去的话剧中的一个核心元素。”穴井将夫对髫发子的总结表现出信任,这也是我所感觉到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