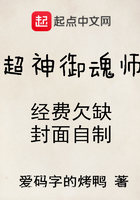八月十五,骆驼驿站的招牌用一块大红绸布包着,宋祭酒请了街坊邻居,东街的屠夫,西街的菜贩,还有周猩猩的老师冯老先生等众人,再加上更夫半夜的一连数十天的广告轰炸,更有吃饭送牙签的开业酬宾。闻讯而来的还有身着各种服饰的驼商。驿站正中有个突出的舞台,西域十二乐坊正在舞台上吹箫鼓瑟,跳着胡旋舞。盖米尔骑着驴子在驿站四周巡逻,驴子身上新铺的毛毡上有“武装巡逻”四个红色大字。朱厚宽提前几天就劈好了柴,今天在前台收账和登礼。后堂里宋祭酒找来的厨子和帮厨的忙的不亦乐乎。在乐队休息的间隙,巫己在舞台上客串些祭祀舞,顺便变些小把戏,宋祭酒在门口迎接着各路客人。
驿站对面是两个大木槽,一个盛满水,一个盛满草。仆人们牵着骆驼、马匹在饮水,补给粮草。几个喽啰守着一叠毛毡,上面写有“六神附体正气水”几个大字,还有几个小字,“骆驼驿站战略合作伙伴”。喽啰们给每个来往的牲畜都换上了印有广告的毛毡。
巫己走到宋祭酒跟前,小声说道:“祭酒大人,饭菜已上桌,吉时已到!”
鞭炮声响起,八个枪手骑在毛色鲜亮的八匹骆驼上,站成一排朝天开始鸣枪。这几个枪手是六神教的大把头带来捧场的。周猩猩听到鸣枪声,从后堂窜到大门口,高兴的直拍胸脯。当看到冯老先生也在场,周猩猩冲老师做了个鬼脸跑进了驿站。鸣枪完毕,大把头和宋祭酒一起从两头把招牌上的红绸布拉了下来的,显出“骆驼驿站”四个烫金大字,这四个大字出自冯老先生之手。冯老先生在门口驻留了一会,看着招牌上的字,捋着胡子摇头晃脑,但很快就被客人们挟裹着进了驿站。
驿站内划拳声、小二的吆喝声夹杂着各种胡语,热闹非凡。巫己提了块鸡腿,递给门口巡逻的盖米尔,“兄弟辛苦,先抽空垫一垫。”
盖米尔接过鸡腿,掏出一把小刀切着吃,没把握好,肉片掉到桌上。“用嘴啃不就得了,还装什么贵族。”巫己笑道,“当年我也是商朝的贵族,现在呢,老兄还是入乡随俗为好。”
“胡知县驾到!”一声锣响,胡知县从骄子里走下来。左右随从打着两只白色的灯笼。
巫己见了,自言自语道:“开业乃喜庆之事,大白天打个白灯笼,晦气又诡异。”
宋祭酒一干人等忙上前跪倒在地:“草民不知胡知县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随从递给胡知县一只手帕,胡知县擦了擦眼睛:“天都塌下来了,还计较什么规矩!”
“天塌了?”宋祭酒不解。
“昨日收到八百里加急快报,当今圣上已于六天前驾崩了!”胡知县用手帕擦着眼泪,啜泣了几声。人群里并无人呼应,只是有个小孩子在哇哇大哭,抱小孩的老婆婆拍了怕小孩的屁股:“别哭!胡知县这次真的来了。”
胡知县见大家并无反应,把手帕递给随从,“不是我不请自来,我来就是告诉各位乡亲这件事的。”胡知县吸了吸鼻子,“厨子手艺好像还不错。”
“胡大人快里边请!”宋祭酒忙起身,门口让开一条通道。“天子陨落,食不甘味哪!”胡知县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大步进了驿站。胡知县走到前台,朱木匠下意识的把记账本抱在了胸前。奏乐顿时停了下来,桌前吃饭的人们都停了下来,朝胡知县这边看了过来。“大家继续!”胡知县两手举起,往下压了压,“本知县向来与民同乐。”
盖米尔牵过胡知县随从的马匹,栓到了马槽上。巫己在抬头看着天。“这么毒的太阳,你不怕眼睛看瞎。”盖米尔说道。
“我又不是向日葵,成天盯着太阳看,我在看云朵!”巫己眼睛一眨不眨。
盖米尔也抬头看了看天,“云朵有什么好看,你会天气预报?”
“你不懂,我会云计算!”巫己道。
“云计算?朱木匠把算盘打的吧啦吧啦的,还用的着你算账?”盖米尔揉揉眼睛。
“你又不懂了,算账只是雕虫小技,我这是看云朵,算凶吉。”巫己还是盯着天上的云朵。
“我知道我还是不懂,可是你不是以烧骨头来算凶吉吗,怎么又改看云朵了。”
“烧骨头增加碳排放,云计算低碳环保。”
“您签署过<京都议定书>?”
“你没发现我现在连屁都不放,睡觉都不打呼了?”巫己用手把下巴托了托,“斜45°看天,多像个忧郁的占卜者。”
“你能看出什么来?满天的棉花糖!”
“你看这云朵有的蓬松如棉花糖,有的纤细如蚕丝,不好!有一片乌云飘了过来!”巫己叫道,“看来胡知县此行来者不善哪!”
“是快要下雨了,你想多了吧。”盖米尔不屑的说道。
宋祭酒与大把头陪着胡知县在舞台前的桌前坐定,胡知县啃着烤羊排,咂一口酒,“此次进京奔丧,路途遥远,花费颇为不菲,然几月前洪水泛滥,县衙开仓赈灾,钱粮已所剩无几。”胡知县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奈何我边关小吏,有心无力,无法进京致祭哪。”说到这儿,胡知县从袖中取出一条白布条,系在头上。
“据我所知,按照礼部的规定,一般皇帝驾崩,各地衙门就地设灵堂致祭,不必亲自去京城。再说了,等你赶到京城,估计圣上的头七都过了。“大把头说道。
胡知县瞪了大把头一眼,“哪怕我到皇帝陵前磕个头也算尽孝了。“胡知县掰着羊排,”你的羊排烤的火候不够,都掰不开,来人啊,给我把羊排劈开!”胡知县把盘子放到了桌子中间。
胡知县左侧的一名随从抽出一把刀,朝盘子里的羊排劈去,羊排分为两半,盘子倒是完完整整的。胡知县把羊排拿起来看了看:“咦,骨髓怎么没出来?吃骨髓补钙。”
宋祭酒心里暗想:“肋条里哪儿来的骨髓,大人,您不光缺钙,还得补补脑子了?”尽管非常不愿意,宋祭酒还是伸出胳膊放在桌上。
胡知县给师爷赛皮匠使了个眼色,赛皮匠坐了下来,把手伸入宋祭酒袖中,两个人的手在袖子里摸索了一会。宋祭酒皱皱眉头,咬咬牙,最后点点头。
胡知县哈哈大笑,举起酒杯道:“痛快人!合作愉快!”宋祭酒苦笑道:”愉快!愉快!“胡知县干完了一杯酒,起身说道:”胡某还要去京城奔丧,此地就不多久留了。宋祭酒,可要好生经营好咱们的生意。“大宴宾客完毕,最后一项目议程是合影留念。驿站门口已放好了一排板凳,胡知县在中间坐定,两边分别是宋祭酒和大把头。画师是冯老先生,听说他从西洋传教士那里新学了油画。虽然已到傍晚,但西域的光线仍然刺眼。冯老先生支好了画板,花花绿绿的颜料罐子摆了一地。冯老先生气定神闲,“大家一起喊妻子!”
胡知县挠挠头,“我还是喊小妾吧,她看照片上我的口型不对,晚上会拧我耳朵的。”等了半个时辰,胡知县有些不耐烦了,他喊道:“冯老先生,把我画仔细就行了,其他人用简笔勾勒一下就行了。只要突出中心思想就可以了。”
“我的老师没教我西洋画法和简笔的混合画法,知县大人莫急,速速就好。”冯老先生捋捋胡子。
“我这不是还要赶着去奔丧嘛。”胡知县摇摇头。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可行不可行。”朱木匠指着门口一块沙地,“大家到沙地上趴下来,把自己的身形印到沙子上,让冯老先生慢慢描画,大家便可各自忙各的,不耽误大家时间”。
胡知县听了,招呼几个手下过来,他走到沙地前,几个手下把胡知县抬起,脸朝下,慢慢的放到了沙子上,一个四肢张开的人形便出现在了沙子上。胡知县嘴里吐出一口沙子,手下忙递上一碗水,胡知县漱了漱口,“此计甚馊!”
送走了胡知县,宾客们渐渐散去,只剩下大把头和宋祭酒一干人等。宋祭酒摆了一桌,答谢大把头的赏光。
酒桌上,大把头悄悄问道:“你方才与胡知县的师爷在袖中做的什么交易?据我所知,本地买卖骆驼马匹之类的大牲口时,才会袖中交易。“
宋祭酒无奈的说道:“跟胡知县打交道,只能用大牲口的交易方式。胡知县这匹老骆驼,口可不轻哪!“
“祭酒兄肯定放血了!“大把头举起酒杯,”老兄,这杯酒权当安慰了。“
“谁?谁要放血了?“朱厚宽放下手中的筷子,慌忙掏出一条毛巾捂在额头上:”巫己,救我,我又要晕血了。“
夜色降临,驿站门口的“7X12时辰”的灯箱亮了起来,宋祭酒正招呼大家打扫卫生,进来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妇,拿着半只破碗,低头站在门口。
宋祭酒见状,摇了摇头,安排人从后厨端来一碗肉和一碗汤。宋祭酒搬过板凳招呼道:“请到里面就坐,不要钱的。”
老妇人径直走到酒桌前,一脚踩到板凳上,用手抓起肉就吃。“小心烫着!慢慢吃,还有。”宋祭酒抱着周猩猩出了门把尿。
等把完尿,周猩猩在宋祭酒怀里把玩着拨浪鼓,路过老妇人的时候,他手里的拨浪鼓突然丢到地上。老妇人一惊,端着没吃完的半碗肉冲出了门外,回头看了看周猩猩,消失在夜色中。
“那个老婆婆好奇怪。”朱木匠在前台对着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