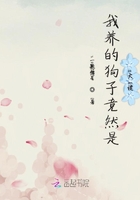——回望建设街112号
那日,交出了原有的业务,拎着一摞书走出了工作近20年的办公楼——建设街122号,我没有回头。那栋灰色的偏凸式楼院,早已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我了解,它没有挽留我的能力,也没有挽留我的意图。因为,对这栋楼里的人,去与留,它已司空见惯,它始终默不作声。但我心里却希望它为我能走出这里而欣慰,因为,它该记得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故事。
楼院原本是沉默的,只因有了活生生的人出出进进,才使它有了生机。20年前的这个楼院,是本市比较有特色的建筑之一,整栋楼虽只有四层,每层也只有十多间办公室,但它的后院耸着一座60多米高的发射塔,那可是当年全县唯一的新闻机构——电台标志。办公楼坐西朝东,面临建设大街。一群广播人出入这个楼院,满楼满院生机勃勃。能在这里工作,着实令许多人羡慕。
局、台的木制牌子白底黑字,总是眉目分明,木制的窗门油得光滑滑的、匀匀的,犹如美丽女人脸上涂的美容霜。院内有两个双菱形花坛,分别守在铁大门的两侧,总是不失时机地开满鲜花;一道矮墙爬满青藤,墙根长着一排枝繁叶茂的垂柳;院内总有大小车辆停留,车棚里总有一排自行车膀挨膀地站在那。
20年的变迁,楼院迎来送往。送走了一任又一任领导、一批又一批离退职工、一拨又一拨调动升迁的能人;迎来了一茬又一茬的新人、一个又一个借驻的单位。进出这座楼的人:上进的、混事的、谋事的、谋人的、霸道的、受气的。整个楼院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可它就是沉默不语,始终扳着一张灰色的脸,不支持谁、不责怪谁,也不庇护谁。它不像办公室里的桌椅板凳,承受超重负荷时,还能发出吱嘎的响声。
我曾经为它那种不愠不火的冷漠态度而恼火。我觉得人不可以像它那样,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然而,再好的楼院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褪色。旧窗子上涂上了新油漆,并不能使糟烂的窗框坚硬起来,只有打掉旧的,换了新的,而这需要人来改造它。但新也好,旧也罢,楼房本身并不在意,你打扮它也好,摧残它也罢,它始终沉默不语。
当我走出122号几个月后,楼里所有人马也迁入新的广播电视大楼。每当我路过这个空荡荡的楼院,总是不由自主地多看几眼,有时竟驻足细细端详一番,体味人去楼空的凄凉景状。它满面灰尘,门窗都已破旧不堪,楼门、院门都被大铁链链着,加坠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院里的杂物被风卷来卷去,墙脚聚集着一堆堆垃圾,与门外繁华干净的建设大街格格不入,整条街唯有它——122号,这么破败。它那昔日的辉煌也随着广电人在新的广电基地上重新熠熠生辉。残余的它,只能落寞地等待着前来梳洗它的人。或许等到的不是改头换面,而是毁灭。只有那时,它才能发出最后的,也是有生以来的吼叫,或者说是哀鸣,伴着现代化拆迁机械的轰鸣声,与世诀别。
忽然间,我觉得这楼院沉默的性格像一位厚道的人一样,很有胸襟,它能包容一切。只是拆了它,是功是过,只能让历史作证,后人评说。
楼院始终是楼院,它的沉默告诉我:它可以无动于衷地承受一切,任人主宰,而人不能这样。人虽是万物之精灵,有时可以忍耐,但不能一忍再忍;人是可以抵抗外力侵入的,人可以为了维护尊严不沉默;人可以主宰一方,却不能主宰一切,哪怕是对一座沉默的楼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