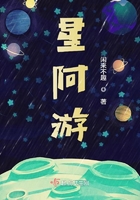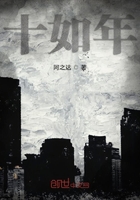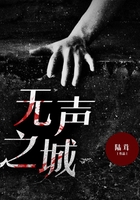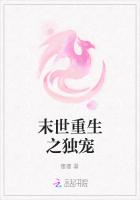1951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修改了1950年的决定,改为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和分级管理的制度。在收入方面,划分为中央预算收入、地方预算收入以及中央与地方比例分成收入。分成比例一年一定。在支出方面则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支出范围。
1953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为了适应这个时期经济建设的需要,不仅行政区划上做了调整,而且在财政上坚持了1951年颁布的划分收支的办法,实行了中央、省和县三级财政体制,并且还决定把地方“超收节支”的部分全部归地方所有。
由于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演说强调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重要性,中央决定大面积下放企业的计划管理权给地方政府。国务院在1957年11月颁布了《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决定从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体制。但是,由于“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经济混乱,这个体制实际上只执行了一年不到的时间。1958年9月,国务院决定用“总额分成、一年一定”取代原来的“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规定。
从1959年到1971年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修改的。其间,因为大饥荒的发生,1961年起中央又实行了集中管理的体制来恢复和调整经济,但后来很快又转向扩大地方财权的体制。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出现经济混乱的局面,1968年中央曾决定实行早期的收支两条线的做法,但最终也没有执行。
1970年前后,中央决定把大多数企业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为此,从1971年,也就是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央决定实行地方财政收支的“大包干”制度。具体做法是“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节余留用,一年一定”。“大包干”制度扩大了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的范围,在理论上自然可以增加地方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地方政府的激励。
但是,中央在执行中马上就发现,地方超收的大小“苦乐不均”,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和经济上的混乱使大多数地方的预算收支难以平衡,超收成为空话。因此,在1974~1975年间,中央对“大包干”体制进行了修正,调整为“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这个规则显然把地方的收与支之间的关系切断了,当然难以给地方以激励。
因此,在1976年之后,中央再进行调整,回到之前的规则,即改为“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同时于1977年设立江苏省为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试行“固定比例包干”的体制。按照这个试点体制,江苏省可以根据最近几年的预算支出占预算收入的比例来确定上缴中央和留用的比例,一定四年不变。比例确定之后,地方的预算支出从留给地方的收入中解决,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1978年,中央选择10个省市为“收支挂钩,增收分成”的试点,给予地方政府增加预算收入的激励。
所有这些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把过去的“条块结合,以条条为主”的财政体制改变成了“条块结合,以块块为主”的财政体制。可以这么说,在1957~1978年的这二十多年间,中国所执行的中央计划和集权财政体制不断被修改和瓦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事件对中国的经济体制造成的破坏更像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因为它破坏了前苏联式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步演变成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而这就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
记忆中,我在1990年前后对前苏联型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演进路径产生过浓厚的兴趣。1992年,我在上海的一个经济学杂志《经济发展研究》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信息费用、有限理性与计划约简:关于中国传统计划结构的一个理论解说》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我从计划当局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这个假设(这个假设当然是很现实的)出发,讨论了计划管理的体制会朝什么方向变化的问题。事实上,说计划当局处理不了那么多的微观信息一点都不夸张。前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发现,要做到有效的计划,一家企业包含的数据就高达4万个,一年需要至少完成600万次运算。前苏联当时有17万家企业、60万家零售店。可想而知,计划当局怎么能够有效地进行计划管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将近10万家国有企业、700万家集体企业,要实行集权计划管理,在信息上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央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计划当局一定会作出理性的反应,对计划的范围和计划任务进行大幅度的压缩与约简。如果我们把计划任务想象成投入—产出的矩阵,那么,约简计划任务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让矩阵中出现更多的“零向量”,这意味着计划单位之间没有关联,从而能减轻中央计划的协调和综合平衡的工作量。遵循这样的思路,如果计划的再约简能够按照地理区域或者特定的产业部门来规划,上述条件就可以基本满足。这是因为地理区域相对来说在其内部容易产生合作,减少对外部的依赖程度。特别是当这个区域在经济上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的时候更是如此。而按照特定的工业部门来约简中央计划,条件相对来说要更严格一些。只有那些在生产中对外联系不多,而较多依赖本行业内部提供投入品的产业才最适合。不用说,重工业比其他类型的产业更适合。
中国对计划的约简与前苏联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的工业部历来不够发达,地方政府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以及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资源大都控制在地方政府的手里而不是工业部的手里,这与前苏联有着根本的区别。所以,中国的计划约简基本上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中央把计划的权力更多地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尽管也存在着工业部的计划范围,但整体而言,中国的地方政府担当了更多计划者的角色。而在前苏联,工业部是计划??主要制定者和管理者。
辛向阳,《百年博弈: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100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张明庚和张明聚,《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公元前221年-公元1991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
关于这两篇经典文献的全文,可分别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62~771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56~1060页。
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孙冶方在1956年发表的文章是《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及《从“总产值”谈起》,均见《孙冶方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顾准于1956年写成的论文是《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见《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当然后来两人在60年代都受到审查和批判,并分别成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清洗运动的受害者。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吴敬琏在《共和国经济50年》一文中提到:在这一轮改革中,农村发生了与国营工商业体制相反方向的运动:后者的变革方向是放权让利,前者却是将原来只有15~20户规模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归并为“大社”,并于1958年夏秋之交建立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保持命令经济行政协调的总框架不变的条件下,层层分权的行政社会主义体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一起,形成了“大跃进”的组织基础。这是1958年中国经济生活陷于混乱的重要成因。
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并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数字,学者的研究和估计也各有差异。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数据。学者们的推测和估计大都是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其他各种数据进行的。例如,1984年,安斯利·科尔(Ansley J.Coale)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1963年间的线性死亡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1986年和1987年,蒋正华和李南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年、1964年、1982年人口普查中的全国年龄、性别报告数据,并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编制1981年人口生命表,再建立动态参数估计模型,求解后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是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1993年,金辉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年和1957年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根据这个数字可以推论出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果加上1959年的数字,三年间中国内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详见http://www.*****.com/?20051223/n241097986_5.shtml。
参见王绍光,《分权的底限》第4章,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
王绍光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分权以及经济的混乱作过政治的分析。参见王绍光,《分权的底限》第4章,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吴敬琏从经济学的视角对这段时期的行政分权过程也进行了分析。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45~54页。
黄肖广,《财政资金的地区分配格局及效应》,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参见政治学家Susan Shirk的研究。Susan Shirk,1993,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该文发表于《经济发展研究》1992年第3期。这本杂志是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创办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停刊了。这篇文章也收录于作者的《制度、组织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书中,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参见张军著,《制度、组织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6页。
参见张军著,《制度、组织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1~12页。
1978年以后的财政分权
1980年以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进入一个以“包干”为特征的体制。“包干”或者“承包”是我国民间对一种简单的合约形式的俗称。有意思的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在微观上基本就是依靠“包干”或“承包”这种方式推进的。私人产权的所有制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意识形态“禁区”,但在实际操作中“包干”却很容易被改革者接受,因为在“包干”或“承包”中政府依然拥有所有权。在经济学上,“包干”大概就是一种“固定租约”。
就这样,中国进入经济改革时期之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也开始以地方与中央签订财政上的“承包”为主,形成了以划分收支为基础的分级包干和自求平衡的协议关系。这种体制也时常被称为“分灶吃饭”。但其间因为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推行,也使得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相应地作出了一些调整。
1980年2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决定除了三个直辖市之外,其余地方均实行形式各异的财政包干体制,实行所谓的“分灶吃饭”。这个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对财政收入进行分类,划分为固定收入、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三类。而财政支出按照企事业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进行划分,地方财政在划分的收支范围内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
但是,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初始的财政条件不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地区的包干方案是有所不同的。根据钟晓敏教授的总结与分析,1980~1985年,大概有四类方案在不同的地区得到了执行。
第一类是执行标准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执行这一体制的是四川等15个省。这15个省根据1979年的收支预计数作为基数,收大于支的,按比例上缴中央;收少于支的,不足部分由中央从工商税中根据某一比例进行调节。中央承诺这个方案一定五年不变,地方自求财政平衡。
第二类执行的是特殊的地方预算财政体制。这类体制主要是在新疆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几个视同民族自治区待遇的省内实行。根据这个方案,这些地区除了继续享受原来的特殊待遇之外,也参照第一类方案划分收支范围,确定中央的补助金额,并保证每年增加5%,五年不变。地方的收入增长全部留归地方。
第三类方案的设计针对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在这两个省实行的是“划分收支、定额上缴或定额补助”。这个特殊的政策是为了配合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设。
第四类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江苏省的试点方案。在1980年后,江苏省继续按照试点办法执行,即实行“固定比例包干”的体制。但是实际上在1981年后江苏省也实行了上面第一类方案的包干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