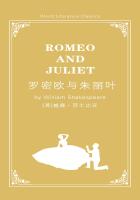——题记
人们
老远老远
一眼就望见了我
满树的枣子
一色青青
只有我一颗通红
红得刺眼
红得伤心
一条小虫
钻进我的胸腔
一口一口
噬咬着我的心灵
我极快就要死去
在枯凋之前
一夜之间由青变红
仓促地完成了我的一生
不要赞美我……
我憎恨这悲哀的早熟
我是大树母亲绿色的脚前
凝结的一滴
受伤的血
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
很红很红
但我多么羡慕绿色的青春
1982年秋
北京的城砖
北京高高的城墙
好多年以前已经拆除
但如今在小胡同里
还能到处看见那些
面熟的铁青色的城砖
拆下来的城砖太多太多
足足可以堆成一座山
如果当作垃圾清除
真还找不到那么一个大坑去埋葬
(想想看,要埋掉一圈四五十里长的城墙)
于是勤俭的北京人
用残破不全的城砖
在胡同里垒了墙角花坛
修补大门口的台阶
街道工厂砌成坚实的围墙
下雨时还把它们当作“垫脚石”
但是,古老的城砖上面
死死地粘着许多刮不尽的东西
黑的苔藓和白的灰浆
深深浅浅的刀啊箭啊的创伤
(听说有的城砖里还嵌着生锈的枪弹)
以及早已变黑的血迹……
又大又厚又重的城砖
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
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炮火的轰击
有的居然还完整无损,有棱有角
仿佛新出窑的一般
人们珍惜这些完好的城砖
用它们修成结结实实的山墙
还竖起来拼成马路的牙齿
还铺成了一条条齐整的人行道
每当行人踩在城砖上
踩在那些刮不尽的
历史的创伤和痕迹上
脚下总感觉到
有一点坎坷
有一点艰涩
心灵深处还会微微地震颤一下
眼前恍惚又壁立着高高的城墙
祖母推着小儿车
在城砖铺的人行道上
慢悠悠地走
车把上挂着菜篮
车厢里睡着胖乎乎的婴儿
车篷摇摇晃晃
车轮咯登咯登地响
哦,新铺的城砖路
一时难以磨平啊
城砖
那种又大又厚又重的铁青色的砖
中国不会再烧制了
中国永远不会再出现新的城墙
黄河与鲤鱼
黄河
你多么高傲啊
弃绝水草和浮萍的爱抚
弃绝太阳和云朵亲昵的投影
你甚至憎恶地不断地冲毁着
与你相依为命的河岸
黄河
高傲的黄河
你永远不能
从你似乎可以吞没一切的激流里
赶走一条鲤鱼
倔强的鲤鱼
经过千千万万代的死死生生
学会了在你泥浆似的激流里
睁着圆圆的眼睛,一眨不眨
学会了在你的恶浪与恶浪的隙缝中从容地呼吸
学会了迎着你的逆流冲刺
还学会了用剑一般的鳍
和闪着血光的锋利的鳞片
划开你的胸膛
向太阳飞跃
飞跃得比你的浪头还要高
1983年夏
岸边的草芽
这一带黄河岸
看不见一棵树
树在远近的花岗岩堤头
树在更远更高的北邙山上
高高的堤
和宽阔的河之间
是不断倾斜倒坍的岸
是灰茫茫的河滩
是呼啸旋转的大风
草芽,一棵棵草芽
碧绿的鹅黄的草芽
顶着明亮的露水
在黄河岸边挺直地站立着
它们离奔腾的大浪
不到一步远
不到一尺远
不到一寸远
不到黄河岸边的人
永远看不见这一棵棵细小的草芽
他们只能在远远的堤头或北邙山上
朦胧地望见
浑浊的流水
苍凉的沙滩
也许在今天起风的黄昏
也许在明天的黎明
这岸边的草芽
滚滚的波浪就把它们淹没
被冲得无影无踪
然而,岸边的草芽
在翻腾不怠的大浪面前
默默地穿破寂寞单调的河岸
擎起了旗帜般的草叶
告诉世界
黄河岸边
也有星星点点的绿色
毒日之下
焦渴的纤夫们
常常弯下腰身
拔起几棵带露的草芽
每棵草芽都有雪白的长长的根
纤夫们把它们含在嘴里咀嚼,咀嚼
苦腥之中有一点提神的辣味
哦,草芽,岸边的草芽
你是一首诗
你是一曲歌
人们不止一次地吟咏你
人们也不止一次地高唱你
1983年夏
阳 光 恋——一个真实的故事
雨后黄昏
你和我
坐在黄浦江陡立的岸上
浑浊的江面
闪烁着一道
血红的路
通向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记忆里都有
这样一道斜斜的阳光
你声音干哑
平静地向我叙述
自己过去的故事
眼角的皱纹不住地抽搐
夕阳浸红了你的苍发
你说那些年
你盼望的季节
不是明媚的春天
而是一年之中
白昼最短促的那一个月
那一个月
在严寒的冬天
只有那一个月
太阳奇迹一样
擦着你的囚室而过
从一个两尺见方的天窗
每年每年
你幸运地看见
二十几次
日出日落
有一年
你一次也没有见到和触到阳光
你病了很久
几个月工夫
生命象发了霉
面颊上手臂上长出一块块灰斑
你平静地说
眼光烁烁嘴角微亮
那一个月
中午
不比中午早一刻
你仰望天窗
看着日出
象童年时望着
九龙江岸的山峰
太阳天天从那儿上升
你象一个天文学家
在水泥墙上
用指甲
划了一道道
阳光走动的轨迹
计算得十分准确
阳光在哪儿落脚
又从哪条线上
依依地离开
日出的时刻
你仰起面孔
颤颤地举起手臂
仿佛期待久别的亲人
(你哪里晓得
你的妻子
早已投进这浑浊的黄浦江
瘦弱的儿子一个人
去了遥远的北大荒)
太阳圆圆的
睁着充血的眼睛
望见了你
矗立的身影
哦太阳初升
(窗外的世界已是中午)
桔红银白?鲜艳夺目
是儿子的面颊妻子的心
是一朵香喷喷的玫瑰
是一口嗡嗡响的血钟
是苦难祖国的
挂笑的面容
太阳太阳啊
在天南地北
找了亿万个窗口
才找到了你
坚贞的赤子
你站起身来
双手比划着
太阳真大真红?真亮
有一刻时间
正镶在你的天窗
你和太阳
面对面凝视着
热切地笑谈
那一刻
霉湿而斑剥的泥墙
冷凝的空气
梦幻般变了颜色
仿佛注进温暖的鲜血
阳光
亮在墙上
横在头顶
阳光
向你伸出火热的臂膀
你脱掉棉农
拼出全部生命力
(肌肉血液骨髓?神经?心灵……)
向上向上
纵身一跳再跳……
双臂象翅膀伸开
(你从春天纵跳到夏天
又从夏天纵跳到秋天)
生命
触到了阳光
触到了更多的阳光
第一年
只有手指手掌触到阳光
第二年
前额触到阳光
三年以后
胸腔也能触到阳光
你说
地球有引力
太阳对你更有引力
你说
触到的
不是光
是热血
是宣誓时摸过的红旗
你平静地说
那一个月
中午过一会
你目不转睛地看着太阳
离开天窗离开矗立不动的你
这奇迹
只存在二十几分钟
你也许是世界上
看日出最晚的一个人
你也许是世界上
看日落最早的一个人
但你看到的
是世界上最神奇而美丽的
日出和日落
每年
在最短促的一个月
在最严寒的一个月
你象活在春天
你哼唱几十支过去的歌
你背诵几十首青春的诗
有几年
医生诊断说
你的精神已经分裂
你望着他大笑
你对医生讲
太阳不但没有烧断你的神经
太阳还焊接好了你的
出现了裂纹的神经和脑壳
(你的头在紧闭的门上撞过许多次)
回到家里
已有五六年
你仍然天天纵跳
把双手高高举起
拼着全生奇
纵跳再纵跳
不是为了
触到阳光
阳光遍地皆是
你可以浴着阳光
在大街上走得浑身汗涔涔
你可以去海边河滩上
把浑身上下
晒得紫红紫红
连脸上的灰斑
都发出红光
不是为了
了望自己消失在天边的
青春的背影
家庭的幸福幻景
而是为了看见
更广阔的世界
更广阔的人生
纵跳吧
向上纵跳吧
生命
浴着阳光的生命
1980年秋——1982年冬
虎啸的回声
虎啸的回声
广东省一个自然保护区的护林老人难过地说:“由于溢伐森林,这一带的华南虎都远走他山。”
——杂记
一
这座有名的大山
尽管莽莽苍苍
有方圆几十里的原始森林
生息过千万年的华南虎
却已经绝迹
二十多年来
每当春情发动的三月天
幽静的月夜或清香的早晨
这里再也听不到虎啸
那一声声,一声声
与春雷在天地间共鸣的
强健无比的声音
春天的虎啸
是使四山震颤回响不己的山韵
是企求爱情的
最壮阔最有诱惑力的呼唤
是把全身的血脉酿成春潮的
一声声诚挚的心声
人们说
华南虎啸吼时
浑身的斑纹像火焰似地沸腾
每一根彩色的毛发
竖立起来
成为发声的金属的音叉
二
二十年前
这座大山上
还有最后一只虎
不愿离开家乡
每天在森林里孤独地游荡
三月天,从黄昏到清晨
这只华南虎悲凄地固执地呼唤
遥远的爱情
一会儿一阵风地窜到山巅
一会儿岩石般地立在一个小湖边
但三十里之内
没有另一只虎
虎啸
只使林中栖息的鸟乱飞
只使岩壁上洞穴里的蛇发抖
虎啸
终于成为绝望的呻吟
最后一只虎
流浪到远方
这之后
这里再没有见到一只虎
再也听不到虎啸
三
但虎啸没有绝响
远方,很远很远的大山
仍有华南虎
春雨蒙蒙的黎明
有时能隐隐地听到虎啸
像春雷的久久不息的尾音
如今当春雷滚动的时候
只有在陡峭的岩壁
只有在深山老林的树洞
只有在草丛中过去的虎穴
才能听见一点虎啸的回声
远方传来的虎啸
在这里久久地留恋
仿佛虎啸
能寻觅到虎的故乡
寻觅到它诞生的地方
有一个美丽的童话说
从此这一带山林里
长出了一丛丛虎耳草
日日夜夜
等侯着谛听着远方的虎啸
四
这里的华南虎
虽然已经绝迹
但留下许多淹没不了的虎穴
虎穴隐伏在哪里
没有护林老人的指点
谁也无法在千山万壑
在云雾缭绕的丛林中发现它们
据说只有天空盘旋的鹰
能认出过去的虎穴
它们的锐眼
望见黑魑魑的虎穴里
飘忽着经久不灭的火焰般的血气
虎穴
在绝壁
如今洞口长满了茅草和灌木
红的白的野花
在微风中摇曳
通往虎穴
没有路
没有可以攀援的藤蔓
虎穴前面
常常有一个峡谷
但猎人们喜欢找寻过去的虎穴
喜欢在虎穴附近露宿
那里不会出现毒蛇和蛤蚧
虎穴和虎常走的地方
长久地凝聚着老虎的气息
五
虎啸发自
最险峻最美丽的山上
距离虎穴不远的地方
多半有潺潺的溪涧
有飘洒的瀑布
有宁静的小湖
有浓密的山林
在这些地方
华南虎曾经一代一代
饮水,嬉戏,捕猎
昂首啸叫
繁衍健壮而威武的后代
是不是
最险峻最美丽的山
才能引发出一声声虎啸
才能召唤来远方的青春勃勃的回响
哦,这只有
远方的华南虎能够回答
六
山林的虎
不是村边的牛羊
不是池塘里沉默的鱼
它从没听到过呵斥
从没有看见过鞭影和捕网
一生只听到过见到过几回
猎人闪电似的枪火
像勾魂的血线紧紧地跟踪过它们
广阔而寂静的山脉思念远方的华南虎
林中的树脂、蘑菇、野花、草叶的芬芳
在呼唤
海潮般的虫鸣,鸟歌在呼唤
童年的洞穴,青春的梦在呼唤,呼唤……
护林老人说
华南虎会回到这座大山
这几年春天
远方的虎啸
已经越来越近
越来越响
有一天,这远方的回声
会变成五里之内的虎啸
1983年11月
夔门之谜
进入夔门
我才感到
滔滔的长江
闯过了
岂止一个夔门
而是几十个
它们一样的狭窄
一样的凶险
迎着船头
不远的前面
总壁立着一座山
冷冷地严严实实地挡着江流的去路
好象关死了的墓门
山壁上
悬着数不清的棺木
准备收硷长江的粉碎的灵魂
哦,长江
它浑身鼓荡着怒涛
被逼在峨岩之间
哪里还有第二条路可寻
只见它直撞那一个个拦路的峨岩
直撞那一个个关死的山门
狰狞的峨岩
在一瞬之间
怎么悄悄地避开了江流
关死的山门
在一瞬之间
怎么被江流猛地撞开
我始终没有看得清楚
更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
回头去看
那壁立的山
仍冷冷地严严实实地堵在那里
象一个关死的门
1983年冬
神 女 峰——记一个同船青年的谈话
我要独自登上那个苍苍莽莽的山顶
去膜拜敬仰已久的神女峰
从清晨直到黄昏
爬山越岭整整攀登了一天
人们说日出日落的时刻
神女峰的姿态最为魅人
神女峰那里
没有庙
没有碑
也没有一条通向她的小径
一路走一路找寻
云雾中有一座山峰兀立
多么象神女峰
日落前我赶到了那里
看到的却是个峻拔雄伟的大山
与神女峰毫不相象
于是我寻找孤单细瘦的山峰
孤单细瘦的山峰中
想必有神女峰
可是这样的山峰很多很多
也没有一个相象
我想应当寻找
向远方凝望的山峰
但看到的每个山峰
没有一个不向远方凝望
我寻找有泪痕的山峰
真让人吃惊
每个山峰
几乎都有斑斑的泪痕
我终于没有找到神女峰
也许见到了认不出来
但是我并不懊悔
我看到了那么多,那么多
峻峭美丽的大山
1983年冬
山 与 人
远远地望见了
一个陡峭的山峰
孤零零地矗立在云雾中。
我对同行的诗人说:
“瞧,那山峰
真可以雕成一个
顶天立地的人。”
诗人摇摇苍白的头
望望那山峰,又望望我:
“不要以为把山雕成了人形
山才能变得不朽,变得神圣
山本来是不朽的,
人只能虔诚地去攀登。”
关于大山和小草
不止一个诗人说过
小草恋山
野花总依恋在
高高的悬崖上
有谁想到过
有谁能说得清楚
那沉默的大山
那沉默的悬崖
它们想些什么
假若一座秃秃的荒山
只有暴风雨冲刷的沟壑
只有焦渴如焚的岩石
那高高的大山
横亘几百里的大山
该有多么地寂寞和凄凉
大山的
干裂的唇舌
弓起的背脊
粗砺的肌肤
多么企望
呼吸到一滴湿润的水气
咀嚼到一点儿青草的液汁
细长柔韧的小草的根须
扎进了山岩的裂缝
大山的神经再迟钝
也能感触到
有小小的生命,芳香的生命
向它贴近,向它亲吻
默默地抚慰它那焦渴的心灵
草叶草茎和草花
被峡谷的劲风
吹得摇摇晃晃
折弯了腰身
匍匐在峰岩上
于是大山才有了快乐
大山的心灵也觉得摇摇晃晃
当狂风暴雨袭来
霹雳鞭笞着大山的背脊
那浓密的草丛
那长长的藤蔓
那看不见的根须
还有那厚厚的落叶
都紧紧拥抱着大山
大山呵涌出了热泪
从山岩的缝隙
泻下了瀑布
流下了溪水
读梵·高画四题
《石凳与常春藤》
梵·高饥饿
梵·高困倦
梵·高孤单
梵·高草草地画了一个
甜蜜的梦境
为他自己,为贫穷的人
多么荫凉而魅人的角落
它平凡,自然,安静
常春藤下只有一个沁凉的石凳
常春藤挂满紫色的花
阳光为草地和石凳
印上闪动的斑纹
一个人加一个朋友
默默地坐在石凳上
小风吹拂着渴望生活的心灵
《一钵土豆》
土豆,泥土的结晶
不是一幅静物画
它是梵·高以深深的感激
画出了给他活命的粮食
土豆,浑圆硕大
有乌黑的瘢疤
有更多更多的
孕育生机的芽眼儿
梵·高的画就象土豆
也是泥土的结晶
它的乌黑的瘢疤比土豆还多
它的孕育生机的芽眼儿比瘢疤还多
《奥弗的教堂》
奥弗教堂修盖在高坡上
让人们仰望它
让钟声飘荡到远方
里里外外装饰得象梦境
窗玻璃涂遍了彩丽的颜色
凡是走进去的人
苍白的面孔
会突然镀一层光亮
但天空阴沉沉
乌云翻滚
通向奥弗教堂的道路弯曲而泥泞
人们只能仰望它
不停地跋涉
不停地喘息和祈祷
《麦田上的鸦群》
——梵·高最后的画
金黄的麦田
呼唤着收获
乌云般的鸦群
揽暗了天空
象一群魔鬼扑搧着翅膀
飞进了梵·高的灵魂
梵·高仰起面孔
伫立在画的当中
向太阳,向世界
有声有色地告别
一粒大阳的种籽
沉甸甸地落进大地
最后的画
是他的墓地
从翻耕过的麦田里
将会长出一棵不朽的向日葵
二分硬币
河北省蠡县辛兴大队,一九七七年还穷得叮当响。近五六年来,由于全面经营和发展工
农商业,勤劳致富,大大地改变了多年来的穷困面貌。一九八三年,大队拥有的固定费金已
达五百多万元,成为冀中太平原上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农村。
——题记
但是
不能忘记
永远不能忘记
1977年3月
(谁能忘记这个春天)
华北太平原刚刚解冻
老支书阎建章重新上台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
走进久违的大队部
翻开破破烂烂的账本
唉,一个几千人的生产大队
只剩下
二分钱的现金
二分钱
二分钱
千真万确只有这二分钱
阎建章
把这枚二分硬币
放在满是硬茧的手掌心
紧蹙着眉头
久久地沉思……
小小的硬币
在春天的阳光下
显得异常地苍白
是饥饿的面孔
是瞪得圆圆的眼睛
阎建章伤心地望着
这枚沾满了泥巴和泪渍的
疤痕般的二分硬币
他仿佛第一次发现
圆圆的硬币上面
有一个圆圆的国徽
他凝望着国徽
抚摩着国徽
阎建章啊阎建章
共产党员
大地之子
俯下沉重的头颅
(这些年
两鬓添了多少白发)
闻了闻硬币和国徽
硬币和国徽是酸的
硬币和国徽
跟他的生命一样
发着
汗的气味
血的气味
土的气味
二分硬币
一小撮盐的价值
一小撮泥土的重量
一下子变成了千斤重
从阎建章抖颤的手掌心
滑落到了地上
发出洪钟一般的声音
这声音
几十年来
他听过不知多少回
从老支书网着血丝的眼睛里
掉下一滴泪珠
泪珠滴在地上
也象一枚圆圆的二分硬币
哦,圆圆的泪水里,
浸着一个庄严的国徽
立在1977年春天的阳光下
老支书阎建章
在二分硬币前
在饥饿的面孔前
在瞪得圆圆的企待的眼睛前
把硬币从地上拾起来
(谁说“文革”没有“遗产”呀)
向生他养他的苦难的祖国
默默地起誓
他把这枚二分硬币
(如果能放大一千倍多好)
当作神圣的国徽
带着泥土和血汗气味
悬在大队部的门楣上
一直到永远
永远
1984年6月
长跑
年轻时,我练过长跑。这几年,我作为一个观众,几次立在长跑竞赛的终点,望着向我冲来的冠军。
——题记
长跑的人
在开始一段路上
用眼睛瞟着高高的蓝天
他看见风吹动自己的额发
看见路边丛立着的观众
看见自己弹动的手臂和闪光的膝头
他听见清脆的鼓掌声
听见前前后后向他逼近的脚步声
他微微地闻到了草叶的清香
和槐花甜甜的气味
他的面孔挂着微笑
渐渐地
渐渐地
再听不到什么杂音
再闻不到什么气味
天地问变得异常单纯
只充满了一个巨大节奏和音律
心脏轰轰地搏动
呼吸声仿佛扩大了几十倍
这单纯而雄浑的声音
生命的脉息
是自己的
是跑在前面的人的
是跟在后面的人的
现在
他只看见
面前长长的发光的路
(是谁在路面上镀了一层亮色?)
梦境一般向他扑来
路似乎直立了起来
用阔大的胸壁狠狠地阻挡着他
他的胸腔
他的腿脚
感触到了重重的冲压
他的每根骨骼向前弹射
他的每条肌腱向前冲刺
胸骨一张一收地在喘息
哦,生命最顽强的喘息
他的手
向前刨,向前抓,向前砍杀
他的每一个血球
向前滚滚地飞驰,冒着火焰
他第一次觉得空气是透明的实体
是千万层阿
是灼热的火墙
他,一步,一步
穿透了沉重的空气
路倒了直立的路
终点是一个巨大的磁石
长跑者的生命
是一粒铁
他的骨骼里有铁质
肺叶里有铁质
血脉里有铁质
脑汁里有铁质
他不回顾地
扑向终点
终点
不是艳丽的彩带
不是雪白的斑纹
终点是一个升起的地平线
终点
伸出了强健的手臂
长跑者也伸出了强健的手臂
他和终点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长跑的人
挣脱了终点的拥抱
向前冲出好远好远
把地平线
拋在身后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