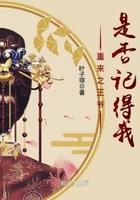潘·阿波廖克美好而又智慧的一生,如醇酒一般冲击着我的大脑。在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这座被匆匆忙忙粉碎的城市里,在一片杂乱无章的废墟上,命运把一卷堪称稀世之宝的福音书掷于我脚下。在圣洁光环的包围中的我,立刻庄严宣誓要以潘·阿波廖克为榜样。想象出的仇恨带来的快感,对猪狗一般的人类的痛苦的蔑视,沉默而又令人陶醉的复仇之火——全都被我当做祭品奉献给我的新誓言。
在诺沃格拉德那位业已逃亡了的天主教司铎家里,墙上高高供着一幅圣像画。圣像画上有一句铭文:“施洗者之死”。我一眼就认出这位施洗者约翰是一位我曾见过的人的形象。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早晨:在笔直而又明亮的两墙之间,笼罩着一片蛛网般的寂静。恰好有一缕阳光直射在画像台座上。光影中闪烁着无数的尘埃。忽然身形修长的约翰从蓝幽幽的壁龛深处,直冲冲地向我走来。冷酷无情、瘦得令人生厌的身躯上,庄严肃穆地披着一件黑斗篷。斗篷的圆形纽扣里,有一滴滴的血液在闪烁。施洗者约翰的头颅是被从剥了皮的脖子上斜砍下来的。头颅放在一只黏土烧制的盘子里,盘子被一位士兵粗大而又发黄的手指牢牢地握着。我觉得死者的面容煞像我的一位熟人。我立刻预感自己将要揭开一桩秘密。黏土盘子上,放着那颗死者的人头,是照着在逃司铎的助手罗姆阿里德先生的样子画的。在死者那张开的嘴里,垂着一条极其细小的蛇,蛇的鳞片在闪闪发光。小蛇那充满生机的浅玫瑰红色的小脑袋使得作为背景的深色斗篷愈发凸显出来。
这位圣像画家的技巧及其阴暗构思,令我惊奇。但更令我惊奇的是,第二天,我在老司铎的女管家艾丽扎太太的双人床上,发现居然挂着一幅脸色红润的圣母像。两幅圣像画显然出自同一人手笔。圣母那圆滚滚的脸庞,一看就是从艾丽扎太太的肖像摹写下来的。这下我距揭开诺沃格拉德圣像之谜,就又近了一步。这个谜引导我们走进艾丽扎太太的厨房。在那里,每逢芬芳馥郁的夜晚,以一位圣愚[2]画家为首,一群波兰老仆的幽灵,总是会在那儿聚会。然而,那个使郊区村镇住满了天使,让改信者瘸子雅涅克跻身于圣徒之列的潘·阿波廖克,果真是圣愚吗?
三十年前,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夏日里,他带着瞎子戈特弗里德来到这里。朋友俩——阿波廖克和戈特弗里德——来到距城边两里、位于罗夫诺公路上的什梅列尔大车店。阿波廖克右手拎一只颜料箱,左手挽着盲人手风琴手。他们那钉有铁掌的德国式鞋底,发出宁静而又充满希望的、悦耳的脚步声。阿波廖克细细的脖子上,有一条绣有浅黄色的围巾,而盲音乐家的蒂罗尔[3]帽子上,则插着三根巧克力色的羽毛。
一进店,两个来客便将颜料箱和手风琴搁在了窗台上。艺术家解开脖子上的围巾,不想那围巾居然像市场上耍把戏人手中的带子一样,怎么也不见头。随后他来到院子里,把自己脱了个精光,用寒冷的冰水,往自己那瘦骨嶙峋的身上浇。什梅列利的老婆给客人们上了葡萄干酿的伏特加和一钵米馅肉饼。吃饱喝足后,戈特弗里德抱起手风琴,放在他那瘦骨伶仃的双腿上。他叹了口气,仰着脑袋,细溜溜的手指开始在键盘上飞动。海德堡浪漫派乐曲美妙乐音,开始在这座欧式小酒馆内回荡。阿波廖克也用颤抖的声音,附和着这位盲乐师。这情形就好像人们把管风琴从圣英捷吉尔达天主教堂,搬进什梅列利小酒馆里似的。两位身披花花绿绿围巾的、德式皮鞋钉有铁掌的缪斯,并肩坐在管风琴上演出似的。
客人们一直唱到日落时分才收摊,他们把颜料箱和手风琴装进麻布袋里。阿波廖克向勃莱娜——小酒馆老板娘——深施一礼,递给她一张纸。
“仁慈的勃莱娜太太,”他说,“请笑纳一位流浪艺人、教名阿波利纳利的基督徒,为您所画的肖像,以此表示对您的奴仆般的感激,也是对您乐善好施、殷勤待客的一个证明。假使上帝耶稣延长我的寿数,让我的技艺臻于完善,我一定会重返此处,为这幅肖像上色的。我还要让您头上戴珠宝首饰,让您胸口戴上宝石项链……”
在一张很小的纸片上,有用红铅笔而且是那种像黏土一样绵软的红铅笔,画的勃莱娜太太,她金黄色的头发盘在脑后,一脸笑容。
“花的可是我的钱啊!”什梅列尔一看见妻子的画像,就心痛地嚷了起来。他操起一根木棍就追赶起这两个客人来。可追着追着,他油然想起阿波廖克那被冷水浇得红扑扑的身体,小店院里和煦的阳光以及和谐美妙的手风琴声。这个旅店老板一下子分了神,丢掉木棍,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阿波廖克向诺沃格拉德的司铎出示了慕尼黑美术学院毕业证书,并向他展示了十二幅以《圣经》为题的绘画作品。这些画都是油画,画在一张张薄薄的柏木板上。这位神父看见摆在自己的写字台上的画中,有一套鲜红欲燃的祭服,有闪耀着绿宝石光芒的田野,还有被盛开的鲜花铺满的巴勒斯坦平原。
潘·阿波廖克笔下的这组圣徒,全都是兴高采烈、憨态可掬、胡子花白、面色红润的老者,他们全都身披绫罗绸缎置身于盛大的宴会中。
就在那天,潘·阿波廖克奉命为一座新开张的教堂画装饰壁画。神父在饮完本尼狄克丁酒[4]后,对这位艺术家说。
“圣母马利亚,”他说,“亲爱的阿波利纳利阁下,您如此令人愉悦的天赋才禀是从怎样奇妙的天国,降临到您身上的呢?……”
阿波廖克工作干得很起劲很卖力,刚过了一个月,新教堂的内壁,就画满了咩咩叫的羊群,尘土飞扬、晚霞满天的日落景象和淡黄色的母牛乳房。皮毛被摩擦尽净的水牛们,争先恐后地往套子里钻,狗吐着猩红的舌头,一只只跑到羊群前面,绑在笔直的棕榈树干之间的摇篮里,摇着胖乎乎的婴儿们。破衣烂衫的方济各会修士们,围护着一个摇篮。一群占星家都剃了锃亮的秃头,脸上布满了像伤口一样泛着血色的皱纹。在这群占星家中,还隐现着列夫十三世那带着狐狸般奸笑的老太婆一样的面孔。而诺沃格拉德天主教司铎本人,一只手捻弄着一串中国式雕花念珠,另一只空闲的手,则在为刚刚诞生的耶稣祝福。
整整五个月,阿波廖克被钉在木制高脚凳上一般,一直在大殿的内壁,拱顶和圣诗台上忙活。
“亲爱的潘·阿波廖克,您很喜欢画熟人的面孔。”有一天司铎在那群占星家里,发现了自己和被画作砍下的约翰的头颅的罗姆阿里德先生,于是便这样说道。老神父微微一笑,打发人敬了正在穹顶下干活儿的艺术家一杯白兰地。
此后,阿波廖克还画了《最后的晚餐》和《受石刑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于是,在一个礼拜天,他揭开蒙在壁画上的布幔。受司铎邀请前来参观的当地名人,认出使徒保罗的原型,原来是改信者瘸子雅涅克,而抹大拉的马利亚,其原型则是一个生父母不明的孤女、犹太女孩埃丽嘉——许多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孤儿们的母亲。地方名流下令遮盖这些亵渎神圣的壁画。司铎随即向这位渎神者发出严厉威胁,但阿波廖克却拒不遮盖其壁画。
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爆发了,一方是大权在握的天主教会,另一方是玩世不恭的圣像画匠。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十年之久。这一事件差点儿没把一个温顺平和、游手好闲的闲人逼得成为一个新邪教的创始人。在当时,他堪称动荡而又曲折的罗马教会史所曾有过的所有斗士里,最令人费解而又搞笑的,他怀揣两只小白鼠,兜里揣着一套最细的画笔,怡然自得,酒意微醺地走遍大地。
“15兹罗提一幅圣母像,25兹罗提一幅圣家族像,50兹罗提一幅最后的晚餐,里面的形象可以根据定制者的家属来绘制。可以把定制人的死对头,画成卖主求荣者犹大的形象,但需要另加10个兹罗提。”自从阿波廖克被从建造中的教堂里赶出来后,便如此这般对本区教民说。
找他定制的人络绎不绝。一年后,由于收到了诺沃格拉德司铎气急败坏的诉状,日托米尔[5]主教派了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委员会在几间破败潦倒、散发恶臭的破农舍里,找到了这些面目狰狞的圣家族成员的肖像画,这些画亵渎了神明、画风幼稚却活灵活现。所有约瑟[6]的脑袋上,头发都是中分式的,耶稣都涂了膏油,所有的马利亚都像生育过多的村妇,双腿叉开——此类圣像被悬挂在圣像角,周围放了一圈纸花环。
“他让你们活着时就成为圣徒!”杜本和新康斯坦丁教区的副主教,在回答那些拥护阿波廖克的人群时,这样嚷道,“他让你们周围摆满了无比崇高的圣物,可是你们算什么,你们是犯了不尊圣训之罪的下三流,是偷酿私酒的人、是毫无同情怜悯心的放高利贷者、造假秤砣的骗子、出卖自己女儿贞操的混蛋!”
“神父阁下,”这时,瘸腿的赃物倒卖贩子兼墓地看守人维托利德对副主教说,“谁能告诉这帮愚民,最仁慈的上帝先生认为什么是真理呢?能满足我们自豪感的潘·阿波廖克的圣像画,难道不是比您那些充斥诋毁中伤和傲慢的怒火的话,所包含的真理更多吗?”
人群的怒吼让副主教只能连忙撒腿逃跑。城近郊区人们的思想状况,对教会人士的生命构成了威胁。被请来代替阿波廖克的那位艺术家,犹犹豫豫地,不敢动手把埃丽嘉和瘸腿雅涅克抹掉。这些画儿直到今天,也能在诺沃格拉德天主教堂侧面的附属建筑物里找到:雅涅克即使徒保罗,是一个胆小怕事的跛子,留着一把梳得一绺一绺的大胡子,是一个被乡村抛弃的浪荡子;还有就是抹大拉的荡妇,病体支离,疯狂痴迷,以及她那舞蹈中的肢体和深陷的脸颊。
与司铎的斗争持续了三十年之久。随后,哥萨克起义把老修士,从其散发强烈气味的石穴[7]中驱赶了出来,而阿波廖克也就顺理成章地搬进艾丽扎太太的厨房定居——命运实在无常呀!于是也就有了我这么个一晃而过的闪客,每天晚上和他喝酒聊天。
聊天——聊什么?聊浪漫主义的小贵族时代,女教徒的宗教狂热,聊艺术家鲁克·德尔·拉比奥,聊来自伯利恒那位木匠的家庭。
“文书先生,我可有东西和你聊……”晚饭前,阿波廖克神秘地对我说道。
“好,”我说,“好吧,阿波廖克,我听着呢……”
可是,神情阴郁、表情刻板、骨骼粗大、两耳垂肩的教堂差役罗巴茨基先生,所坐的地方离我们实在是太近了。他在我们面前挂起了沉默和敌意的帘子。
“我有事儿对您说,”阿波廖克把我领到一边对我耳语道,“且说耶稣,马利亚之子,曾经娶德博拉——一个耶路撒冷非名门望族家的女儿……”
“喔,你这个银儿[8]!”罗巴茨基先生气得直嚷嚷,“你这个银儿,死了都没地儿埋……你就等着被银们打死吧……”
“晚饭后,”阿波廖克压低声音对我悄悄说道,“如果文书先生您方便,晚饭后……”
我没什么不方便的。被阿波廖克故事的开头点燃起了好奇心的我,在厨房里踟蹰徘徊,等待着宝贵时刻的来临。外面已经是黑洞洞的夜了。窗外那座生机勃勃的园子,黑森森的,也给冻僵了。月光下那条通往教堂的路,煞像一条银光闪烁的河流在流淌。大地以及灌木丛里如项链一般的果实,也都泛着幽暗的冷光。百合花的香味纯净、醇厚,像酒精一样。这阵新鲜的毒气咬住了炉子浓重、急促的呼吸,也驱散了充斥着整个厨房的松脂燃烧带来的闷热。
阿波廖克挽着粉红色的蝴蝶结,穿着被磨破了的粉红色的裤子,像一头善良的又文雅的动物,在自己的一方角落里爬来爬去。他的桌子涂满了胶水和颜料。这老头正用细碎而又频密的小动作,涂抹着什么,从角落里传来一阵轻微的、节奏分明的颤动声。老戈特弗里德用颤抖的手指,为其打着节拍。盲人一动不动地呆坐在泛黄的、油腻的灯光下。他歪着已经秃了顶的脑门,凝神倾听着自己那盲目这支永无休止的音乐,凝神倾听自己这位永远的朋友的絮絮叨叨。
“……神父们所说的,以及《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文书先生,全不是真的……文书先生如果愿意出50马克,我可以给您画一幅怡然自得的方济各像,背景是绿树环绕和湛蓝天空,您一看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了。这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圣徒方济各先生。如果文书先生在俄国有未婚妻……女性都喜欢怡然自得的方济各,尽管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先生……”
在这个散发着浓郁的云杉味儿的角落里,有关耶稣和德博拉婚姻的故事,就这样开了头。少女德博拉有过一个未婚夫,这是阿波廖克的说法。她的未婚夫是个倒卖象牙的以色列青年。可德博拉的新婚之夜,却是在误会和眼泪里度过的。当她看见正在走近婚床的未婚夫时,感到十分恐惧。一个饱嗝顶开了她的喉咙。她把婚宴上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德博拉本人,她的父亲、母亲以及她整个家族,全都蒙受了耻辱。新郎把她挖苦了一番,扬长而去。走时叫走了所有宾客。耶稣看到了这位既渴望丈夫又害怕丈夫的女人的痛苦,于是,他穿上新郎的新婚礼服,满怀怜悯地和躺在呕吐物里的德博拉进行了交合。完事后德博拉走到客人面前,为自己终于成为一个女人而骄傲而欢天喜地,笑语喧哗。而耶稣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他出了一身冷汗,哀伤的蜂刺蜇伤了他的心脏。谁都没察觉他是如何悄悄离开宴会厅,来到犹太王国以东的一个荒漠国度,约翰正在那儿等着他的到来。于是德博拉便生了第一胎……
“这孩子现在在哪儿?”我大声问道。
“他被那些神父隐藏起来了。”酒鬼阿波廖克将一根细长怕冷的手指,移到鼻翼一端,神情庄重地说道。
“画家先生,”突然,罗巴茨基从黑暗中冒了出来,扇动着两只灰绒绒的耳朵嚷道,“你胡说哈么呀?简直是胡说八道……”
“嗯,嗯,”阿波廖克搂着戈特弗里德蜷缩成一团,“嗯,嗯,先生们……”
他拖着盲友走向出口,可在门槛上,他放慢了脚步,用指头朝我示意。
“怡然自得的方济各,”他眨动着眼睛喃喃道,“袖筒里藏着小鸟儿,是鸽子还是金翅雀,文书先生喜欢什么就是什么……”
说完,他就和他永恒的朋友瞎子消失在黑夜里了。
“哎,真是福闹!”教堂杂役罗巴茨基恨恨地说道,“这种银儿不得好死……”
说完,罗巴茨基先生像懒猫似的,大张着嘴打了个哈欠。我告别了他,回到我那被抢劫一空的犹太人家里去过夜。
无家可归的月亮正徘徊在城市上空。我与月亮同行,无以兑现的理想和不成曲调的歌谣使我感到一丝暖意。
注释
[1]原文为Пан,是革命前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区对地主、贵族、封建领主的尊称。此处由于特指译为“潘”,其余处根据情况译为“老爷”、“先生”等。
[2]圣愚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有人物。他们通常是浑身污垢、半疯、半裸体的游民,脚上套上脚镣。他们有些人几乎不能言语,他们的声音却被解释成神谕。
[3]蒂罗尔州,位于奥地利南部。
[4]一种法国蜜酒,又称利口酒,主要用作餐后酒或调制鸡尾酒。
[5]乌克兰北部的一个州,其首府为日托米尔市。
[6]指耶稣的养父,下文中来自伯利恒那位木匠也是指耶稣之父圣约翰。
[7]应指教堂。
[8]罗巴茨基由于疯癫而口齿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