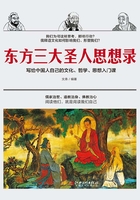邵汉明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开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便无从谈起。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文化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即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一、儒家文化研究历程的简要回顾
建国以后,儒家文化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值得回味的过程。
总的脉络是:50年代初期,人们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将其运用于儒学研究之中;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儒学研究出现简单化、教条化倾向;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儒学研究遭受厄运,儒学被歪曲为腐朽反动的意识形态;70年代后期至今,儒学研究重新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关此,赵吉惠先生的《建国以来儒学研究的艰难历程与最新进展》一文有较为具体详尽的论述,可资参考,我们不再作新的绍述和补充。我们要借此强调的一点是,建国50年来,儒学时而被批判,时而被宣扬,儒学研究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与现当代中国政治密切相关。儒学地位的变化、儒学角色的转换、儒学研究的进展,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化和发展。郑家栋先生揭示50年来儒学研究的特点说:“如果说50至70年代的儒学研究是服务于政治和隶属于意识形态的斗争,80年代的儒学研究是追随打破禁区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90年代儒学研究则显示出相对独立的学术与文化意义”。就总的趋向和特点而言,这一概括和揭示应是符合实际的。
这里,我们要着重就80年代以来的儒学或儒家文化研究作一较为全面的总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儒学研究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成立了众多的儒学研究机构,如国际儒学联合会,全国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山东大学周易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易学研究所等等;二是创办了一些专门的儒学研究刊物,最著名的如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主办的《孔子研究》、全国易学研究会和山东大学周易研究所主办的《周易研究》等等;三是召开了大量的国际国内儒学研讨会,如纪念孔子诞辰2535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1984年)、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89年)、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年)、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1987年、山东曲阜)、“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上海)、海峡两岸首次儒学学术讨论会(1991年、山东曲阜)、’94南京金秋儒学国际研讨会(1994年,南京)等等;四是出版、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儒学研究学术论著,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中,出版孔学、儒学研究方面的专著有近干种之多,若加上知识性、资料性方面的编著,数量更是惊人,而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其数量更是难以精确统计,恐怕要在万篇以上;五是社会各界人士给予儒学研究以普遍的关注和重视,一些国家领导人(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如江泽民、李瑞环、李光耀等等)纷纷出席一些大型的儒学研讨会,发表讲话,肯定孔学、儒学的历史地位及其现代价值;学术界、文化界(尤其是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领域)的众多前辈和后进更是频繁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孔学、儒学研究成果;甚至一些有远见的实业界人士也对儒学研究中的儒商问题、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如果说上述五个方面尚属儒学研究之繁荣的外在表现的话,那么儒学诸问题探讨的深度和广度的双向拓展、对待孔子儒学之态度的根本性改变似可视为儒学研究之繁荣的内在表现。就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而言,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孔子、儒学基本上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批孔批儒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人们的思维局限于单线的两极对立式的思维,即总是在唯物唯心、进步反动的对抗中打转。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人们放弃了非此即彼的单一的对立式的思维方式,彻底改变了对于孔子、儒学的态度,从而终止了孔子儒学遭批判的厄运。张岱年先生在《孔子大辞典·序言》中指出:“我们研究孔子,与过去的时代有所不同。在‘尊孔’的时代,‘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削弱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批孔’的时期,对于孔子谩骂攻击,表现了对于历史的无知,这样的时代也已过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如实地理解孔子,正确地评价孔子,也就是对孔子进行科学的研究,批判继承儒学的文化遗产。”“如实地理解孔子,正确地评价孔子”,“批判继承”,反映了人们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尽管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但毕竟人们有了这样的愿望和自觉,达成了理性的共识。这种态度、立场的转变乃是儒学研究从非正常状态进入正常状态的标志,乃是儒学研究出现繁荣局面的内在前提和基础。
就儒学诸问题探讨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亦是显而易见的。像先秦原始儒学的研究、宋明儒学(理学、心学)的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可以说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深度和水准的成果。当然,这里所谓“深度”也还是相对的,且基本上还停留在“史”的“述”的局面,停留在儒学本文的诠释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哲学创造”的层面,进入儒学改造或创造性转换的层面。在广度方面,近20年中,人们的探讨不仅涉猎古代儒学,也涉猎现代儒学;不仅涉猎儒家的专门人物和儒学史,也涉猎儒学的许多专门问题如中庸问题,儒学本体论问题,人生哲学问题等等;不仅对于许多老问题有新的认识,如孔子的再评价问题,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而且提出许多新问题并展开了初步的讨论,如儒商问题,儒教问题,儒学的大众化问题,郭店简与儒学的关系问题等等;不仅有历史的反思,如关于儒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也有现实的思考,如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问题。应该说,新视域的开辟与一些新方法的引入、新资料的发掘、视野的拓展是密切相关的。而这也正构成儒学研究所以出现繁荣局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儒家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极为丰富。人们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要将这方方面面的探讨情况作一全面系统的总结,实是不易,本书篇幅也不允许。这里,我们只能就儒家思想中几个最最重要问题的讨论作一钩玄撮要的总结,而舍弃一些次重要和大量微观层面问题的讨论情况。
(一)“中庸”研究
1.中庸观念的提出及其演变
有论者探讨了“中庸”观念的形成,指出“中庸”作为一个概念虽始见于《论语》,然“尚中”的观念却由来已久。早在甲骨、金文中已有“中”字,在《尚书》、《诗经》、《易经》中也多次出现“中德”、“中罚”、“中行”等观念。在《尚书》等典籍中亦有“庸”字。孔子在继承和发挥殷周时期“尚中”思想的基础上,首次将“中”和“庸”结合起来,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正式提出了“中庸”的概念。
有论者着重论述了“中庸”观念的演变及其哲理化的进程。指出孔子第一个将“中”“庸”并用作为“至德”的伦理范畴,这种“至德”首先体现为公允地坚守中正的原则,以无过无不及为特征。《中庸》则将“至德”提升到“天下之大本”和“天下之达道”的哲学高度,强调“固执”,要求自觉地保持与中道的一致,站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适中立场,即做到“时中”或“慎独”,以达到“尽合乎中”的理想状态。孟子的中庸观是以“权”、“义”为中心范畴建立起来的,强调既要坚持圣人之道——“义”,也要有“权”——灵活性与合理性。“权”即“义”之“宜”,“执中无权,独执一也”,“执中无权”与“执一”都不可取,惟“执中有权”,方能恰到好处地坚守圣人之道。荀子的中庸观以“礼义”为中心范畴,这一中庸观基于“性恶”,强调“分”、“别”,追求“兼”“一”。他主张“以分求一”、“从别到兼”,礼义统摄下的差异性的“各得其宜”,从而达到“才举不过”。
《易传》的中庸观是在《荀子》“各得其宜”的“和一”之道的基础上,通过贯穿于“穷变通久”的“位”、调和于分阴分阳的“中”,警惕于“否极泰来”的“时”完善而深化的。所谓“位”指卦爻位次,表示等级秩序,“位”规定了“穷变通久”的基调。所谓“变”即改变原状,回到正位上来。所谓“中”,一指构成一整体的个体各得其宜的状况,二指由个体所组成的和谐与均衡的整体。“中”是对“过”而言的一种以正道守其位的“宜”而“和”的境界。所谓“时”,一指“见几而作”,二指动静以时,三指兼顾利害,治不忘危。至此,先秦儒家中庸观,经过“至德”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提炼,中经“权”“义”的调节,由“分”“别”进入“一”“兼”后,终于“位”矣“定”矣,从而结束了其哲理化的历史进程。
2.中庸本义
有论者认为,中庸之“中”有二义,一日“内也”,即人之本性情感藏之于内心中,尚未显露,无偏无倚;二日“正也”,即无过不及,恰到好处。中庸之“庸”,也有二义,一日“用也”;二日“常也”。于是,中庸即是“用中”,中庸之道即是“用中”之常道。有论者指出,“庸”,还有“和”义,中庸也即“中和”。有论者认为,中庸、中和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包括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两层含义。还有论者指出,中庸的核心在一个“中”字,“中”有三义:一日中礼或中道,这是讲“中”的标准,道乃规定无过不及的尺度;二日时中,强调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随时变通以合于中;三日适中,强调不偏执,不走极端,这是中礼、中道在人的行为和人格风貌上的具体体现。又有论者认为,中庸包含尚中和尚和。尚中即推崇中正不偏,具体而言,一谓执两用中,二谓以礼制中,三谓因时而中。尚和即强调矛盾事物的统一、和谐,恰到好处。“和”一指和谐、调和,二指中和、恰到好处。
有的论者归纳儒家中庸观的特点为四项,一是反对过与不及,二是反对“攻乎异端”,三是主张权变与“时中”,四是要求“中”与“和”的和谐统一。
3.仁、礼与中庸
仁、礼、中庸都是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然何者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呢?历来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一种意见认为,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一种意见认为,仁、礼共同构成孔子思想的核心。近年又有人提出第四种意见,认为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持中庸核心说的论者论仁、礼与中庸的关系说,礼是孔子思想的政治范畴,仁是孔子思想的伦理范畴,中庸是孔子思想的哲学范畴。仁和礼皆不能构成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中庸则不同,第一,孔子把中庸看作超越其他诸德之上的至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因而包括了礼和仁。第二,在礼与中的关系上,孔子提出复礼时,首先要求正名,所谓正名即要求君臣父子的名位必须符合中正。因而执中致和成为礼制的指导思想。第三,在仁和中的关系上,孔子经常以射喻仁。这就意味着:(1)孔子的求仁之方是从射中领悟而来的,也即中正要求的体现;(2)射之不中与道之不达一样,存在一个过与不及的失中问题;(3)以射喻仁反映了对君子思想行为的中节要求;(4)以射喻仁体现了人我关系处理的恰如其分。这都说明中庸世界观是孔子整个思想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应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另有论者根据对《论语》有关章节所作的时序考察和其它文献记载,把孔子的思想分为三个发展期,并与礼、仁、中庸挂搭起来:他37岁自齐返鲁为前期与中期的分界,60岁居陈为中期与后期的分界。
孔子前期立论多与礼有关,有关仁的主要论述则集中在中期,“中庸”、“中行”是他居陈以后的新提法。因此,其思想演进当以“礼——仁——中庸”为基本脉络。这一进程不仅符合孔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大体符合孔子对自己的思想演进所作的“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表述。这一进程使孔子思想呈现阶段性差异,但其中心仍然是仁,仁不仅对礼起制导作用,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庸的提出也是为了在存在社会矛盾的情况下更切实地推进仁的实施。
仁是否一定如论者所说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固然还可以讨论,但论者摒弃单纯地就礼、仁、中庸谈礼、仁、中庸,而将其与孔子思想的演进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和认识,此种研究理路却是值得提倡的。
4.中庸之道不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