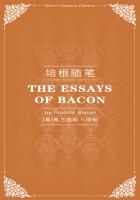1
卖水人曾经去过我的村庄,他挑着
两桶水,满脸汗珠,站在大树到处漏光
的阴影里。他问刚从地里归来的
我的母亲:“水缸空了吗?这里有水。”
我的母亲因过量的劳作而身体变形
她弯着腰,一声不吭,肩上的锄头
碰着了卖水人的桶绳
满天的阳光照射着地上的两桶水
两只水桶在斜坡上渐渐滚远,我的母亲
在水迅速渗透的瞬间回过头看了一眼
她看见了水中有一张支离破碎的脸
并且眨眼之间就被土地吸走了,而卖水人
正在斜坡上追赶他的水桶,拖着的扁担
不停地打击着他那奔跑的影子
我的母亲对着斜坡大喊:“嗨,卖水人
我没钱,但可以煮顿饭给你吃。”
那顿饭我还记得,吃的是土豆和南瓜
外加一碗火烧辣子。卖水人
坐在我父亲的旁边,始终很少说话
像一尾跳到岸上的鱼,干渴的身体上
看不到一点水分。他走的时候
夜己经深了。他跟我的父亲说
我的村庄是一个开裂的村庄,然后
挑着两桶月光消失得一干二净
2
这个古怪的卖水人后来再也没有去过
我的村庄,可作为一个暗示,在他走后
的连续几年间,干旱使我的父母颗粒无收
在无休止的饥饿折磨下,我的父亲
开始怀疑卖水人是个神灵,可是
任凭我们怎样地怀想,也想不起
卖水人的样子,只记得他的水桶上
画着很多饱满的谷穗,而在等待开饭
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坐在暗处
玩着一副破破烂烂的纸牌
我记得卖水人的身材很矮,他的眼睛
仿佛一直都不曾睁开。我的父亲高大健壮
弯着腰问他:“嗨,卖水人,家在哪个寨子?”
他腾出一只手,指了指南边,南边是我家的门
门外就是空空荡荡的菜园子,以及阳光
和天。父亲摇了摇头,“呸”的一声
吐了口浓痰在手心里,开始替母亲劈柴
母亲不同意父亲的看法,母亲认为
她引回家的是个对土缺少耐心的人
不像掌管土地的神灵。母亲的理由很简单
谁会到一个到处都是池塘的地方来卖水
父亲则一直在饥饿中坚持自己的看法
他的理由很简单:谁会到一个
到处是池塘的地方来卖水,而且带着纸牌
而且,父亲说:“他的牌技实在高超
纸牌和他,好像是一个整体,他的脸
埋在暗处,分明就是一张黑桃k”
这种争论持续了多年,直到磨刀人去了
我的村庄,我的父母才闭上嘴巴
磨刀人坐在干涸的池塘中,没有人理会
他们觉得这又将是一个秘密的人
我的父亲甚至非常肯定地断言:
“到一个没有收成的地方来磨刀的人,
这人如果没有带着神示,那么就是病人。”
3
很多天过去了,磨刀人依旧没有揽到
一笔生意,我的父亲再也坐不住了
他决定将那把劈柴的大斧子送去
父亲身无分文,他打算请磨刀人吃饭
他佯装没看见母亲眼中的泪水,以不可
违抗的手势,指了指屋梁上吊着的半袋种子
我记得父亲出门的时间大约是黄昏
他提着斧子,脸很阴沉,有点像一个
前去复仇的恶棍。母亲则泪流满面
种子在石磨中破碎的声音令她浑身颤栗
种子做成的饭,香气弥漫了我的村庄
端上桌,冷了,父亲还没回来,回来的时候
己经很晚,父亲手中的斧头没有磨亮
样子像一个被仇人打败的人
磨刀人没来,种子却做成了饭
我的母亲却不再流泪,对父亲说道:
“嗨,饭冷了,要不要再热一热?”
那口气,仿佛家里还有几千斤粮食
父亲的失败纯粹是天意,击败父亲的
是神秘女人米米,米米像只乌鸦
她也看中了那个摇人心旌的黄昏
她飞抵池塘的时候,我的父亲
才提着斧头走出家门。米米的刀
是一把黑颜色的屠刀
米米说:“嗨,磨刀人,这是我的刀!”
那是个没有水的黄昏,我的父亲
目睹了一幕困扰他一生的情景
他看见夕照中的红颜色的磨刀人
首先挑破了自己的手,用血为米米磨刀
那是把嗜血的刀,磨到天空彻底黑完
仍拒绝暴露本性,依然比天空黑
磨刀人对米米说:“女人,我知道你叫
米米,你走吧,我会让刀锋利无比。”
米米走出了池塘,在离我的父亲不远
的一棵树下站定,神色凄迷
我的父亲和米米,两个饥饿的形容词
他们看见池塘中的磨刀人迅速地
扒光了衣物,以交媾的姿式拱动在
磨石上面。像一个自慰的动词。池塘中
没有发出例行的喊叫,树下的米米
没有动。没有动。只是紧紧地抱住了大树
磨刀人用精液为米米磨刀
磨出了一把天下最美最锋利的刀
这成了我们村庄的又一个秘密
4
我的父亲,这秘密中的线人
从此便沉默不语。而雨水自那天深夜
便开始不停地浇灌我的村庄
村庄里到处都奔跑着哭泣的人
就像那些池塘,水满了,就往外流
在这混乱的背景中,米米和磨刀人
悄悄地走了,像两个遗失了的地址
很久以后,我的母亲才朝着我的父亲
大吼:“嗨,你知道磨刀人去了哪里,
还有米米?”我的父亲,他正
跪在潮湿的地上,掠沟里的水
认真地清洗白菜叶子……父亲整天
都很忙,绝不跟母亲争论
直到有一天,母亲说:“嗨,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疼得要命。”
父亲说:“让我看看。”我记得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的父亲
他指着母亲的右眼,笑得浑身发抖
母亲的右眼角长出了一根绿色的细苗
在村卫生所肮脏的病床上,我的母亲
回忆道:“请磨刀人吃饭的
那个黄昏,一颗籽种飞进了眼睛。”
医生笑得前仰后合,可这个技术低微的
城里人,并没有医好母亲的眼睛
眼睛里长禾苗,我的母亲,成了县报上
的一条新闻,母亲的照片,模糊不清